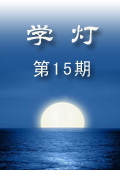
《學(xué)燈》2010年第3期(總第15期)
主 編:李銳 朱清華
周 期:季刊
出版時間:2010年7月
味道:追尋中國哲學(xué)方法論
貢華南
一
科學(xué)主義思潮的興起與挑戰(zhàn)是20世紀(jì)中國哲學(xué)遭遇到的最深刻、最強(qiáng)大的一次危機(jī)。表面上看,中國哲學(xué)的危機(jī)源于另一學(xué)科——科學(xué)——的挑戰(zhàn),從實(shí)質(zhì)層面看,科學(xué)-哲學(xué)一體的西方哲學(xué)文化構(gòu)成了中國哲學(xué)最強(qiáng)大的威脅。“科學(xué)派”所倚重的利器——科學(xué)方法(具體地說就是:經(jīng)驗(yàn)、理性、實(shí)證、、形式化、普遍有效性,等等),乃是西方哲學(xué)慣常推崇與使用的方法。眾所周知,西方近代以來的實(shí)證主義(20世紀(jì)以邏輯實(shí)證主義為代表)、現(xiàn)象學(xué)等流派以“科學(xué)”作為哲學(xué)的目標(biāo),將“科學(xué)方法”樹立為追尋的目標(biāo)而一再表現(xiàn)出西方哲學(xué)方法論的自覺。當(dāng)科學(xué)方法的普遍價值被中國的科學(xué)派認(rèn)同、接受,并以之作為根據(jù)來清理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結(jié)論自然且必然是:中國哲學(xué)沒有“科學(xué)方法”支持,它不是“科學(xué)的”,故它“不科學(xué)”。基于科學(xué)的普遍價值,“不科學(xué)的”就等于“無真理性”,便是“錯誤”、“荒謬”,便是“玄學(xué)”。
顯然,中國哲學(xué)首先遭受的是現(xiàn)代方法論的挑戰(zhàn)、方法論的危機(jī)。
如何應(yīng)對方法論的挑戰(zhàn)與危機(jī)?中國哲學(xué)如何自我理解、自我規(guī)定?這問題關(guān)涉的是:中國哲學(xué)或者存在,或者毀滅。
“科玄”論戰(zhàn)中的“玄學(xué)派”意識到了這個問題。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在“科玄”論戰(zhàn)之前結(jié)合中西文化大談“直覺”的梁漱溟先生。在1922年出版的名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xué)》一書中,梁漱溟說“宇宙的本體不是固定的靜體,是‘生命’、是‘綿延’……要認(rèn)識本體非感覺理智所能辦,必方生活的直覺才行,直覺時即生活時,渾融為一個,沒有主客觀的,可以稱為絕對。”[1]與生命、綿延、本體相應(yīng)的方法即是與感覺、理智相對的“直覺”。梁漱溟又將“直覺”與儒家思想傳統(tǒng)最核心的范疇“仁”建立聯(lián)系,他說“‘仁’就是本能、情感、直覺。”[2]直覺不是認(rèn)識外物意義上的純粹的方法,而是與儒學(xué)最核心的“仁”有著直接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的、“中國人的”存在方式。
張君勱1923年清華大學(xué)的演講以類似的方式突出了直覺的方法論意義。他認(rèn)為,直覺可以解決人生觀,解決人的獨(dú)特的價值,發(fā)展人的完善的人格,表現(xiàn)人類精神之自由等活的實(shí)在問題,直覺是玄學(xué)的標(biāo)志。在張君勱看來,直覺在內(nèi)涵上是與理智的分析,與科學(xué)的歸納、演繹等科學(xué)的方法相對立的一種方法。“皆其自身良心之所命起而主張之……故可曰直覺的也。”[3]直覺的發(fā)生都是主觀意識偶然流露、起起滅滅而無理可循。在這個意義上,直覺屬于非理性的功能與方法。由強(qiáng)調(diào)與“科學(xué)方法”的對立,直覺遂成為一個影響深遠(yuǎn)的、方向性的,同時又是配得上其玄學(xué)稱號的玄而又玄的中國哲學(xué)的方法論綱領(lǐng)。
中國哲學(xué)之后的進(jìn)程正是沿著這綱領(lǐng)所開辟的方向展開的。我們看到,朱謙之在《一個唯情主義者的宇宙觀及人生觀》中將直覺當(dāng)作通達(dá)有情世界的唯一道路;[4]熊十力有“性智”與“量智”之分,將性智規(guī)定為識體之知、對本體界的實(shí)證之知,即“證會”、“體認(rèn)”、“身作證”。在熊十力看來,西方哲學(xué)中的思辨?zhèn)鹘y(tǒng)往往將自己以思維構(gòu)造的本體或其它存在當(dāng)作對象性的東西看待,而對象性意味著與自身存在不相關(guān),這樣就把本體當(dāng)作了外在于己的物事,獲得知識然而卻無法獲得本體。熊十力堅(jiān)定地認(rèn)為,性智乃實(shí)證本體的唯一路徑,這也是中國哲學(xué)的血脈:“吾平生主張哲學(xué)須歸于證,求證必由修養(yǎng),此東圣血脈也。”[5]血脈在此,故熊十力在《新唯識論》結(jié)篇鄭重申明“欲了本心,當(dāng)重修學(xué)”。[6] “修學(xué)”即修養(yǎng)的工夫,即證會、性智。
將直覺推至中國哲學(xué)方法論根基的是牟宗三先生。牟宗三認(rèn)為,直覺是“呈現(xiàn)”,是“具體化原則”,是知識、理論、概念、思想獲得具體實(shí)在意義的根基。大體上說,直覺有兩種:感觸直覺與智地直覺。[7]感觸直覺可以呈現(xiàn)出“現(xiàn)象”;智的直覺則呈現(xiàn)“本體”。牟宗三認(rèn)為,感觸直覺只呈現(xiàn)而不創(chuàng)造,即西方認(rèn)識論中的接受性經(jīng)驗(yàn)。智的直覺既呈現(xiàn)也創(chuàng)造,但智的直覺之存在為康德所代表的西方思想傳統(tǒng)所否認(rèn)。中國哲學(xué)將人理解、規(guī)定為“有限而無限”的存在者,因此,才能將“創(chuàng)造性”的“智”與“呈現(xiàn)性”、“實(shí)現(xiàn)性”的“直覺”結(jié)合起來。智的直覺之可能只能依據(jù)中國哲學(xué)傳統(tǒng)來建立,反過來說,智的直覺是中國哲學(xué)的基石,是中國哲學(xué)的特質(zhì)。中國哲學(xué)之命運(yùn)就系在智的直覺之上,否定智的直覺則“全部中國哲學(xué)不可能”。[8]
將中國哲學(xué)命系直覺、性智、智的直覺,其旨皆在強(qiáng)調(diào)中國哲學(xué)獨(dú)特的方法論。但考慮到它們與“形上學(xué)”的親密關(guān)系,我們有理由提問:中國哲學(xué)是否只有形上學(xué)、沒有形下學(xué)?對西方哲學(xué)來說,這個問題則是:西方哲學(xué)是否只有形下學(xué),沒有形上學(xué)?如果有形下學(xué),那么,其方法論的根基何在?中國哲學(xué)有無貫穿于形上形下的方法論?
牟宗三以感觸直覺說現(xiàn)象界已經(jīng)向我們點(diǎn)示,直覺非中國哲學(xué)的代名詞,其在西方哲學(xué)也有其位置。事實(shí)上,從梁漱溟始,我們的哲學(xué)家一直依傍著、跟著柏格森、倭鏗、康德等西方哲學(xué)家在說“直覺”。我們的直覺到底與他們的直覺有何不同?“不同”在作用機(jī)制方面如何表現(xiàn)?單以“主客”不分、不用概念、推理等中介直接覺到、與科學(xué)對立等依傍性的方式描述的話,直覺何以能洗脫“神秘兮兮”、“糊涂漿”之嫌疑?
牟宗三對“智的直覺”的規(guī)定最有依傍嫌疑,比如,對“智的直覺”的界定。牟宗三依著康德說:
就其為理解言,它的理解作用是直覺的,而不是辯解的,即不使用概念。就其為直覺言,它的直覺作用是純智的,而不是感觸的。智的直覺就是靈魂心體之自我活動而單表象或判斷靈魂心體自己者。智的直覺自身就能把它的對象之存在給我們,直覺活動自身就能實(shí)現(xiàn)存在,直覺之即實(shí)現(xiàn)之(存在之)此是智的直覺之創(chuàng)造性。[9]
“智的直覺”的內(nèi)涵界定,其存在的條件、根據(jù)皆依據(jù)康德之判定,把中國哲學(xué)拿來與康德所設(shè)置的條件一一對照而產(chǎn)生了諸多說法。這些說法對于與西方哲學(xué)“接軌”,對于“使中國哲學(xué)哲學(xué)地建立”[10]無疑有著重要作用。但他卻必然將中國哲學(xué)引導(dǎo)至于“道德的形上學(xué)”、“無執(zhí)的存有論”,而遠(yuǎn)離了(形)上(形)下貫通的真實(shí)的文化世界。
依傍著西方說中國哲學(xué)的特質(zhì),這實(shí)在是像“吊詭”的做法。依傍不依傍先存而不論,就問題說,我們要追問的是:中國思想中有無貫通于形上形下的方法?到哪里去追求這樣貫通于形上形下的方法?從邏輯上說,從西學(xué)東來之前,乃至從佛學(xué)東來之前的思想世界尋求中國思想自身的經(jīng)驗(yàn)、范疇似乎是一條可行的道路。
二
事實(shí)上,許多哲學(xué)家更愿意講普遍的哲學(xué)方法,或者說,將自己推崇的方法表述為普遍的哲學(xué)方法,以期能使自己的哲學(xué)獲得更多的認(rèn)同,獲得更強(qiáng)的合法性。比如,馮友蘭在《新理學(xué)》中認(rèn)為其體系是“接著”宋明以來的理學(xué)講,在《新原道》中將“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理解為中國哲學(xué)的主流傳統(tǒng),相應(yīng)于此的形上學(xué)(不是哲學(xué))方法有二:正底方法與負(fù)底方法。[11] “正底方法”就是邏輯分析法;“負(fù)底方法”是“講形上學(xué)不能講”。邏輯分析法是純粹形式演繹,其命題是分析命題、是永真的重復(fù)敘述。真正的形上學(xué)命題對于實(shí)際無所肯定,但對于一切事實(shí)卻無不適用,因此,形上學(xué)命題都是空靈的命題,“真正底形上學(xué),必須是一片空靈。”[12]在馮看來,西方哲學(xué)大部分用“正底方法”,中國禪宗、道家主要用“負(fù)底方法”,馮友蘭稱其新理學(xué)是集兩種方法而成就。就新理學(xué)的四組命題看,它們都是永真的分析命題,但就其中的最重要“理、氣、道體、大全”觀念看,它們又是不能講的,或,只能用負(fù)底方法講。掌握這幾種觀念可以使人游心于物之初、有之全,可以提高人的境界。[13]哪些方法可以稱得上是“中國哲學(xué)的方法”?馮友蘭沒有說。他推崇邏輯分析方法,但認(rèn)為這不是西方獨(dú)有的方法。他對名家、魏晉玄學(xué)辨名析理、超脫形象、經(jīng)虛涉曠的贊譽(yù),以及對孔孟未能“經(jīng)虛涉曠、超乎形象”的批評,對宋明道學(xué)沒有直接受名家洗禮的遺憾都表明馮友蘭更熱衷于在中國傳統(tǒng)中尋求邏輯分析思想的資源。他推崇負(fù)底方法,認(rèn)為道家、禪宗都是真正的形上學(xué),但他也認(rèn)為維特根斯坦的靜默與禪宗方法相通。
金岳霖不大談“哲學(xué)的方法”,而是談“哲學(xué)的態(tài)度”,談“中國哲學(xué)的態(tài)度”。他說“元學(xué)(即哲學(xué))的態(tài)度”與“知識論的態(tài)度”不同,“知識論的態(tài)度”是“我可以站在知識論底對象范圍之外,我可以暫時忘記我是人,凡問題之直接牽扯到人者我可以用冷靜的態(tài)度去研究它,片面地忘記我是人適所以冷靜底態(tài)度。”[14] “元學(xué)的態(tài)度”則不同:“我雖可以忘記我是人,而我不能忘記‘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我不僅在研究底對象上求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底結(jié)果上求情感的滿足。”[15]聯(lián)系金氏《中國哲學(xué)》一文,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元學(xué)的態(tài)度”在中國哲學(xué)中始終得到貫徹與體現(xiàn)。比如,金岳霖說,“天人合一”是中國哲學(xué)最突出的特點(diǎn),具體說就是,堅(jiān)持“主體融入客體,客體融入主體,堅(jiān)持根本同一,泯除一切顯著差別,從而達(dá)到個人與宇宙不二的狀態(tài)。”[16]天人合一即是人與自然合一,就是哲學(xué)與倫理、政治合一,個人與社會合一。所以,金岳霖說:“中國哲學(xué)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蘇格拉底式任務(wù)。其所以如此,是因?yàn)閭惱怼⒄巍⒎此己驼J(rèn)識集于哲學(xué)家一身,在他那里知識和美德是不可分的一體。他的哲學(xué)要求他身體力行,他本人是實(shí)行他的哲學(xué)的工具。按照自己的哲學(xué)信念生活,是他的哲學(xué)的一部分。他是事業(yè)就是繼續(xù)不斷地把自己修養(yǎng)到進(jìn)于無我的純凈境界,從而與宇宙合而為一……哲學(xué)……在極端情況下,甚至可以說就是他的自傳。”[17]在金看來,蘇格拉底的傳統(tǒng)在西方中斷了,而中國幾乎一直保存到今天。西方發(fā)展的是思維的數(shù)學(xué)模式、幾何模式,是邏輯與認(rèn)識論,簡言之,堅(jiān)持與發(fā)展的就是“知識論態(tài)度”;“元學(xué)的態(tài)度”則算得上中國哲學(xué)的態(tài)度,也可以說就是中國哲學(xué)的方法。
有態(tài)度,有理智,那么,中國哲學(xué)有邏輯嗎?眾所周知,金岳霖所謂“邏輯”主要是指“形式邏輯”,金氏說中國哲學(xué)邏輯不發(fā)達(dá)主要指中國哲學(xué)中“形式邏輯”不發(fā)達(dá)。那么,形式邏輯之外還有邏輯嗎?與金岳霖把邏輯理解為不依賴于時間與經(jīng)驗(yàn)而永真的先天之物不同,中國現(xiàn)代另一位重要的哲學(xué)家張東蓀則認(rèn)為,邏輯首先不是知識,而是思想的程式,它受文化中范疇的左右,跟著哲學(xué)思想走,其最終的決定者則是“文化的需要”。因此,邏輯的“真”由其背后的文化所決定,不存在脫離具體思想范圍而永真的邏輯。邏輯由文化的需要決定具體地表現(xiàn)在不同的文化需要都有相應(yīng)的邏輯與之對應(yīng)。所以,邏輯不是唯一的,而是具有多種的形式。基于此,張東蓀認(rèn)為邏輯大致有四種:形式邏輯、數(shù)理邏輯、形而上學(xué)的邏輯及社會政治思想的邏輯。
形式邏輯的特性在于整理言語,它的內(nèi)容或規(guī)則都受到社會性的通俗哲學(xué)的左右[18]數(shù)理邏輯表示的是人類思想中的數(shù)理思想,它不是為了整理言語而產(chǎn)生,因此它并不是形式邏輯的繼續(xù)。就其背后的哲學(xué)看則是“關(guān)系哲學(xué)”或“函數(shù)哲學(xué)”,而不是形式邏輯依靠的本體哲學(xué)與因果哲學(xué)。形而上學(xué)的邏輯之特性在于滿足人類的神秘經(jīng)驗(yàn)。它的基本原理是“相反者之合一”,其對象是“絕對”。[19]社會政治思想的邏輯則是從事社會政治活動的人自然具有的邏輯,其特性是“相反律”即只承認(rèn)相反而不需要兩者之“合一”,其目標(biāo)是動、變化。從四種邏輯的特性看,它們都是為了對付不同的對象這種需要產(chǎn)生的。張東蓀通過對四種邏輯的分析后指出,邏輯都是跟著文化走的,任何邏輯都沒有通貫一切文化的普遍性。就中國思想的狀況講,漢語的特殊構(gòu)造與形式邏輯并不協(xié)和;中國古典數(shù)學(xué)只發(fā)展到代數(shù)的階段,所以,數(shù)理邏輯亦不會產(chǎn)生出來。因此,這兩種邏輯并不為文化所需,自然也就不能發(fā)達(dá)起來。然而,中國歷史上漫長的朝代更替又直接、間接地促使人們對社會政治活動進(jìn)行反思。哲學(xué)思想是社會政治思想的間接表達(dá),后者的發(fā)展使形而上學(xué)的邏輯與社會政治思想的邏輯都得到了發(fā)展。所以,在中國思想中,后兩種邏輯非常流行、發(fā)達(dá)。
馮契基于中國哲學(xué)史的研究既探討了中國哲學(xué)中另類“邏輯”,也探討了中國哲學(xué)中另類“認(rèn)識論”。另類邏輯是“辯證邏輯”;另類認(rèn)識論是“廣義認(rèn)識論”。
就形式看,辯證邏輯不像形式邏輯那樣撇開內(nèi)容只談形式,其內(nèi)容與形式是不可分割的有機(jī)體;形式邏輯研究思維處于相對穩(wěn)定中的形式,而辯證邏輯是研究思維的辯證運(yùn)動的形式;形式邏輯這種把握思維形式的靜態(tài)的關(guān)系,辯證邏輯由抽象到具體,反映了事物的整體、過程、綜合、趨勢、泉源,達(dá)到了具體與抽象、主觀與客觀的統(tǒng)一;形式邏輯不考察概念的理想形態(tài),辯證邏輯揭示具體真理,具有理想形態(tài)。[20]馮契認(rèn)為,中國在先秦也曾發(fā)展出比較完備的形式邏輯體系,如《墨辯》,但從整個哲學(xué)演進(jìn)的過程看,這個傳統(tǒng)沒能得到持續(xù)的發(fā)展,相反,辯證邏輯卻得到了持續(xù)的發(fā)展、取得了較大的成就。在先秦總結(jié)階段,即在《荀子》、《易傳》、《月令》、《內(nèi)經(jīng)》已具有辯證邏輯雛形,到宋明,辯證邏輯有了進(jìn)一步的發(fā)展。[21]當(dāng)然,馮契也補(bǔ)充道,古代的辯證邏輯只是樸素的、自發(fā)的,還不具備嚴(yán)密的科學(xué)形態(tài)。
在認(rèn)識論方面,馮契在狹義認(rèn)識論所關(guān)注的“感覺能否給予客觀實(shí)在”和“科學(xué)知識何以可能”問題之外,又拓展出“邏輯思維能否把握宇宙發(fā)展法則”和“理想人格如何培養(yǎng)”問題,這四個問題合成馮契著名的“廣義認(rèn)識論”。他認(rèn)為,中國古代哲學(xué)“較多和較長期地考察了上述后兩個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考察上,顯示出中國傳統(tǒng)哲學(xué)的特點(diǎn)。”[22]馮契先生還提及,在自然觀上,西方的原子論得到比較早的發(fā)展,中國古代則比較早地發(fā)展出了氣一元論。所以,中西哲學(xué)的差異既是思想方向、理想關(guān)懷的差異,也是思維方式、思想方法層面的差異。
三
本書所關(guān)心的問題是:哲學(xué)既然與哲學(xué)家互體,哲學(xué)方法如何體現(xiàn)于個人的存在?或者說,中西哲學(xué)展開方式的差異在個人存在方面是如何生成,及如何體現(xiàn)的?或者,個人存在方式的差異如何到達(dá)思想層面的?
牟宗三取自傳統(tǒng)哲學(xué)的另外一組概念,即感通與潤物,對我們的方法論思考有十分醒目的啟示,它既能真切地表述“智的直覺”的內(nèi)涵,又緊密接近這個真實(shí)的文化世界。“仁以感通為性,以潤物為用”[23] “感通”是指我以“感”的方式進(jìn)入他人、進(jìn)入世界萬物。“潤物”則是我在“感”的過程中,由物我相互進(jìn)入、相互攝取而給予萬物以價值、意義、精神生命等人性內(nèi)容。“感”展示了一種不同于康德意義上的接受性經(jīng)驗(yàn)方式,同時也兼表達(dá)出經(jīng)驗(yàn)、理性,以及一般存在論的內(nèi)容。不過,正如上文所論,牟宗三僅關(guān)注形上感通的主體,即仁心本體,這又使感通概念的適用性變得可疑起來。
唐君毅在《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中亦嘗試著以“感”來解釋中國哲學(xué)傳統(tǒng),頗有可觀。“所謂感通活動,與其方向、方式,如更說吾人之生命存在之心靈為其體,則感通即是此體之活動或用……言境為心所感通,不只言其為心所知者,乃以心之知境,自是心之感通于境,此感通中亦必有知;但知之義不能盡感通之義,知境而即依境生情、起志,亦是感通于境之事故。”[24] “感通”不限于形而上之心體的感通,也可指形下之心與境的感通,乃至指妄境與妄心之感通。種種心靈之感通活動,包括我們通常所說的感官之活動。唐說:“實(shí)則感覺即感通,通即合內(nèi)外,而兼知內(nèi)外”[25]一切感官活動都被納入“心靈”活動,因而有它們亦是“感通”活動,比如唐說“視心”進(jìn)行視覺的感通,“聞心”進(jìn)行聽覺的感通[26]唐君毅還以感通(知)、感應(yīng)(意)、感受(情)來解釋意識的活動,他說“人謂知與情意有別,乃自知只對境有所感通,而不必對境之有所感受、感應(yīng)說。感受是情,感應(yīng)是意志或志行。心靈似必先以其知通于一境,乃受此境。而應(yīng)之以意或志行。……心對境若先無情上之感受,亦無知之感通;人心若初不求應(yīng)境,亦對境無情上之感受。又感受、感應(yīng),亦是一感通于境之事。人若只有知之感通,不更繼之以感受與感應(yīng),則其對境之知之感通,亦未能完成。”[27]知、情、意皆是“感”,只不過,其“感”的方式、方向不同而已。由種種心靈感通起種種境,而顯出境的層次之高低、遠(yuǎn)近、淺深,遂成“心靈九境”。
說感覺即感通,特別是以視覺、聽覺來說感通,我們聽來頗覺新鮮。但恰恰于此,我們的問題也涌現(xiàn)出來。視覺、聽覺如何“通”內(nèi)外?如我們后文所述,在古希臘以來的原子論思想傳統(tǒng)中,視覺只能把握外物的外在形狀而無法“進(jìn)入”物自身,是無法“通”內(nèi)外的。以“視心”、“聞心”說視覺、聽覺事實(shí)上將感覺的問題轉(zhuǎn)換成了“心”的問題,轉(zhuǎn)換成了文化的問題。以視心說視覺,以視覺說感通只有在特定文化傳統(tǒng)中才可能,至少,中國文化中生成了這種可能性。
“感”如何能夠“通”物?誠然,這個問題只是中國文化系統(tǒng)中的一個子問題。進(jìn)一步追問會有許多層次、許多方向,我個人的興趣是關(guān)注這個問題在生命存在層次的根基,試圖在生命“經(jīng)驗(yàn)”層面嫠清這個問題。至于如此做的理由,我愿意再引唐君毅在《中國哲學(xué)原論——原道篇》“自序”中的一段話來申明之:“吾所謂眼前當(dāng)下之生命心靈活動之諸方向,其最切近之義,可直自吾人之此藐?duì)柶叱咧|之生命心靈活動以觀,即可見其所象征導(dǎo)向之意義,至廣大,而至高遠(yuǎn)。吾人之此身直立于天地間,手能舉、能推、能抱、能取;五指能指;足能游、能有所至而止;有口能言;有耳能聽;有目能見;有心與首,能思能感,即其一切生命心靈之活動之所自發(fā)。中國哲學(xué)中之基本名言之原始意義,亦正初為表此身體之生命心靈活動者。試思儒家何以喜言‘推己及人’之‘推’?莊子何以喜言‘游于天地’之‘游’?墨子何以喜言‘取’?老子何以言‘抱’?公孫龍何以言‘指’?……誠然,字之原義,不足以盡其引申義,哲學(xué)之義理尤非手可握持,足所行履,亦非耳目之所可見可聞。然本義理以觀吾人之手足耳目,則此手足耳目之握持行履等活動之所向,亦皆恒自超乎此手足耳目之外,以及于天地萬物。此即手足耳目所以為手足耳目之義理。此義理之為人之心知所知,即見此手足耳目,亦全是此‘義理’之流衍之地。故真知手之‘推’,亦可知儒者之推己及人之‘推’。真知足之‘游’,亦可知莊子之游于天地之‘游’充手之‘抱’,至于抱天地萬物,而抱一、抱樸,即是老子。盡手之取,至于恒取義,不取不義,利之中恒取大,害之中恒取小,即是墨子。窮手之指,至于口說之名,一一當(dāng)于所指,即公孫龍也。”[28] “經(jīng)驗(yàn)”方向恰恰是生命展開的方式,思想亦在此生命展開中運(yùn)行。
依照這個識見,本文從味、味覺開始討論中國哲學(xué)的生成基礎(chǔ),并探討了“味”活動的存在論意義、結(jié)構(gòu)及其在感覺譜系中的地位,以及形下、形上層面所生長出來的豐富意義。考察了“味”活動與“感”活動的歷史及邏輯關(guān)聯(lián),由此把近代哲學(xué)以來一直被降低為與理性相對的“感性”意義重新上升為一種具有本源意義、貫穿于今日所謂感性與理性層面的活動。在此基礎(chǔ)上,作者參照西方“沉思”、“移情”觀念考察了感思、感情等觀念及它們所展示的思考方式及存在方式。傳統(tǒng)哲學(xué)由“味”、“感”這種特殊的文化經(jīng)驗(yàn)生成了虛實(shí)、幽明、有無統(tǒng)一的范疇——“象”,借助于“象”,中國哲學(xué)在普遍性的追求方面走上了“立象”的道路。最后,在對作為思想方式與存在方式“味”、“感”與“象”的特征的深入思考基礎(chǔ)上,作者考察了20世紀(jì)中國哲學(xué)“中國化”、“哲學(xué)化”的雙重努力,并以“味”、“感”、“象”為核心對此問題作了提綱式展望。
注釋:
[1] 《梁漱溟全集》,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卷,第406頁。
[2] 《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455頁。
[3] 《科學(xué)與人生觀》,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6頁。
[4] 參見朱謙之:《一個唯情主義者的宇宙觀及人生觀》,上海,泰東書局1928年。
[5] 《新唯識論》第691頁。
[6] 《新唯識論》第154頁。
[7] 實(shí)際上,為了貫徹“具體化原則”牟宗三為了給科學(xué)知識提供根基,又提出“形式直觀”(具體參見《現(xiàn)象與物自身》,臺灣學(xué)生書局1990年,第162頁)。
[8] 牟宗三:《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xué)》序,臺灣商務(wù)印書館1971年版,第2頁。
[9] 《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xué)》第145頁。
[10] 《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xué)》序,第3頁。
[11] 馮友蘭:《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五卷,第149頁。
[12] 《三松堂全集》第五卷,第155頁。
[13] 《三松堂全集》第五卷,第136頁。
[14] 金岳霖:《論道》第17頁,商務(wù)印書館1987年。
[15] 《論道》第17頁。
[16] 金岳霖:《中國哲學(xué)》,收入《道、自然與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5年,第54-55頁。
[17] 《道、自然與人》第59-60頁。
[18] 張東蓀:《知識與文化》,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46年,第201頁。
[19] 《知識與文化》第61頁。
[20] 馮契:《邏輯思維的辯證法》,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96年,第六章,第六節(jié)。
[21] 馮契:《中國古代哲學(xué)的邏輯發(fā)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5頁。
[22] 《中國古代哲學(xué)的邏輯發(fā)展》,第42頁。
[23] 《中國哲學(xué)的特質(zh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頁。
[24] 唐君毅:《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06年版, 第2-3頁。
[25] 《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第57頁。
[26] “視心”、“聞心”詞見《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第3頁。
[27] 《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第9頁。
[28] 唐君毅:《中國哲學(xué)原論——原道篇》自序,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06年版, 第4-5頁。
本文為貢華南《味與味道》一書《緒論》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