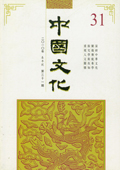
《中國文化》第31期(2010年春季號(hào))
主 辦: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中國文化》編輯部
周 期:半年刊
出版時(shí)間:2010年春季號(hào)
學(xué)人寄語
20世紀(jì)關(guān)於“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爭(zhēng)論,雖然在不同時(shí)期有不同的爭(zhēng)論焦點(diǎn),有不同的理論側(cè)重,有不同的現(xiàn)實(shí)指向,但是無論如何,20世紀(jì)中國的“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討論,從來都不是要不要“現(xiàn)代”的討論,不是要不要“現(xiàn)代化”的討論,也不是要不要改革的討論,更不是要不要接納西方文化的問題。從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東西古今”之爭(zhēng)到80年代的“傳統(tǒng)現(xiàn)代”之爭(zhēng),大力吸收西方文化,推進(jìn)中華民族的現(xiàn)代化,實(shí)際上是參與爭(zhēng)論的各方所共同肯認(rèn)的。因此,爭(zhēng)論的核心,始終是要不要“傳統(tǒng)”,如何對(duì)待“傳統(tǒng)”的問題。由於爭(zhēng)論的焦點(diǎn)是如何對(duì)待中國傳統(tǒng)文化,所以20世紀(jì)中國的“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論爭(zhēng),始終以兩種對(duì)立的觀點(diǎn)為主導(dǎo)線索,這就是對(duì)中國傳統(tǒng)文化全面否定的急進(jìn)觀點(diǎn),和主張肯定和繼承傳統(tǒng)文化優(yōu)秀部分的溫和觀點(diǎn)。這兩種觀點(diǎn)的對(duì)峙,也就是我所謂的“反傳統(tǒng)主義與反-反傳統(tǒng)主義”的對(duì)立。由於20世紀(jì)各個(gè)時(shí)期對(duì)中國文化的檢討往往是當(dāng)時(shí)強(qiáng)烈的現(xiàn)代化受挫感的表現(xiàn),折射出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思潮和社會(huì)心理,即渴求現(xiàn)代化的焦慮,所以,在發(fā)生學(xué)上,反傳統(tǒng)主義總是主動(dòng)的、主導(dǎo)的,而反-反傳統(tǒng)主義則是對(duì)反傳統(tǒng)主義的回應(yīng)和抗?fàn)帯7磦鹘y(tǒng)主義希望義無反顧地甩掉歷史文化的包袱,大力推進(jìn)中國走向世界的步伐;反-反傳統(tǒng)主義則主張?jiān)谏鐣?huì)改革和走向世界的過程中,保持文化認(rèn)同,承繼文化傳統(tǒng),發(fā)揚(yáng)民族精神。而在整體上看,這兩方面都是中華民族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張揚(yáng)其生命的不同側(cè)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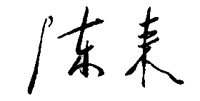
陳來
2010年4月
編 後
本期刊發(fā)湯一介先生兩篇文字,都是警世警策之語,關(guān)心吾中華文化之命運(yùn)者不可不讀。張立文先生的兩篇,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dòng),知善知惡為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四句教新解之外,還有他為韓國版文集所寫的序言。另一探討“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xué),為萬世開太平”的橫渠四句教的文章,可與之互讀。“六經(jīng)”中為何獨(dú)《樂經(jīng)》不傳,項(xiàng)陽提出“六代樂舞”即為《樂經(jīng)》的新說。周昌龍從知識(shí)與道德的雙重紐結(jié)入手論梁任公,熟題中生有新意。夏曉虹考證上海女學(xué)堂創(chuàng)辦始末,資料務(wù)求窮盡。景海峰、虞萬里論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現(xiàn)代三大家,不無可觀。張旭東探討民國學(xué)術(shù)流變的“新”與“舊”,清新可讀。瓜飯樓主馮其庸先生自述學(xué)術(shù)次第,平易懇切,圖畫自然。《切問而近恩》為新欄目,所刊四篇文字,湯一介先生之外,陳嘉映論同通,鄧曉芒、許蘇民商啟蒙,思可以啟人。而周汝昌和顧隨兩先生詩詞唱和之披載,又有范曾先生題序於前,應(yīng)為本期之盛。今年的春天,真?zhèn)€是步履蹣跚,來得好遲也。
2010年4月22曰編後記
文章分頁: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