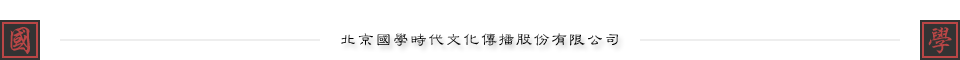拂去記憶的塵埃
正是晉南平原麥熟杏黃的季節(jié),我終于有了合適的機緣,去聞喜看楊深秀墓。
汽車在寬闊的二級路上風快行駛,100多年前戊戌喋血的刀光劍影,仿佛也驚心動魄地閃現(xiàn)在眼前:
102年前的1898年9月28日,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年)八月十三,這是一個血雨腥風的日子。幾天來,北京城里風傳著慈禧從頤和園回宮,囚禁光緒皇帝于中南海瀛臺的消息。維新變法人士或被捕或逃亡,一時間,北京城內(nèi)人心惶惶。加之今天烏云如墨的天色,人們擔心還會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發(fā)生。果然,到了下午,宣武門南邊的菜市口戒備森嚴,忽隆隆推來了六輛囚車,隨著軍機大臣、監(jiān)斬官剛毅的一聲令下,劊子手的屠刀揮處,六位戊戌志士的頭顱落地。他們是:譚嗣同、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第、康廣仁。此時,墨黑的天空大雨傾盆而下,將流淌在菜市口街頭的鮮血漶染得一片淋漓……
然而,戊戌志士的滿腔碧血,真的會被歷史的風雨消痕,讓歲月的囂塵掩匿嗎?
100多年來,有關百日維新運動和戊戌政變的文章和書籍,可謂連篇累牘,數(shù)不勝數(shù)。特別是近十幾年來,電視和電影大演“清宮戲”,令人眼花繚亂,而戊戌變法這段椎心泣血的歷史,卻在這迷亂中閃現(xiàn)出一片耀眼的亮色。“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在苦難深重的漫漫長夜里,變法圖強,成仁取義的忠烈精神,永遠昭示和激勵著后來人。
在“戊戌六君子”中,人們首先想到的是譚嗣同。這位來自湖南瀏陽的青年書生,本可以逃脫慈禧的抓捕,但譚嗣同不走。他慨然對友人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倡也。有之,請自嗣同始。”他不逃不走,而甘愿以自己的血肉身軀,去喚醒國人。他還有獄中題壁詩云:“望門投宿思張儉,忍受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多么激烈而悲壯的亮節(jié)高風!
想到譚嗣同,我卻不能不隨之想起楊深秀。與譚嗣同就義時的轟轟烈烈和死后他應得到的贊譽相比,生前同樣是轟轟烈烈的楊深秀,他的“身后事”又顯得何其寂寞?這位在《清史稿》中依職銜排在“戊戌六君子”之首的人物,多少年來,也僅僅是偶爾被人提及,而他的身世和壯舉卻鮮有人知。
楊深秀,山西聞喜儀張村人。原名毓秀,字恬溟,因諱光緒名載氵恬,遂改名深秀,字漪村。深秀自幼聰穎,6歲入塾,12歲成秀才,21歲中舉。次年赴北京,參加辛未科會試,未中。遂留京拜師求教,深研經(jīng)史、考據(jù)、說文、音韻。在寓居京師的晉人士子中享有盛名。光緒八年,受山西通史局之聘,他回省助修《山西通史》,并曾出任太原崇修書院山長兼主講、令德堂書院協(xié)講。光緒十五年,深秀成進士,補刑部郎中。二十三年十二月,授山東道監(jiān)察御史。此時,面對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欺侮,國內(nèi)維新人士鼓吹變法的潮流涌動,楊深秀上書光緒,闡述“時勢危迫,不革舊無以圖新,不變法無以圖強”的道理,并參加保國會,在朝中積極為康、梁主張推波助瀾。同時上疏光緒,揭露沙俄和德國沆瀣一氣,“合而圖我”的伎倆,反對將膠州灣租讓給德國,以絕列強“踵其后而瓜分”的圖謀。
光緒二十四年初,維新圖強與頑固守舊之間的斗爭日趨激烈,生性懦弱的光緒優(yōu)柔寡斷,時有搖擺。楊深秀于四月十三日上疏,勸光緒不要“游移不斷”,并錚言直諫指出,維新與守舊之間“互相水火,有如仇讎,臣以為理無兩可,事無中立,非定國是無以示臣民之趨向;非明賞罰無以為政事之推行。躑躅歧途者不能至,首鼠兩端者不能行。”“若審觀時變,必當變法。非明降諭旨,著定國是,宣布維新之意,痛斥守舊之弊,無以定趨向而革舊俗也。”
四月二十三日,光緒終于下定決心,宣布變法,頒布“明定國是”詔書。從此,楊深秀更是身體力行地投身于維新變法運動。百日維新期間,面對守舊派對變法的阻撓,楊深秀劾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馬癸,光緒遂將懷塔布等革職;守舊派要劾維新人士湖南巡撫陳寶箴,楊深秀又奮起為之抗疏剖白。在百余天的時間里,楊深秀或單獨上折,或與他人聯(lián)名上折,共上奏折達17件之多。所以,梁啟超在《戊戌變法記》一文中,盛贊楊深秀“上書言定國是,……所陳新政最多。”
八月初六,慈禧發(fā)動政變。囚禁光緒,重新垂簾聽政,并下令逮捕康有為及其同黨。《清史稿》記述當時的情況說:“八月,政變,舉朝惴惴,懼大誅至。獨深秀抗疏,請?zhí)髿w政。”這是八月初八的事。從今人的眼光看來,楊深秀是個多么“不識時務”的人。
楊深秀不顧個人安危,還曾打算前往南苑,說服董福祥的軍隊反正,以救出光緒,重施新政。可惜上疏的第二天(八月初九)他即被逮。心狠手毒的慈禧豈能容他,單是當廷抗疏讓慈禧歸政的“大逆不道”,就夠楊深秀掉幾次腦袋了。
從八月初九被捕,到八月十三被殺,楊深秀在獄中堅貞不屈,寫詩十余首,一身凜然正氣,一意慷慨赴死,而信念不改。他在壁上所留的《獄中詩》寫道:
久拼生死一毛輕,臣罪偏由積毀成。
自曉龍逢非俊物,何嘗虎會敢從行?
圣人豈有胸中氣,下士空思身后名。
縲紲到頭真不怨,未知誰復請長纓。
詩意蒼茫勁健,表達了他對守舊勢力的仇視和對國家民族命運的無盡憂思。
“戊戌六君子”就義時,楊深秀49歲,楊銳41歲,劉光第39歲,譚嗣同33歲,康廣仁31歲,來自福建侯官的“才子”林旭,年僅24歲。一代風流倜儻的志士仁人,以天下為己任,舍生取義,臨大節(jié)而不辱。他們手無寸鐵,甚至可說是手無縛雞之力,但他們有的是滿腔熱血,一片丹心,甘愿為國家民族捐軀灑血,冒死不辭。他們真是將自己的人生的極致,義無反顧地涌入了歷史的大波。至今思之,令人無限感慨,唏噓不已。
儀張村就在新開的二級路旁側,儀張村到了。
楊深秀墓在村邊不遠的地方,熱心的縣文博館館長張英雋先生,很快把我領到了那里。墓丘完全可以用“荒涼”兩個字來概括。一座并不高大的圓土堆,用石塊圍砌著,寂寞地立在一片果園中。果園里間作著小麥,成熟的麥子正待收獲,金黃耀眼。若不是墓丘前面有一塊上書“戊戌志士楊深秀之墓”的碑石,誰會相信這土堆會屬于名震中外的一代英杰。
“六君子”血濺菜市口時,何等的陰森恐怖。楊深秀的尸體,是他的大兒子黻田在山西同鄉(xiāng)的幫助下收殮回來的。縫了八大針才將頭顱與身體連綴。也是在山西同鄉(xiāng)的幫助下,黻田將父親的靈柩運回了聞喜老家。深秀在京還有一小妾,當時京城里盛傳是自縊了的,其實是在混亂中逃離了京城,以后又輾轉回到聞喜,與黻田的妻兒生活在一起。為官清廉的楊深秀,家無余財,生前沒有積蓄,又遭抄斬的滅頂之災,是回鄉(xiāng)后草草安葬了的,豈敢鋪排,也鋪排不起。當時只怕是連一塊碑石也未曾豎立。楊深秀雖身為御史,生前兩袖清風,死后一抔黃土,盜墓賊當然是無須光顧的了。
楊深秀有三個兒子:黻田、墨田、孤田。大兒子黻田,戊戌變法時是隨父親留居京城的。據(jù)《清史稿》記述:楊深秀寫成了“抗疏”,要讓慈禧歸政光緒,“方疏未上時,其子黻田苦口諫之,深秀厲聲喝之退”。生性懦弱、謹慎的黻田,是被父親淋漓的鮮血喚醒了的,此后思想激進,擁護辛亥革命,曾出任民國后的聞喜縣長,后終老故鄉(xiāng)。
在儀張村,我們問起楊深秀的后人,陪同的張英雋先生說,黻田先生的老伴還在呢,于是我們相隨前去探望。
儀張是個大村,新房與舊宅參差,磚墻和土圍毗連。七拐八繞,八卦陣似的,終于找到了一處院落,黻田先生遺孀林風雪老人的住地。這是一座極其破舊的農(nóng)家小院,你很難想象,這座銹磚土墻比一般農(nóng)家還要寒酸的小院,竟會是楊深秀后人的居所。
林風雪老人,河北束鹿人,嫁與黻田在這里已生活六、七十年。老人94歲的高齡,歷盡風雨雪霜,如今病骨支離,生活不能自理,但記憶清晰。現(xiàn)由她的大女兒去域在家侍奉。去域也已76歲,退休前為運城高專教師。
在儀張故里,還有楊深秀的三兒子孤田的后人。依照楊深秀給他的孫輩名字的取字,他的孫子、孫女的名字分別為:去域、去塵、去壅、去坷、去垢……史書上說楊深秀以“澄清天下為己任”,他孤傲高潔,獨立不遷,從給子孫的取名上,也可以看出他寄望后輩力除社會污垢坎坷,為國成才,澤及蒼生的拳拳之情。
楊深秀生前還曾留有《楊漪村侍御奏稿》、《雪虛聲堂詩鈔》等著述,可惜至今未能整理出版,深為憾事。
當今,在我們這個經(jīng)濟洶涌,快餐文化盛行的年月,若要進入一個追求學術、追求真理的境界,遠比進入“戲說”什么歷史故事和人物之中,要困難得多,也枯燥得多,更不要去奢談什么憂國憂民了。歷史上的那些曾留下熱血和生命,那些曾令人肅然景仰、滌蕩著靈魂的身影和足跡,有多少已被記憶的塵土所覆蓋,被時光的風雨沖刷得蹤跡依稀而少有人問津了。物質(zhì)的誘惑,像一條恣肆汪洋的河流,卷載著人們漂流而去。
但對聞喜我并不悲觀。所謂“花落春猶在”,這塊古河東大地上的豐厚的人文積淀,仍在向世人展示著它昔日的輝煌。這塊曾經(jīng)產(chǎn)生過裴氏家族、楊門義杰的土地,仍然是人們解讀何以在歷史上崛起一個名門望族和俊杰義士的最翔實、最原始的“文本”。幸存在這里的地上和地下的文物古跡,也正在吸引著愈來愈多的學者和游人。裴家的德業(yè)文章,楊公的驚世壯舉,不僅是聞喜奉獻給中國的一筆財富,同時也是聞喜現(xiàn)代化經(jīng)濟文化建設的人文源頭和根基。
聞喜畢竟是值得欣喜的。聞喜正聞雞起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