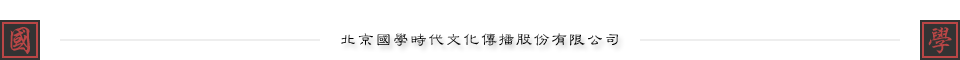“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討論”——讀湯老兩篇舊文
湯用彤先生是我國當代著名的學者,是我最敬仰的師長之一。一九五五年我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正趕上湯老在前一年患腦溢血后臥病在床,因而整個大學期間未能聆聽湯老的教誨。畢業留校工作后,雖亦時有機會與湯老接觸,然仍因湯老病體虛弱,不得在學術上深入求教,此誠平生一大憾事也。但是,湯老在學術上的博大精深,他的專著和論文,對我在學術上的成長是有深刻影響的。我對魏晉玄學研究的興趣,可以說完全是在湯老《魏晉玄學論稿》一書的啟迪下萌發起來的。我雖未能忝列湯老門下,然對湯老之為人學問,私淑久矣,獲益宏矣。
凡讀過湯老論著的人,都會有這樣一種感受,即:湯老的論著史料翔實、考證精當、邏輯嚴密、論理精深、平情立言、實事求是、樸實無華。不論是幾十萬言的巨著,還是幾千言的短文,均有發前人之未發的微旨精論,使讀者開卷受益,得到深刻的啟發。湯老論著的這些特點,固然與他淵博的中外哲學素養和堅實的歷史知識有關,也和他采用了與封建學者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有關。但是,我認為,最根本的,還是在于湯老把對文化的研究,特別是對中國文化的研究,當作是對真理的探求,這樣一個基本的思想,以及他對中外文化相互關系的基本看法有關。這篇短文就想對湯老這些思想作一簡單的介紹。
在湯老親自選編的《往日雜稿》一書中,收錄了他在一九二二年和一九四三年寫的兩篇有關文化史研究的論文。湯老在序言中說:“附錄二篇是我解放前對文化思想的一些看法,它表現了我當時的歷史唯心主義的錯誤觀點,編入本集,便于讀者在讀本書和作者的其他著作時,于我思想有所認識”。這里湯老自稱這兩篇舊文表現了他對文化思想的唯心史觀,這說明了他在解放后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堅持進步的精神。然而我們今天來讀這兩篇舊文,確實可以從中了解一位舊時代愛國的、正直的學者在治學上的基本思想。其中雖不免有許多不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但文章對文化史研究提出的一些有意義的看法,從歷史的眼光來看,還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近代中國,隨著西方科學文化的傳入,對于如何看待西方文化,以及西方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相互關系等問題,在知識界曾引起長期的爭論。有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者;有鼓吹全盤西化者;有提倡尊孔讀經,保存國粹者。一九二二年湯老發表一篇題為《評近人之文化研究》的文章,對當時文化研究中的不同偏向,提出了切中要害的批評。他指出,當時學術界的一個主要弊病是“淺隘”。那些膜拜西方文化者,對中國傳統文化肆意誹薄、輕謾,而實際上,他們對西方文化的了解和介紹“亦卑之無甚高論”。“于哲理則膜拜杜威、尼采之流;于戲劇則擁戴易卜生、肖伯納諸家。以山額與達爾文同稱,以柏拉圖與馬克思并論。”當時正值杜威、羅素來中國“講學”,有些人把他們比之于孔子、釋迦。湯老嚴肅指出,“此種言論不但擬于不倫,而且喪失國體”。那末,那些守舊者的情況又如何呢?湯老分析說,他們看到一些西方學者研究亞洲文化,贊美東方精神,于是就妄自尊大,認為歐美文化即將敗壞,而亞洲文化將起而代之。而實際上,這些人既對東方精神沒有深刻的了解,甚且“亦常仰承外人鼻息”。如“謂倭鏗得自強不息之精神,杜威主天(指西方之自然研究)人(指東方之人事研究)合一之說,柏格森得唯識精義,泰戈爾為印化復興淵泉”等等。總之,“時學淺隘,故求同則牽強附會之事多;明異則入主出奴之風盛”。于是,湯老尖銳地指出:“維新者以西人為祖師,守舊者借外族為護符,不知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討論,新舊淆然,意氣相逼,對于歐美則同作木偶之崇拜,視政客之媚外恐有過之無不及也”。湯老在此提出“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討論”,批判那種崇洋媚外的風氣,這在當時的學術空氣下,不能不說是相當深刻的。
具體地說,湯老認為,文化研究中必須是“研究者統計全局,不宜偏置”,應當“精考事實,平情立言”。只有這樣,才可能探得真理之所在。我認為,對文化研究本著“乃真理之討論”的精神,正是湯老一生為學的基本指導思想和學風。“統計全局”、“精考事實”、“平情立言”,這些也正是湯老著作所以能做到精深、獨到,而歷數世不失其學術價值的根源所在。馬克思主義對待一切問題,包括對歷史文化遺產的研究的根本態度就是“實事求是”。那種從某種既定框架去推衍,用主觀好惡去割取歷史,都是在根本上違背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精神的。因此,就這方面講,湯老的這種治學精神和學風,在今天也還是值得我們提倡和發揚的。
湯老對于中外文化的看法,在我們上引文章中已可看到這樣一個基本的態度:即對于外國文化不是盲目崇拜,對于中國傳統文化也不固步自封。至于中外文化之間的相互關系問題,湯老在一九四三年寫的《文化思想之沖突與調和》一文中有精當的見解。
湯老在當時或主張以中國文化為本位,或主張全盤西化的聲浪中,排除對中外文化關系問題上的各種抽象、空洞的爭論,而從事實出發,特別是以中國歷史已經歷過的事實為借鑒,切實地討論了中外文化是否會相互發生影響和如何相互發生影響,這樣一個本質性的問題。湯老明確反對文化史研究中的兩種錯誤理論:一種是認為“思想是民族或國家各個生產出來的,完全和外來的文化思想無關”;一種是認為“一個民族或國家的文化思想都是自外邊輸入來的”,“外方思想總可完全改變本來的特性與方向”。湯老認為,外來文化與本地文化相互接觸后,其結果是雙方都要受到影響。他說,一方面,一種外來文化傳入,對于一個民族來講多了一個新的成分,這本身已經是一種影響了;另一方面,外來文化要對本地文化發生影響,就必須適應本地文化環境,因此這種外來文化也要受到本地文化的影響而有所改變。至于外來文化之所以會發生變化,這是由于本地文化思想有其自己的性質和特點,不是隨便可以放棄的。湯老以佛教傳入中國為例,指出:“印度佛教到中國來,經過很大的改變,成為中國的佛教,乃得中國人廣泛的接受”。
在這篇文章中,湯老還具體地分析了外來文化思想傳入后與本地文化思想發生關系時一般所需經歷的三個階段:“(一)因為看見表面的相同而調和。(二)因為看見不同而沖突。(三)因再發見真實的相合而調和”。湯老并特別指出,在這第三個階段中“外來文化思想已被吸收,加入本有文化血脈之中了”。這時,“不但本有文化發生變化,就是外來文化也發生變化”。總之,“外來文化思想在另一個地方發生作用,須經過沖突和調和的過程”。“一個國家民族的文化思想實在有他的特性,外來文化思想必須有所改變,合乎另一文化性質,乃能發生作用”。
湯老一生用力最勤的,是對中國佛教史的研究,其中尤其注意于佛教初傳時期——漢魏兩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史的研究。原因就是因為這一時期佛教作為一種外來的文化思想傳入,與中國傳統文化發生了復雜的調和和沖突的關系,如果把這一歷史過程解剖清楚,那就不僅對那一時期中國文化的演變過程可以得到一個清晰的了解,而且對以后中國文化的發展也得窺其端倪。湯老對中國佛教史的研究,正是遵循著上述文章中所總結的那些原則進行的。因此,他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打破了以往佛教史研究中,或以印度佛教來牽合中國佛教,或根本無視印度佛教之原意等偏向,而是深入探討了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后,兩種文化相互作用、影響的關系。具體地分析了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后如何被改造成為中國化的,而同時它又如何影響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過程。因此,湯老的研究,開創了中國佛教史研究的一個嶄新階段。
這里,我想舉出幾個具體例子,以見湯老對問題分析之精深。
一、湯老在上引一九四三年那篇文章中,舉“念佛”這個概念為例,分析說:“通常佛教信徒念阿彌陀佛。不過‘念佛’本指坐禪之一種,并不是口里念佛(口唱佛名)。又佛經中有‘十念相續’的話,以為是口里念佛名十次。不過‘十念’的念字乃指著最短的時間,和念佛坐禪以及口里念佛亦不相同。中國把念字的三個意義混合,失掉了印度本來的意義。”
二、湯老在《謝靈運辨宗論書后》一文中分析了謝靈運如何將中國傳統“圣人不可學不可至”,與印度傳統“圣人可學亦可至”的說法調和起來,歸納出“圣人不可學但能至”的理論,從而為當時著名僧人道生的“佛性”、“頓悟”說論證。謝論本論不足二百字,湯老廣征博引,文亦僅五千言,然從中卻發掘了中印文化融合的契機,并進一步闡發了此種融合,使得“玄遠之學乃轉一新方向”,而且成為“由禪家而下接宋明之學”的一大關鍵。
三、湯老在《魏晉思想的發展》一文中,通過對魏晉玄學思想淵源、發展歷史的細致考察后,得出結論說:“玄學是從中華固有學術自然的演進,從過去思想中隨時演出‘新義’,漸成系統,玄學與印度佛教,在理論上沒有必然的關系。”“反之,佛教倒是先受玄學的洗禮,這種外來的思想才能為我國人士所接受。”“不過以后佛學對于玄學的根本問題有更深一層的發揮”,“佛學對于玄學為推波起瀾的助因是不可抹殺的。”
這些例子都充分說明了,湯老在中國佛教史和魏晉玄學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是與他對中外文化相互關系的基本看法分不開的。我們從中國近代革命的實踐中體會到馬克思主義理論要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生根開花,結出勝利的果實,就必須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湯老從對歷史上文化史的研究中,所得出的上述結論,不是也可作為一方面的借鑒,以提高我們進一步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自覺性嗎?
我對湯老的學術思想和成就,認識都還非常膚淺,時值湯老九十誕辰紀念,謹以此短文聊寄緬懷之情。
原載于《燕園論學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