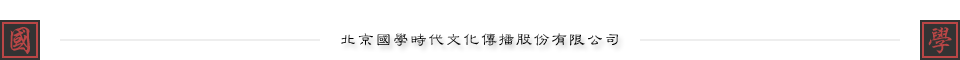有關(guān)新版《全宋詞》的幾個(gè)問題
內(nèi)容摘要:中華書局新近改版重印的《全宋詞》,在整體質(zhì)量上,確較舊版有所提高。但是,作一部廣為詞學(xué)研究者翻檢引用的學(xué)術(shù)名著,新版《全宋詞》仍存在諸多不盡如人意之處。筆者仿”《春秋》責(zé)備賢者”之例,從輯佚、考訂、校勘、檢索等四個(gè)方面,摘出新版《全宋詞》的某些可再完善之處,以期對(duì)這部詞學(xué)界的巨著盡一點(diǎn)綿薄之力。
關(guān)鍵詞:新版《全宋詞》;輯佚;考訂;校勘;檢索;再完善
作者簡(jiǎn)介:許雋超,男,1969年生,哈爾濱人。1996年6月畢業(yè)于哈爾濱師范大學(xué)中文系,獲文學(xué)碩士學(xué)位。現(xiàn)為哈爾濱師范大學(xué)中文系古代文學(xué)教研室講師。(哈爾濱師范大學(xué)中文系 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0)
1999年1月,中華書局出版了署名唐圭璋編纂、王仲聞參訂、孔凡禮補(bǔ)輯的新版《全宋詞》。新版合舊版《全宋詞》及孔凡禮《全宋詞補(bǔ)輯》于一編,采用簡(jiǎn)體字橫排,并把舊版附錄中已經(jīng)列出的排印、標(biāo)點(diǎn)、底本等方面的錯(cuò)誤,納入新版的相應(yīng)位置。中華書局編輯部暨孔凡禮等先生在校讀中又是正了有關(guān)的訛誤。關(guān)于新版《全宋詞》的學(xué)術(shù)含量,中華書局編輯部在書前的”改版重印說明”中認(rèn)為:”這樣,經(jīng)過全面修訂的改版重印的《全宋詞》,無論在整體質(zhì)量,還是在網(wǎng)羅資料上,都有明顯提高,版式也有了更新。希望它為學(xué)術(shù)界同仁及廣大宋詞愛好者提供更大的便利”。筆者近來對(duì)新、舊版《全宋詞》做了一番比勘,覺得這個(gè)評(píng)價(jià)是中肯的。但在比勘過程中,也偶爾窺見新版《全宋詞》的某些尚須完善之處。現(xiàn)擬分四個(gè)部分,將自己的一得之見寫在這里,以就正于新版《全宋詞》的修訂者及詞學(xué)界的師長(zhǎng)。
一、在輯佚方面。新版《全宋詞》的修訂者注意到了近年來發(fā)表在各種學(xué)術(shù)刊物上的宋詞輯佚成果,并把這些輯佚成果增添到新版中去。如《文史》第二十四輯(中華書局。1985)刊有孔凡禮先生的《宋詞拾零》一文,補(bǔ)《全宋詞》、《全宋詞補(bǔ)輯》所未收的龔端《畫堂春》及馮觀國《滿庭芳》,二詞被收入新版《全宋詞》第五冊(cè)后面所附的《全宋詞補(bǔ)輯》中。這也就是新版優(yōu)于舊版的地方。但網(wǎng)羅輯佚成果難免有遺漏之處。就筆者所看到的,《中華文史論叢》第五十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刊有李裕民《司馬光佚詞二首》,是李先生1992年1月在日本東京內(nèi)閣文庫翻閱傳世孤本《司馬溫公全集》時(shí)摘錄下來的,二詞是《西江月·河橋參會(huì)》、《中呂調(diào)踏莎行·寄致政潞公》。司馬光的詞作傳世本來甚少,新版《全宋詞》一仍舊版,只輯得《阮郎歸》、《西江月》(寶髻松松挽就)、《錦堂春》三首,不能不說是件憾事。
又如,《詞學(xué)》第九輯(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92)刊有施蟄存先生的《宋金元詞拾遺》一文,其中補(bǔ)輯舊版《全宋詞》未收詞作七首,計(jì)有李壁《滿江紅·同蔣洋州飲湖上》、《滿江紅·蔣示和篇余亦再作》,章概《蝶戀花》,無名氏《七娘子》二首、《滿江紅·詠雪梅》、《阮郎歸》。施蟄存先生的這些輯佚成果也被新版《全宋詞》的修訂者遺漏了。
二、在考訂方面。新版《全宋詞》在詞人生平事跡的考訂上,未能對(duì)舊版有較大突破,這就忽略了近些年來眾多學(xué)者在宋代詞人生平事跡考訂上所取得的成果。如李清照的里籍,《學(xué)林漫錄》八集(中華書局,1983)刊有褚斌杰等先生的《李清照里籍考》一文,以確鑿的史料考訂出李清照是濟(jì)南府章丘縣明水鎮(zhèn)人,這一考訂成果早已得到學(xué)界認(rèn)可,并被寫進(jìn)數(shù)種通行的高校文學(xué)史教材中。孫望、常國武主編的《宋代文學(xué)史》(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6),即著意標(biāo)出李清照是”濟(jì)南章丘明水(今屬山東)人”。莫礪鋒、黃天驥主編的《中國文學(xué)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也標(biāo)明李清照是”濟(jì)南章丘(今屬山東)人”,且未作任何解釋,見得是作為定論來使用的。而新版《全宋詞》同舊版一樣,仍以李清照為”濟(jì)南人”,這顯然是過時(shí)的、不確切的說法。又如,《文史》第四十輯(中華書局,1994)刊有方建新先生的《〈全宋詞〉小傳訂誤》一文,補(bǔ)訂舊版《全宋詞》內(nèi)86位詞人小傳中的某些疏誤之處,用力甚深。而這些言之鑿鑿的考訂成果,新版《全宋詞》卻無所取裁,不免令人遺憾。
三、在校勘方面。舊版《全宋詞》初以唐圭璋先生一人之力編定,繼以王仲聞先生的參訂及后來唐先生本人的修訂,詞句錯(cuò)訛之處仍在所難免。新版《全宋詞》雖經(jīng)中華書局編輯部暨孔凡禮等先生的審核修訂,亦不免留下些許遺憾。蓋校書如掃落葉,況《全宋詞》這樣一部三百多萬字的大書,宜乎其難也!以筆者翻檢所見,如晏幾道《訴衷情》(都人離恨滿歌筵)上片:”星屏別后千里,更見是何年”(新版第1冊(cè),第317頁)。”更見”,底本《彊村叢書》本作”重見”。晏幾道《醉落魄》(鸞孤月缺)上片:”信道歡緣,狂向衣襟結(jié)”(同上,第329頁)。”狂”,底本作”枉”。又如,吳潛《滿江紅·戊午秋半……》下片:”放兒童、今夜上青霄,探蟾穴”(新版第4冊(cè),第3504頁)。”兒童”,底本《彊村叢書》本作”兒曹”。三處均系誤排。蓋唐先生治學(xué)嚴(yán)謹(jǐn),但改動(dòng)底本,必出校記;而此三例處并無校記,顯系排印之誤。竊以為新版《全宋詞》照排舊版時(shí),似乎未能盡復(fù)核其所用底本也。在版本的比勘上,如李清照的名詞《聲聲慢》上片中的”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曉)來風(fēng)急”。此處向有”晚來”與”曉來”兩種版本。舊版《全宋詞》作”晚來”,這是事實(shí);但編纂者唐圭璋先生對(duì)此早已有所訂正。唐先生的《讀李清照詞札記》(原載《南京師大學(xué)報(bào)》1984年第2期,后收入唐先生的《詞學(xué)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其中有專條辨正此處作”晚來”之非、”曉來”之是,指出是延明人楊慎《詞品》之誤,并表示”必須從今改正,絕不能再以訛傳訛,厚誣清照”(見《詞學(xué)論叢》,第618頁)。新版《全宋詞》卻仍作”晚來”,故使唐先生晚年對(duì)《全宋詞》的修訂之功無從體現(xiàn)了。
四、在檢索方面。新版《全宋詞》把舊版第一冊(cè)前的總目次分排到每?jī)?cè)之首,這本無可厚非;但新版卻刪除了舊版第五冊(cè)后面的作者筆畫索引,舊版《全宋詞補(bǔ)輯》書前的目次及書后的作者筆畫索引也被刪除了。讀者若想查找某個(gè)詞人的作品,尤其是不太著名的詞人,只能把新版《全宋詞》每?jī)?cè)前的目次翻檢一遍,使用起來頗感不便。僅從作者檢索方面來說,新版《全宋詞》就不如舊版便捷。況且,與舊版《全宋詞》、《全宋詞補(bǔ)輯》配合使用的,還有高喜田、寇琪編的《全宋詞作者詞調(diào)索引》(中華書局,1992)。該索引不僅能檢索作者,而且藉某詞調(diào)及首句,便可知該詞確切的冊(cè)數(shù)、頁數(shù)。同時(shí),該索引采用四角號(hào)碼檢字法,使用起來十分便利。而這些便利,都是新版《全宋詞》所不具備的。一部高質(zhì)量的學(xué)術(shù)書,尤其是《全宋詞》這種帶有工具書性質(zhì)的學(xué)術(shù)書,附有內(nèi)容詳盡、檢索快捷的索引,應(yīng)該不是讀者對(duì)它的苛求。
鐘振振先生曾經(jīng)慨嘆其先師唐圭璋先生的《全金元詞》”校對(duì)不精,魯魚亥豕,俯拾皆是”,希望能”細(xì)細(xì)校改訂正”(見《文學(xué)遺產(chǎn)》1999年第3期,第7頁)。新版《全宋詞》的整體質(zhì)量雖然遠(yuǎn)高于尚未及修訂的《全金元詞》,但其可資完善的馀地仍是很大的。筆者之以偏概全,專意指瑕,實(shí)仿”《春秋》責(zé)備賢者”之例。蓋于《全宋詞》這樣一部廣為詞學(xué)研究者翻檢引用的學(xué)術(shù)名著,任何形式的求全責(zé)備,于其學(xué)術(shù)價(jià)值非但無損,相反地,只會(huì)有所增益。其業(yè)已確立的學(xué)術(shù)地位,在這些求全責(zé)備聲中,也會(huì)得到進(jìn)一步的證實(shí)。
以上是筆者就管見所及,在粗略比勘新、舊版《全宋詞》之后的一些想法。至于新版《全宋詞》在學(xué)術(shù)普及上的功績(jī),學(xué)界自有公論,本來就不是這篇小文所能夠承擔(dān)的,故而也就沒有多談。這是需要最后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