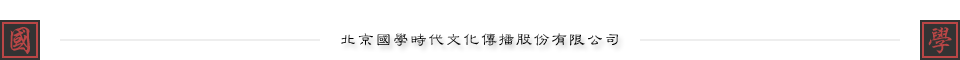追星也成學界風
眼下最為搶眼的是一幫明星,他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受到媒體與大眾的格外的關注,風頭之勁,不出緋聞的總統也無法與之爭鋒。而明星的耀眼,也并非自己真的有多少閃光之處,主要是有一大幫追星族寵著他們,讓他們找不著北了,于是便有某歌星的讓歌謎為其系鞋帶的狂態,便有某球星對球迷拳打腳踢的勇武亮相。對于少男少女的追星倒也無可厚非,因為他們正處在成長的年代,個性與自信都有待于完善,崇拜偶像可以幫助他們獲取奮斗目標并滿足心理的依賴感。
對于大眾中所流行的名人熱也不必驚詫,因為中國一向有崇拜偶像的傳統,這種偶像從龍鳳鳥獸演變為后來的祖先鬼神,再到政治權威,再到氣功大師,眼下又完成了與國際的接軌,開始崇拜各類名人。所謂名人,就是名字在媒介頻頻曝光的人,就是街頭巷尾、販夫走卒經常議論的人,就是可以恐嚇無知的幼童、在他們哭鬧時聽到一聲“你要再鬧,××就來了”就馬上乖起來的人,就是打拳時“動口不動手”、一下咬掉人半個耳朵的“君子”,就是學富五車、才高八斗的大師,就是德侔天地、道貫古今的圣人。名之一字,吸引力大得驚人。東晉桓溫慨言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要遺臭萬年,真是參透名之三昧的大智者。因為名的價值并不與善惡掛鉤,而在于在時空方面的普遍流傳,不論是什么樣的名,都能讓人獲得不朽,都能讓人由此得利。眼下進入知識經濟的時代,據說最重要的就是對眼球的爭奪,事實上也就是對名的爭奪,名與利既然更加直接地掛上了鉤,就無怪乎世風的轉向或者說是愈演愈烈了。
曾幾何時,這股風也刮到了學術界,于是又有一群科技明星、學術大師被包裝出來,成為萬眾注目的焦點與熱點,當然也出現了一群追星族,圍繞在大師的身邊,眾星捧月一般,成為學界特有的風景線。
畢竟學術界能稱為大師的人還不多見,于是僅有的幾位更是被奉為國寶,倍受關注,已逝的錢鐘書先生便是其中公認的一位。近來的報刊圍繞錢先生所作的文章多得難以數計,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僅僅出版家是否被錢先生會見過的就有好幾篇,先是有說范用于錢八十壽誕之日攜八十朵鮮花登門祝壽未被會見,后來又有人撰文說前說應為該打之假“精神產品”,范用確實被接見了,并有范與楊絳的合影為證,還稱前說“既作踐了范,又損傷了錢”,使錢有“不近人情”之嫌,近日又有人撰文,道是《范用確實未被錢鐘書會見》,是是非非,紛紜莫辨。
范用到底是否真被錢接見,其實并不重要,圍繞這一問題的聚訟也沒多大意思,有意思的是為什么會有這么多的人對這一問題如此感興趣。有道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人一旦成為名人,與之有關的一切都被加上了“名”作為定語,即便是極尋常的話,也成了“名言”,極沒意思的事,也成了名聞趣事。賣豆腐的老王是否“會見”了賣青菜的老李,想必無人去考證,如果有一天老王或者老李成了名流大款,成了社會賢達,這種過去無人過問的事馬上就會被發掘出來,說不定會有數不清的學者為此費盡腦汁地調查研究、臉紅脖子粗地爭論不休呢。
崇拜名人,想來是尊師重道的傳統再加上樹榜樣、立標兵的新風使然,倒也無可厚非。然而,如果從崇拜名人發展到崇拜與名人有關的一切,乃至名人的雞犬、名人的吐痰,就大可不必了。從崇拜名人再到按照私意拔高名人、架空名人,讓名人不食人間煙火,甚至有意作偽,把名人的一切缺點都給掩飾起來,把名人的瘡疤包裝成閃閃發光的亮點,就更讓人覺得惡心了。至于為抬高自己心儀的名人而將其周圍的一切都予以砍頭斷足,盡加貶損,對于針對名人的批評一概加之以“文雅”的污言惡語,恐怕就不能以崇拜名人為由了。
崇拜名人,當然是出于對名人的學問道德的仰慕,不過是否也有挾名人以自重、攀喬木以自升的心態,就只有崇名者自己清楚了。正是由于時下(古已有之)社會不僅有崇拜名流的習氣,還有崇拜近名者、衛名者之風,致使好名之士曲線救國,以奔走為榮,以圍繞為寵,以衛道為功,于是有出入某宅的名流,又有出入出入某宅的名流之宅的名流,有崇拜名人的名人,又有崇拜崇拜名人的名人的名人,世風如此,士風如此。
日月之為人所重,不僅由于其麗天之明,更由于其孤高。錢先生一向是以孤高自許的,并非愛好喧囂之輩。怎奈其孤高反成了媒介炒作的對象,眾人皆大談先生之如何孤高,如痛斥瑞典某諾貝爾獎委員會的漢學家,如美國某名大學以八萬美元聘其講學而被拒,這些未經完全證實的傳聞反而使先生的孤高流于熱鬧了。正是由于先生孤高,不喜交游,無暇交際,才更成為好名者獵取的首選目標,想方設法得近先生,如同追逐珍稀動物一樣。先生不輕許人,故登錢門如登龍門,稍受青睞,便頓有身價百倍之感。故略有瓜葛者,多有沾沾自喜、著書立說,惟恐人不己知之輩。難近門庭者,也大可推出“錢學”,以“知圣”自命。君子可欺之以方,孤高反成先生之病。若是錢先生來者不拒,一是沒有時間再做學問,只能成為徒有虛名的假學者,更重要的是恐怕真沒有人來了,因為再好的書法,一旦滿街上都是,就不值錢了。一旦孤高被人利用,成為閑人議論的談資,就會落入相反一途。以孤高自命的錢先生,晚年卻成為被追逐的學界明星,先生之幸乎,先生之悲乎?
浮云之趨逐,非日月之咎。時下的“錢學”,想來與先生本人毫無關系。只是一生不計名利的逝者,卻成為他人撈取名利的工具,沉醉于真學問的真學者,卻成為制造偽學問的偽學者的手段,真是可悲。試問錢先生何曾以精研“×學”得名,何曾以吹捧某大師飆升?真好龍者,何不效法先生之孜孜為學,何不效法先生之淡泊名利?偽“錢學”森則真“錢學”隱,鐘“錢”不如鐘“書”,崇拜名人不如自尊自重,等到為他之學休、為己之學興時,中國的學術才會真有希望。學術界的追星之風可以休矣。
原刊《粵海風》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