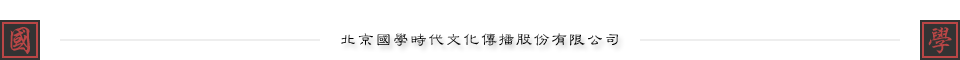唐衡岳大律師希操考
內容提要:希操為中唐時期南岳著名律師,一生度人無數。其弟子中有不少是禪宗大師,因此他與禪宗有不解之緣。弄清希操的史事,不僅有助于了解唐代南岳的律學傳承,對于理清藥山惟儼、丹霞天然、百丈惟政、興果神湊等人的師承與受戒時間也有所裨益。本文依據唐人碑傳等史料,對希操的名字、師承、生卒、傳人、等提出了一些假說。并肯定了他對律禪發展的貢獻。
關鍵詞:希操;律學;禪宗
中唐時期,律學頗盛,毗尼之中心也漸次南移,形成了“言律藏者宗衡山”(1)的形勢。其時南岳名德輩出,言律者眾,而希操律師德感天地,度人無量,非但挺出時輩,亦足垂范后世。世事滄桑,孰能料之!其后禪宗大興,言律者稀,雖當時之大德宗匠,亦不為后人所知,今之稍存其名,未全埋沒,也是由于其弟子中出了幾個禪門宗師,這恐怕也是希操本人始料未及之事。
禪史云藥山惟儼從希操律師受具,但語焉不詳,名或乖誤,《祖堂集》云是惟儼“大歷八年受于衡岳寺希澡(今本稍有漫漶,但亦可辨認出確為’澡’字)律師”,《宋高僧傳·惟儼傳》亦云其年“納戒于衡岳寺希澡律師所”,《景德傳燈錄》則稱受戒于希操律師(《五燈會元》同),唐伸《澧州藥山故惟儼大師碑銘》道是“受具于衡岳希琛律師”,令學者無以為從。因讀白樂天集,見其中有《唐江州興果寺律大德湊公塔碣銘并序》,其云神湊“具戒于南岳希操大師”,疑當以希操為正。又覽柳河東集,睹《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驚喜莫狀,始知柳宗元早已為之作碑,唯后人不知耳。
據《塔銘》,希操俗姓昝,春秋五十七,僧臘三十一,臨壇度眾二十六會,為南岳著名律師。只是柳宗元未曾明述其生卒之年,但言“既沒二十七年,弟子誡盈奉公之遺事,愿銘塔石”。因此只要能夠確定《塔銘》作于何年,就可弄清希操的生卒時間。
蘇東坡云: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諸碑,妙絕古今。(2)其言柳宗元南遷之后,始作釋氏碑銘,真不刊之論!只是道柳宗元南遷之后,始究佛法,與其自述不合,子厚《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稱“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 …于零陵,吾獨有得焉”,故不如說“子厚南遷,始明佛法”。
柳宗元因參與王叔文、王伾等永貞元年(805)進行的改革,于其年九月以黨人出為邵州刺史,十一月于途中又被貶為永州(今湖南零陵縣)司馬,在永州十年,元和九年(814)十二月召赴京師,旋又出為柳州刺史,元和十四年(819)十月卒于柳州,終年四十七歲。
因此柳宗元作此《塔銘》應在元和元年(806)至永州之后,元和十四年(819)去世之前。又柳宗元所作南岳諸碑,悉撰于在永州時,這也是由于南岳與永州同處湖南,為永州與京師往來必經之地,其可考者,最早作于元和三年(809),最遲作于元和九年(814)。
據此《塔銘》當作于元和三年到元和九年之間,這也是合乎情理的。當其初到永州之時,樂極生悲,折羽青云,遭此巨變,驚魂未定,自然郁郁于懷,無心旁務,此時也不會有人不知趣地請他來寫碑銘。待至二三年后,寓情山水,究心釋教,愁眉漸解,憂懷稍開,故始為釋氏大師作碑。南岳地近永州,名德輩出而斯文罕覓,一聞謫仙降此,故諸人競相邀請,欲令先師之名垂于千古,故其南岳諸碑皆作于此時也。
再從柳集的編次及碑文的內容來看,此《塔銘》應當作于元和九年(814),為其永州釋氏諸碑最后之作。柳集版本很多,最早為劉禹錫所編三十卷本,今已不存,現存本最古者為宋穆修發現并校刊的四十五卷本,題為八九大編,此雖非劉編原本,但卷次之別只是詳略巨細不同,去之未遠,其將此文列于釋氏諸碑之末,《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之后,或有其故。今本將柳集釋氏碑銘分為兩卷,其中卷六大抵是按傳主的名聲和影響排列,故首列大鑒惠能,卷七則大概是依碑文創作的時間排列,故最后是希操《塔銘》。
假定此文作于元和九年(814),則希操應生于開元二十年(732),卒于貞元四年(788),乾元元年(758)受具。其住錫之地應是衡岳寺,《塔銘》稱“南尼戒法,壞而復正,由公而大興;衡岳佛寺,毀而再成,由公而丕變”,表明他有重建衡岳寺之功,這也與《祖堂集》等所述一致。所謂南方毗尼之法,壞而復正,大概是指因安史之亂,天下擾攘,南岳傳戒活動亦為之廢頓,希操對于恢復戒律的傳授有所貢獻。這也表明他很早就開法度人了。
《塔銘》舉出兩人來證明希操的佛學成就和地位,一是作為在世之士的鄴候李泌,一是作為出世之士的高僧懶瓚。李泌對希操尊禮有加,望之而稽首,尊之而不名。懶瓚言不輕出,對希操卻贊嘆不已,以護法視之。二人皆居于衡岳寺側近,亦可證明希操確實為衡岳寺主。
李泌封候拜相,自不待言,懶瓚也是一位在南岳很有影響的高僧。據《南岳總勝集》卷下,懶瓚本號懶殘,唐天寶初衡岳寺的執役僧,性懶而愛食人殘食,故以此為號。他苦節為務,晝專一寺之工,夜與群牛同止,如此積二十年,未嘗倦怠。時鄴候李泌亦在寺中讀書,聞其中宵梵唱,知非凡物,通名謁見,卻遭到唾罵。李泌愈加禮敬,懶瓚見其心誠,便取己食芋之半授之,李泌不以為忤,盡食之。懶瓚言道: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后李泌果拜相。
這位懶瓚禪師顯然是一個遁世的高士,《南岳總勝集》謂其本號懶殘,后世訛為懶瓚,未必果是。據《景德傳燈錄》,普寂有弟子明瓚禪師,不知是否其人,按其天寶初居于衡岳,倒有可能。又據《宋高僧傳·唐南岳山明瓚傳》,可知明瓚確系懶瓚。但據現存的《景德傳燈錄》卷三十所收之《懶瓚和尚歌》,其人卻似應出自南宗一系。如云“向外覓功夫,總是癡頑漢”、“本自圓成,不勞機杼”,更說“饑來吃飯,困來即眠,愚人笑我,智乃知焉”,似是六祖后輩嘴邊常語。若此非后人添加,則懶瓚當與六祖一派亦不無關系,這也許是由于懶瓚長住南岳,其思想禪法也受到住錫此山的懷讓等人的影響。
希操既然能得到李泌、懶瓚兩大高士的禮贊,足以證明其道果。《塔銘》更示其宗系,道是“凡所受教,若華嚴照公,蘭若真公,荊州至公、律公,皆大士;凡所授教,若惟璦、靈干、惟正、惠常、誡盈,皆聞人”。
其中所述希操從學過的大士,只有蘭若真公后世有傳,亦即《南岳彌陀和尚碑》中提到的玉泉真公。據李華《荊州南泉大云寺故蘭若和尚碑》,真公名惠真,俗姓張,年十三出家,隸西京開業寺,為高僧滿意弟子,后當陽弘景律師授以大法,并表請以他為首的京輔大德十四人同住南泉,天寶十年(751)卒,春秋七十九,僧夏六十。惠真接天臺、律宗兩家傳承,其師當陽恒景亦然,恒景初就文綱律師習律,又入玉泉寺習天臺止觀法門,文綱則為道宣上足。惠真則一方面為相部宗滿意弟子,一方面又是天臺宗恒景高足。
至于華嚴照公,則不知何指。與希操前后同時名為照的高僧甚多,如舒州法照、南岳日照、西山慧照、梁漢法照、西明圓照、南岳神照等,不知《塔銘》所述是按受教先后之次第、還是諸師年臘德望之高低,若是前者,則舒州法照(五祖弟子)、南岳日照(普寂弟子)、西山慧照(懷讓弟子)、西明圓照(貞元十年794后卒)、梁漢法照(大歷十二年777后卒)、南岳神照(神秀法孫)都有可能,若依后者,則只有舒州法照年德高于蘭若惠真。舒州法照事跡不詳,《景德傳燈錄》謂其為五祖弘忍弟子,五祖卒于咸亨五年(674),假設其年法照二十,則其應生于永徽六年(655),至天寶十年(751)已九十七歲,即便希操十五歲(746)從之受學,他也已經九十二歲了。但這種可能性不能排除,禪者多壽,九十多歲也不算稀奇。若依受教次第,其為南岳日照或南岳神照的可能性最大。梁漢法照在南岳住止未久,且無論如何,不應列于其祖師真公之前。希操所受教之人,皆在荊州,可見其求學范圍。日照為普寂弟子,明瓚同學,從年德、輩份上說可為希操之師。神照為南岳元觀之徒,亦是神秀法孫,其年德也有可能先于希操。然據《宋高僧傳》卷九,其云南岳東臺元觀太和四年(830)遷塔,春秋七十九,則其應生于天寶十一年(752),非但無緣從學于神秀,就連為普寂弟子也不可能。不知是僧傳記載有誤,還是禪史移后為前,其師事跡不明,神照的生平真偽也難下結論。
荊州至公無考,遍查諸書,不見其名。而荊州律公,也未見諸僧傳,惟《南岳總勝集》卷中云衡岳寺“有唐皇甫湜撰璦律禪師碑,連州刺史王詡書”,此璦律禪師或許就是荊州律公。皇甫湜與柳宗元同時,也是著名文人,有《祭柳子厚文》,劉禹錫《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稱皇甫 “于文章少所推讓”,獨和韓退之之說,以其文可比司馬子長。
文中提到的希操諸大弟子,雖為當時之“聞人”,今卻一無可考。倒是未曾提及的興果神湊、藥山惟儼等弘揚禪律,名在后世。
據白居易《唐江州興果寺律大德湊公塔碣銘并序》,興果神湊(744-817),俗姓成,號神湊,京兆藍田人。“具戒于南岳希操大師,參禪于鐘陵大寂大師。志在《首楞嚴經》,行在《四分毗尼藏》。”大歷二年(767)受具,大歷八年(773)應經、律、論三科策試,中等得度,詔配江州興果寺。后移居東林寺遠公舊道場。元和十二年(817)九月入滅,春秋七十四,僧臘五十一。臨壇度人垂三十年,領羯磨會十三,化眾萬人。弟子有道建、利辨、元審、元總等。
神湊大歷二年從希操受具,這表明其年希操已經開法度人了,如此他臨壇度眾的時間至少有二十二年(767-788)。神湊的律學主要來自希操,既然神湊專行四分律,希操所行也不外如是,這也符合自道宣至文綱、弘景、惠真的南山宗傳承。神湊臨壇近三十年,于會十三次,度人萬數,希操掌律度眾二十六會,自然“受學之眾,他莫能偕也”。
興果神湊為當時著名的律師,《撫州景云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銘》稱上弘(739-815)與“匡山法真、天臺靈裕、京門法裔、興果神湊、建昌慧琎五長老交游”,可見當時神湊在律宗中的地位。白居易也對神湊崇禮有加,與之一見如故。因此神湊盡管“心行禪,身持律”,兼秉希操和馬祖兩派傳承,但他還是以律為主,堪為希操律學的傳人。
如果說神湊兼秉禪律而以律為主的話,那么藥山惟儼則與之相反。惟儼大歷四年(769)從希操受具,以為“大丈夫當離法自靜,焉能屑屑事細行于衣巾耶”,于是轉事馬祖,欲求心法。但是藥山盡管以禪為主,還是保持著持戒精嚴的習慣,大布為衣,山蔬佐食,坐禪轉經,終始如是。這也許與希操的教導有關。
除神湊與藥山外,丹霞天然(739-824)也可能出自希操門下。《宋高僧傳》云天然先謁石頭,三年落發,“后于岳寺希律師受其戒法,造江西大寂會”。此岳寺當為衡岳寺,或謂“后于嵩岳寺希律師受戒”(3),恐誤。天然既于南岳石頭處落發,自然會在本地受具,不必遠至嵩岳,其造大寂會也是從南岳直趨江西,非是由自北方。此希律師當為希操之誤脫,當時衡岳寺只有希操律師,并無其他名為“希”的律師。天然受戒的時間不詳,《祖堂集》云其本為秀才,與龐居士一起赴京應試,欲得選官,后為一客啟發,以為選官不如選佛,便到江西參馬祖,馬祖令其至石頭處出家,在石頭三年,后石頭為之披剃,其后至衡岳寺受具。若其二十歲時應舉,加上往來參學,道途耽擱,則其最早應在二十四歲時受具,亦即寶應元年(762),希操于乾元二年(758)受具,其時也有可能已經開法。
天然、神湊、藥山三人都是先從希操受具,然后再去參禮馬祖,這也許表明懷讓一派在道一離開之后仍然在南岳有著很大的影響,希操或多或少受其浸潤。希操或許未及從懷讓受學,但他肯定會受到懶瓚的影響,對于禪宗宗風有所了解。《塔銘》對其思想述之不多,唯道其“與物大同,終始無爭”,至人無我,故和光同塵,與物無違;自性自足,無欠無余,無待于物,故任心自在,與物無爭。
南岳為中唐毗尼中心,名德輩出,與希操先后同時傳戒度人者有彌陀和尚承遠(712-802)、云峰和尚法證(724-801)、大明律師惠開(733-797)、般舟和尚日悟(739-804)等。其中彌陀承遠算是他的師兄,二人同學于蘭若惠真。盡管希操在諸師中壽命最短,法臘不長,但他占據南岳中部的位置,能夠在不太長的時間內領法會二十六度,因此度人數量最多,這也是十分難得的。
希操享壽不永,卒少顯嗣,故不見后世史傳。非但《宋高僧傳》不見其傳,《南岳總勝集》亦未稱其名。但是飲水思源,他對南岳禪律的傳播還是有一定貢獻的,不可輕易埋沒。
注釋:
(1)劉禹錫《唐故衡岳大師湘潭唐興寺儼公碑》,引自《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第二卷第四冊,中華書局1983年版。
(2)《蘇軾文集》第五冊2084頁《書柳子厚大鑒禪師碑后》,孔凡禮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版。
(3)杜繼文、魏道儒《中國禪宗通史》276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原刊《船山學刊》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