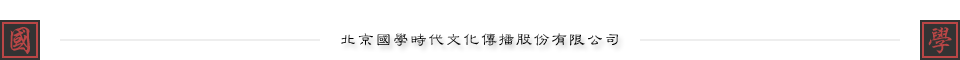牟宗三與康德哲學(xué)散論
五、講透知性的邏輯性格
牟宗三后來對《認(rèn)識心之批判》作了自我批評,在重印志言中,他說:“經(jīng)過近三十余年來中西兩方面之積學(xué)與苦思,返觀《認(rèn)識心之批判》,自不免有爽然若失之感。最大的失誤乃在于那時(shí)只能了解知性之邏輯性格,并不能了解知性之存有論的性格。”
然而,“知性之邏輯性格”是非講透不可的,否則,康德哲學(xué)的革命性便不顯。一般人若是未經(jīng)有意識的哲學(xué)思考訓(xùn)練,總難免實(shí)在論的心態(tài)很嚴(yán)重。康德哲學(xué)的革命意義即在于,它能直截了當(dāng)?shù)嘏まD(zhuǎn)入的實(shí)在論心態(tài)。依康德說,時(shí)間空間是人的先天直觀形式:并非外在的事物本身有時(shí)間性空間性,而是人的認(rèn)識機(jī)構(gòu)之一部分(直觀)把時(shí)空形式加于外物;因果性等等是人的先天知性范疇:并非外在事物相互間本來就有因果聯(lián)系,而是人的認(rèn)識機(jī)構(gòu)之另一部分(知性)把因果范疇加于外物。人好象從娘肚子里出來就戴著一副有色眼鏡:并非世界萬物都有某種顏色,而是透過眼鏡我只能把世界萬物看成某種顏色。說桌子的邊緣是直線,等于是說我把它們看成直線;說兩事物甲為因乙為果,等于是說我把它們看成因果。生活中的有色眼鏡,可以戴上,也可以脫掉;而從娘胎里帶出來的直觀形式、知性范疇,卻好比永遠(yuǎn)脫不下的有色眼鏡。這就使人們誤以為世界本身有某種顏色,從而陷入實(shí)在論的迷夢。康德哲學(xué)如一聲霹靂,驚破人類的千年迷夢。
在康德的哲學(xué)里,人類的知識是就現(xiàn)象界、經(jīng)驗(yàn)界而談。這種知識分成“經(jīng)驗(yàn)的”與“先驗(yàn)的”兩方面,但知識全體并不能看作“先驗(yàn)的”與“經(jīng)驗(yàn)的”兩部分的”拼盤,似乎中間可以有一條明確的界線,可以看得到“先驗(yàn)知識”與“經(jīng)驗(yàn)知識”的單獨(dú)存在。不是的!“先驗(yàn)知識”和“經(jīng)驗(yàn)知識”這兩部分總是有機(jī)地結(jié)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難分難解。
當(dāng)然,也不能說“經(jīng)驗(yàn)的”那部分構(gòu)成對象,為“所知”;“先驗(yàn)的”那部分構(gòu)成主體,為“能知”。“所知”的成立,在這里也需要“能知”的參預(yù),在認(rèn)識的對象上,也是“能所不分”的。說得準(zhǔn)確些,先驗(yàn)的直觀形式和知性范疇不僅參予形成知識,更參預(yù)形成知識的對象。舉例說,我們看到一個(gè)桌子,并知其為桌子,(此“知”包含許多內(nèi)容,如知其形狀[空間形式],知其新舊[時(shí)間形式],知其來歷與用途[因果范疇等等],康德所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我人認(rèn)識機(jī)構(gòu)先天具有的那些形式、范疇,不僅是關(guān)于桌子的知識的條件,而且也是作為經(jīng)驗(yàn)對象的桌子的條件。一言以蔽之,“經(jīng)驗(yàn)可能的條件,即是經(jīng)驗(yàn)對象可能的條件”。(在這個(gè)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沒有認(rèn)識的先天機(jī)構(gòu),也就沒有桌子的存在。這好象頗有貝克萊“存在即是被感知”的唯我論味道,但兩者有本質(zhì)的不同,要須在論證推演中分辯清楚,康德所以難讀之故,于此可見一斑。)
所謂“知性的邏輯性格”,就是強(qiáng)調(diào)了這一面,此處“邏輯的”一詞,是在與“實(shí)在的”一詞為對的意義上使用的。強(qiáng)調(diào)知性的邏輯性格,就是與為常識所擁護(hù)的實(shí)在論唱反調(diào)。康德知識論的這一革命面,得到了現(xiàn)代科學(xué)特別是理論物理學(xué)的充分支持。在物理學(xué)中,人們不能談?wù)撐镔|(zhì)基礎(chǔ)(例如光子)本質(zhì)上是“波”,還是“粒子”。粒子也好,波也好,都是在實(shí)驗(yàn)、觀察、理論的參予下形成的。同為光子,在如此這般一套實(shí)驗(yàn)裝置、觀察程序、理論解釋下,它是粒子;在如彼那般另一套實(shí)驗(yàn)裝置、觀察程序、理論解釋下,它又是波。說“物質(zhì)是波與粒子的對立統(tǒng)一”,這不過是用辯證法來變戲法,一點(diǎn)兒幫不了忙,一絲毫未增加點(diǎn)新知識。N·波耳說得好:“我們可以讓釘子固定,也可以讓釘子松動,但是我們不能讓釘子既固定又松動”。近代物理學(xué)大家關(guān)于理論與實(shí)在關(guān)系問題的哲學(xué)表態(tài),幾乎一面倒,倒向康德而不取實(shí)在論;這類言論俯拾皆是,例如,堪稱活著的愛因斯但的斯蒂芬·霍金就毫不客氣他說:“在科學(xué)的哲學(xué)方面很難成為實(shí)在主義者,因?yàn)槲覀冋J(rèn)為實(shí)在是以我們所采用的理論為前提”,“沒有理論我們關(guān)于宇宙就不能說什么是實(shí)在的”,“問理論是否和實(shí)在相對應(yīng)沒有任何意義,因?yàn)槲覀儾恢朗裁词桥c理論無關(guān)的實(shí)在。”
現(xiàn)代物理學(xué)在強(qiáng)力支持康德認(rèn)識論的同時(shí),對之也稍稍有所修正:“觀察者參預(yù)形成觀察對象”,此無異議,但現(xiàn)在“觀察者”不僅僅是一個(gè)“知性我”,觀察者除了“先天地配備從娘胎里帶出來的全套直觀形式、知性范疇,而旦還被數(shù)學(xué)概念、物理理論、實(shí)驗(yàn)工具武裝著。與經(jīng)驗(yàn)實(shí)在相對應(yīng)又成為經(jīng)驗(yàn)實(shí)在之條件的內(nèi)在化的先天認(rèn)識機(jī)構(gòu),其邊界已大大向外擴(kuò)充;而認(rèn)識主體先于客體并且開出客體這一康德認(rèn)識論的要旨,也因此擴(kuò)充而更加鮮明、凸顯。不妨想像,在另一個(gè)星球上有比人類更高級的智能動物,它們的先天的認(rèn)識機(jī)構(gòu)中已包含著地球上人類經(jīng)過千萬年歷史才發(fā)明出來的那些認(rèn)識工具:數(shù)學(xué)概念、物理理論、實(shí)驗(yàn)儀器等,在那里,復(fù)雜精致的量子力學(xué)象因果范疇一樣,是從娘肚里帶出來不學(xué)而能的“知性形式”,人人都是天生的物理學(xué)家,白癡也不例外,想忘記也忘不掉。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現(xiàn)代科學(xué)具有一種與“實(shí)在論的”相對立的“邏輯的”性格。
細(xì)繹康德原文,和王國維十分推崇的叔本華的述康(《康德哲學(xué)批判》一文),以及王國維本人的再述,關(guān)于“邏輯的”一詞,有一個(gè)重要的區(qū)別必須強(qiáng)調(diào)提出,即,在與“存有論的”(或“實(shí)在的”)相對立的意義上使用,跟在與“綜合的”相對立的意義上使用,兩者完全不同。前一種意義上文已論及,茲請說明后一種意義。與“綜合的”相對立,“邏輯的”一詞有分析的、同義反復(fù)的意思,它常常指“套套邏輯”(tautologY)的形式和規(guī)則.“人皆有死,蘇格拉底是人,故蘇格拉底有死”,是它的典型例子,“一個(gè)命題與它的否定不能俱真”(矛盾律)曾是它的中心規(guī)律。符號邏輯早就把所有套套邏輯的規(guī)律一網(wǎng)打盡,畢其功于一役地收羅進(jìn)一個(gè)簡單的公理系統(tǒng)。這種意義上的邏輯只能行于命題,不能行于感性事實(shí)材料,行于命題也只能起安排整理的作用,不能導(dǎo)出原則上為新的命題。
然而,自從歐幾里得幾何以來,兩千多年間,邏輯的地位和作用一直被不適當(dāng)?shù)乜浯罅恕VR應(yīng)該具嚴(yán)密性、精確性,而歐氏幾何不愧為知識嚴(yán)密性精確性的典范,似乎一切知識都應(yīng)該向它看齊,似乎不能象它那樣編織成系統(tǒng)的知識便不成熟,而歐氏幾何之所以能致此者,端賴于邏輯的功效。古典理性主義錯(cuò)誤的一個(gè)重要根源就在于這種對于歐氏幾何的錯(cuò)誤的哲學(xué)詮釋上。這種錯(cuò)誤的看法至今猶在淺學(xué)的人中有著根深蒂固的影響,簡直成了教條。康德《純理批判》(以及《未來形而上學(xué)導(dǎo)論》)所要完成的一個(gè)任務(wù)就是反對這樣的“邏輯主義”。他要證明,人的認(rèn)識以先天直觀形式和先天知性范疇行于感性材料以產(chǎn)主知識,是一個(gè)“綜合”的過程,而不是分析的邏輯演繹的過程。他在討論“形而上學(xué)如何可能”、“物理學(xué)如何可能”、“數(shù)學(xué)如何可能”等問題時(shí),反復(fù)辯稱真理的“綜合性”,即使象5+7=12這樣簡單至極的算術(shù)真理,它亦不是單純的狹義的邏輯分析所能達(dá)到的。人的實(shí)際的認(rèn)識過程包括諸多因素,邏輯的、歸納的、類比的、猜測的、直覺的,甚至詩意、激情、夢幻、迷亂、變態(tài)心理,都能起積極作用,“邏輯的”則肯定不在其中居主導(dǎo)地位。康德把這一點(diǎn)辯證得十分清楚了,科學(xué)的后來進(jìn)展每能具體地示證康德爾的先見之明。例如對初等算術(shù)的皮亞諾改制顯示算術(shù)的核心在于囊括無限個(gè)三段論式的“數(shù)學(xué)歸納法”,遠(yuǎn)遠(yuǎn)越出了邏輯之所能為,康德關(guān)于算術(shù)定理也是“綜合判斷”的哲學(xué)論證,徑可以作皮亞諾算術(shù)系統(tǒng)的前驅(qū)。數(shù)學(xué)當(dāng)然是邏輯性最強(qiáng)的科學(xué),但只要是創(chuàng)造性的數(shù)學(xué)家,他入乎其內(nèi),深嘗過研究工作的個(gè)中三味,當(dāng)他出乎其外,談?wù)勥@種工作的性質(zhì)時(shí),他決不會把創(chuàng)造發(fā)明的關(guān)鍵歸于邏輯推理,邏輯推理只在關(guān)鍵步驟已經(jīng)完成,需要作整理、安排、表達(dá)時(shí)才起作用。特別重視數(shù)學(xué)邏輯性的,往往是那些傳授現(xiàn)成知識的數(shù)學(xué)教師,和那些人云亦云的“哲學(xué)家”,而不是實(shí)干的數(shù)學(xué)家。
康德在“邏輯的”與“綜合的”兩者間所作的辯證,為叔本華和王國維所深契。王國維《叔本華的哲學(xué)及其教育學(xué)說》一文中述及康德之處,即以歐幾里得幾何所體現(xiàn)的“理性主義”(意指邏輯主義)為話題,從康德的觀點(diǎn)作批判的考察。歐氏結(jié)撰其幾何原本時(shí)的意向很明確:不信直觀,偏信邏輯,故力求對直觀的依賴(公理)越少越好,減之又減,只剩幾條實(shí)在無可歸并者,才任它們依于直觀,其余則統(tǒng)統(tǒng)交給邏輯。歐氏幾何整體結(jié)構(gòu)所暗示的教訓(xùn)即為:只有邏輯是可靠的,屬理性;直觀屬經(jīng)驗(yàn),所以不可靠。欲識破此種邏輯主義,關(guān)鍵在于能象王國維那樣,抓住康德辯證中的一個(gè)重要區(qū)分:“經(jīng)驗(yàn)的直觀”與“純粹的直觀”。
王國維寫道:“吾人由理性之作用而知五官及悟性固有時(shí)而欺吾人,如夜中視朽索以為蛇,水中置一棒而折為二,所謂幻影者是也。彼等但注意于此以經(jīng)驗(yàn)的直觀為不足恃,而以為真理惟存于理性之思索,即名字上之思索,此唯理論與前之經(jīng)驗(yàn)論相反對。歐幾里得于是由此之立腳地以組織其數(shù)學(xué),彼不得已而于直觀上發(fā)見其公理,但一切定理皆由此推演之而不復(fù)求之于直觀。然彼之方法之以風(fēng)行于后世者由純粹的直觀與經(jīng)驗(yàn)的直觀之區(qū)別未明于世”。在康德的意思,純粹的直觀也有理性的根源,(惟當(dāng)其欲對此作根源的說明時(shí),因論證方式過于邏輯化而碰到困難([二律背反],此為后話)理性一名,非套套邏輯可以所得而私。邏輯形式雖亦行于真理之域,真理的內(nèi)容卻非其所能探及。王國維喻歐氏幾何的結(jié)撰方式:“如觀魚龍之戲,但示吾人以器械之種種作用而其內(nèi)部之聯(lián)絡(luò)及構(gòu)造則終來之示也”。此喻極其形象又極其深刻,它昭示,任何真理內(nèi)容的表達(dá),都是綜合判斷。
在此不妨作一個(gè)有趣的科學(xué)史注記。因非歐幾何出來,有人就嚷嚷,康德的認(rèn)識論被駁倒了。非歐幾何與歐氏幾何是兩套互相矛盾的理論體系(各自內(nèi)部并無矛盾),如果幾何公理表達(dá)先天的直觀形式,那么,先天直觀怎么會帶出兩套互相矛盾的形式呢?其實(shí),要是這些人能夠象叔本華、王國維那樣,對于康德早就做出的“經(jīng)驗(yàn)的直觀”之于“純粹的直觀”之區(qū)分,有深刻的體會的話,就不至于這么嚷嚷了。康德好象是預(yù)見到會有高斯、羅巴切夫斯基這班人出來搞非歐幾何,竟早就預(yù)為之備,作好了這一區(qū)分以待之。歐幾里得的第五公設(shè)與羅巴切夫斯基的平行公理;都不是純粹直觀,而是經(jīng)驗(yàn)直觀,只因?yàn)榈谖骞O(shè)容易在經(jīng)驗(yàn)上直觀到,羅氏幾何的平行公理則很不容易從經(jīng)驗(yàn)上直觀到,所以兩者雖然邏輯上有同等的地位,歷史上的出現(xiàn)卻相隔兩千年。
總而言之,先天直觀形式、先天知性范疇,這些是康德對人的認(rèn)識機(jī)構(gòu)所作的概念上的把握,處于不同經(jīng)驗(yàn)和歷史狀況中的人,將有不同的表現(xiàn),有些也未必能實(shí)存地表現(xiàn)得出來,需要“開”。這些直觀形式、知性范疇全套立在那里,就形成所謂“知性我”(主體)。知性主體與經(jīng)驗(yàn)對象既相對待又參予形成經(jīng)驗(yàn)對象,這樣的一種性質(zhì)牟宗三名之曰“邏輯性格”!《認(rèn)識心之批判》的重心即在解明這一性格。怎樣命名是無所謂的,要在于這一性格集中表現(xiàn)了康德哲學(xué)的革命性。但因命名可能引起混淆,故就“邏輯的”一詞可以有與“存有論的”相對之義,以及與“綜合的”相對之義兩義,特疏明之如上。
六、落實(shí)知性的存有論性格
談到知性的存有論性格,其實(shí)在《認(rèn)識心之批判》里,已經(jīng)有過精彩而深刻的提示。所謂“知性的存有論性格”是說知性接物所成之現(xiàn)象非為一虛象,而有其堅(jiān)實(shí)的本體;“現(xiàn)象的本體”,這也是康德的術(shù)語。牟宗三說:“康德以本體為范疇之一,……他欲建立本體一概念之客觀妥實(shí)性,……關(guān)此問題,康德一套說統(tǒng),每步皆極困難。”而在牟宗三看來,康德這套說統(tǒng)所建立的是“全體現(xiàn)象宇宙之彌漫體”,而不是“個(gè)體之持續(xù)體”因此康德說現(xiàn)象的本體“過多面過高,不能盡現(xiàn)象本體之職責(zé)”。好比做衣服,所有一切衣服的“本體”(原料)都是棉花,但每一件衣服各有它自己的“本體”(特殊的面料)。牟宗三堅(jiān)持認(rèn)為“現(xiàn)象的本體”須克就“個(gè)體性的本體”為言,譬之做衣服,它的原料須克就各別恃殊的布料為言。“吾自始即想自個(gè)之為個(gè)而明之,自個(gè)之為個(gè)而言本體”。為此目的,牟宗三須“別取一途徑。單注意于生理機(jī)體中心中之生起事及其意義之客觀化”,“承認(rèn)生理感中心中之生起事之實(shí)際性及堅(jiān)強(qiáng)性(亦帶有頑梗性).吾人單須就此而客觀化即足,客觀化之使其脫離生理機(jī)體及心覺觀點(diǎn)此而客觀化之即是,客觀化之使其脫離生理機(jī)體及心覺觀點(diǎn)而有客觀而公共之意義。吾人在此客觀化中,決定出個(gè)體之為個(gè),個(gè)體之統(tǒng)一。”康德所建立之“全體現(xiàn)象宇宙之彌漫體”,嚴(yán)格地說,乃是“形上的本體”,而非)現(xiàn)象的本體”,好比對于裁縫來說,棉花是他做衣服的“形上的原料”而不是“當(dāng)下的原料”,當(dāng)下的原料乃是布。
與后來《現(xiàn)象與物自身》不同,《認(rèn)識心之批判》的基本順序仍是“上講”,即從下往上講.牟宗三分“心”為三個(gè)層次:1.“生理感中心”;2.認(rèn)識心;3.形上心。“生理感中心中之生起事”,不僅人能有,動物亦有,人所異于動物者,是由“心覺”行于“生理感中心”之中而成“認(rèn)識心”。有心覺存于官覺之中為其主,故而能行直覺之事;直覺者,覺事,覺事之意義,其中包括事之因果,故因果亦有直覺的確定性.在康德,知性我是由若干形式范疇搭起來的間架:而在牟宗三,則認(rèn)識心為“生理感中心”因心覺提升(緣心覺爬升)而成者。
“心覺”云何?可以說這是整部《認(rèn)識心之批判》的總綱,其第一卷為“心覺總論”以后各卷乃是依心覺展開為認(rèn)識心之方方面面。對于“心覺”一詞,實(shí)無法用三言兩語定義、解釋,須通全書之旨而后能完備并定住其含義。
形上心之自體明覺,也是一種心覺,故認(rèn)識心不僅可以由“生理感中心”緣心覺爬升而成,亦可以由形上心之“坎陷”而成。形上心之“覺物”、“知物”,必非邏輯意義上的覺知,而是本體意義上、存有論意義上的覺知,各種覺知,必不假形式、范疇而行。《認(rèn)識心之批判》一書實(shí)際上已經(jīng)為沿著“下講”(從上往下講)的方向揭示知性的存有論性格,開了端緒。“認(rèn)識心之靜處而與物對……。吾人將溯其源于形上的心之坎陷。”這大概是用易經(jīng)中“坎陷”一詞來說認(rèn)識心之根源的第一次出現(xiàn)。曾聽牟先生早年的學(xué)生傅成綸先生說:“牟先生寫《認(rèn)識心之批判》時(shí),我正隨侍在側(cè)。有一天他對我說,昨夜興奮得一夜不眠,躺在床上輾轉(zhuǎn)反側(cè),想通了一個(gè)問題,即形上心坎陷而為認(rèn)識心。”
用形上心坎陷而成認(rèn)識心來說因果律之必然性,是《認(rèn)識心之批判》中極其精彩的一段大文章。依常識,固果律自身即是一種必然性,這與邏輯律自身即是一種必然性,差可比擬。但牟宗三所欲重言者,不是這種必然性,而是理性根據(jù)上的必然性。處于因果倫系、邏輯網(wǎng)絡(luò)中的必然性,乃是一種平鋪的展開,委順的演化,屬于呈現(xiàn)原理,不屬于實(shí)現(xiàn)原理。牟宗三則要將必然性立體化,要“獲得其所以呈現(xiàn)之理由,即獲得其理性的必然性。而彼理由亦即吾人所說之實(shí)現(xiàn)原則”。橫向的平鋪的因果關(guān)系,無論在直覺層面,還是在知性層面,都不能植立其必然性的根據(jù),盡管它自身是一種必然性。牟宗三說:“凡言必,皆通于理性之根據(jù)而言。若無理性之根據(jù),縱事實(shí)上有矣,亦不得說必。事實(shí)上有而不必,此‘不必’單指無理性根據(jù)言,不指其結(jié)果在此時(shí)此地出現(xiàn)在某時(shí)某地亦可不出現(xiàn)而言。假若有理性的根據(jù),則其結(jié)果亦有時(shí)可以出現(xiàn),有時(shí)可以不出現(xiàn),皆有必然之理由。”儒家講“性善”、講“人皆可以為堯舜”,佛家講“即身成佛”、講“開悟”,都是講在理性層面上有根據(jù)的必然性。至于出現(xiàn)不出現(xiàn),開未開出,那是實(shí)存面上的另一問題。人欲橫流,天下滔滔,若孟子所云性善者,其出現(xiàn)蓋如鳳毛麟角,但仍可堅(jiān)持說“必”,說“性必善”。“求則得之,舍則亡之,是求之在我者也”,植根在既內(nèi)在又超越的理性層面上的必然性,屬于創(chuàng)造原理,實(shí)現(xiàn)原理,它不會現(xiàn)成地出現(xiàn),但只要去“求”,它必出現(xiàn)。這又與刻苦鉆研、孜孜以“求”古德巴赫猜想的解不同,因?yàn)楹笠环N“求”,仍然是“求之在我,礙之在天,是求之在外者也”。可見科學(xué)追求所在的理性層面,比之性理、空理、玄理之理性層面,自又有淺深之別。必然性之筑基,只能在內(nèi)在而超越的理性層面上講,不能在邏輯、科學(xué)、見聞之知的層面上講。這兩種必然性,也可以把它們區(qū)分為一種是外延的,一種是內(nèi)涵的。外延的必然性,有例外就不“必”了;內(nèi)函的必然性,就內(nèi)在根據(jù)立言,雖外表不出現(xiàn),亦仍為“必”。此種區(qū)別,古人知之甚稔。當(dāng)孔子說:“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時(shí).此“必”為內(nèi)涵的必,有根據(jù)的必。“德”、“仁”可作為“有言”、“勇”的根據(jù),反之則否,盡管外延他說,可能有例外:某有德者可能無言,某仁者可能一時(shí)膽小(甚至怕老鼠、怕蟑螂),而眼前的有言者倒真的全有德,勇者倒真的全是仁人君子。即使如此,仍不妨孔子的話是對的。但當(dāng)孔子告誡說:“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時(shí),這里的“必”即為外延的,缺乏根據(jù)的。既然缺乏根據(jù),孔子就教你“毋必”!現(xiàn)代人的生活方式、話語方式越來越外在化,因此現(xiàn)代人講必然性,就只知在平鋪的橫向的外延的呈現(xiàn)原理下講,這種“必然性”,在社會生活、人際事情上很少沒有例外,很少不被反駁不被“證偽”。故講之者往往出自以偏概全的武斷態(tài)度,駁之者又往往導(dǎo)致否認(rèn)必然性存在的虛無態(tài)度。兩方面都不知內(nèi)涵的有理性根據(jù)的必然性之存在。牟宗三將兩種必然性重新區(qū)分,又重新接通,謂之“正本清源”,殆非虛美。
就超越邏輯、科學(xué)、見聞之知的層面而建立內(nèi)在的理性層面而言,此為中國傳統(tǒng)儒釋道三家之共法。但是就為因果律尋其超越的必然性根據(jù)而言,牟宗三獨(dú)取徑于儒家。佛道兩家對世界和生活取一種“冷觀或不關(guān)心之觀照”的態(tài)度,故他們所開的是超“成知識的認(rèn)識心”之認(rèn)識心,因果性難以在此立基。莊子假托孔子言:“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王夫子解曰:“方目之擊,道即存乎所擊。……念念相續(xù)而常新,……不舍斯須而通乎萬年。”人進(jìn)入這種態(tài)度以及這種態(tài)度所成的境界中,就絕對沒有因果性探尋的余地。牟宗三如是詮釋之、引申之:“事至變而不居,目擊而應(yīng)之,是謂循斯須。過乎斯須,執(zhí)古以為今,則固蔽而不通。念念相續(xù),吾即以念念辱應(yīng)之。斯須念念,亦猶點(diǎn)點(diǎn)也。點(diǎn)點(diǎn)密移,亦猶念念相續(xù)也”。點(diǎn)點(diǎn)密移,是不成線,不成流的,也談不上變化,更談不上變化所循之軌跡。不循我,不循物,僅僅“循斯須而應(yīng)之”·縱然成流,亦只是虛無之流;縱然有變,也只是氣機(jī)之變。不能相應(yīng)于不易之理,因果性完全脫落。與二氏不同,“儒家于變易中見不易之理,不易之理發(fā)于天心之仁,則自然因果即得其超越之理性根據(jù)”。
關(guān)于因果范疇的“存有論性格”,牟宗三在《認(rèn)識心批判》中作到了二步,一、在成知識的認(rèn)識心內(nèi),建立因果關(guān)系之直覺的確定性;二、在天心道體上,建立其理性的必然性。于講透“邏輯性格”后,再講存有論性格,就不是簡單地回到實(shí)在論。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哲學(xué)就是訓(xùn)練人擺脫實(shí)在論心態(tài),卻又不否認(rèn)客觀實(shí)在。
七、超越的分解與“一心開二門”
牟宗三對康德哲學(xué)最重要的補(bǔ)正和貢獻(xiàn),在于他依中國傳統(tǒng)哲學(xué)充分證成了人可有“智的直覺”,人能知物自身。關(guān)此,系統(tǒng)完整通透的陳述是《現(xiàn)象與物自身》一書,前此則有《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xué)》一書,可視作《現(xiàn)象與物自身》的前奏。
一方面,牟宗三深入康德哲學(xué)內(nèi)部,徹底了解了它的問題和困難:另一方面,他叉在長期的浸潤和滲透中,將中國傳統(tǒng)儒釋道三家的盡理原型與分際,弄得清清楚楚,在乙多(教”的基礎(chǔ)上又復(fù)將它們?nèi)谕ā?jù)此,才能夠看出井彌補(bǔ)康德的不足。經(jīng)過在中國傳統(tǒng)哲學(xué)中長期的浸潤和滲透,牟宗三寫成《才性與玄理》、《佛性與般若,、《心體與性體》三部大著,分另歸,魏晉玄學(xué)、隋唐佛學(xué)、宋明儒學(xué)作了魚”造性的疏釋。分門另(類地觀之,它們屬于中國哲學(xué)史的研究,整體合一地觀之,貝(無論哲學(xué)史研究,還是康德研究,都是牟宗三學(xué)思生命的展開,正如他自己所說:“經(jīng)《才性與玄理》、《佛性與般若》、《心體與性體》、《從陸象山到劉蕺山》等書之寫作,以及與康德之對比,始達(dá)到此必然的消融。吾愧不能如康德,四無依傍,獨(dú)立運(yùn)思,直就理性之建構(gòu)性以抒發(fā)其批判的哲學(xué);吾只能誦數(shù)古人已有之慧解,思索以通之,然而亦不期然而竟達(dá)至消融康德之境使之百尺竿頭再進(jìn)一步。”這在牟宗三自為謙詞,卻也道出了作為中國學(xué)人,他要攀登西方哲學(xué)高峰的必由之路。這看上去斷斷不是一條捷徑,遷回曲折,艱難至極。牟宗三以艱巨獨(dú)任的勇氣和百折不撓的毅力,走完了這條路,登上了高峰。
如何百尺竿頭,更進(jìn)一步呢?
眾所周知,康德區(qū)分了現(xiàn)象與物自身(或曰“現(xiàn)象界”與“智思界”).按康德哲學(xué)的內(nèi)在理路,人的認(rèn)識只能及于現(xiàn)象,不能及于物自身。只有內(nèi)在于知性主體,人才能認(rèn)識;而只有跳出知性主體,才談得上認(rèn)識物自身。這在詞句上已經(jīng)是矛盾,而要跳出知性主體,不透過時(shí)空形式因果范疇這套機(jī)構(gòu)“純粹”地觀物,根本就做不到。康德不憚詞費(fèi)地證明:人只要試圖跳出知性主體,就會碰到無法克服的二律背反。照康德說來,認(rèn)識物自身,需要智的直覺,但人不可能有智的直覺,智的直覺屬于上帝,上帝知一切,但上帝不內(nèi)在于知性主體來知,不通過數(shù)學(xué)、科學(xué)來知;就如上帝統(tǒng)治一切,但上帝不通過法律和權(quán)力來統(tǒng)治。在西方傳統(tǒng)思想中,人是人,上帝是上帝,中間的鴻溝無法跨越。
但畢竟康德作出了“區(qū)分”(現(xiàn)象與物自身的超越的區(qū)分),既云區(qū)分,就意味著界限,意味著可以從界限的兩邊去看。這又與人永遠(yuǎn)被關(guān)閉在感性、知性的自我之內(nèi)永遠(yuǎn)見不到一線光明的描述不相符,康德因此翻上一層,試圖在《實(shí)踐理性批判》中解決這一問題。物自身既是超越的存在,便須由超越的主體契接之;超越的主體能立,超越的存在也就可知;而超越的主體之建立端在于“意志自由”之貞定。按照概念,真正的絕對的意志自由者是擺脫了一切羈絆束縛的,也就是擺脫了一切的規(guī)定性,連時(shí)空形式因果范疇都能擺脫。人能不能做到這一點(diǎn)呢?與物相比,看來人是有可以做到這一點(diǎn)的一些端倪、趨向的。王國維就這樣說:“我之為我其現(xiàn)于直觀中時(shí),則塊然空間及時(shí)間中之一物,與萬物無異。然其現(xiàn)于反觀時(shí),則吾人謂之意志而不疑也。而吾人反觀時(shí),無知力之形式行乎其間,故反觀時(shí)之我,我之自身也。”“無知力形式行乎其間”,非“時(shí)間空間中塊然一物”的自我,不是頗有“意志自由”的味道么?以上是對“意志自由”的含義的一種抉發(fā),還不是確實(shí)的貞定。康德經(jīng)過艱苦的努力,最終不得不承認(rèn),按照他強(qiáng)探力索建構(gòu)哲學(xué)的方法,并不能從客觀方面證明意志確實(shí)自由。意志自由只能從主觀方面去證明它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所以,他將“意志自由”,連同“上帝存在”、“靈魂不滅”作為設(shè)定,來展開其批判,顯得象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
關(guān)鍵是要將超越的區(qū)分真正地穩(wěn)固地定住,在康德那里,物自身不可知,自由意志只為設(shè)定,故現(xiàn)象與物自身的區(qū)分也就定不住。在牟宗三看來,超越的區(qū)分是康德“心中所閃爍的通識與洞見”,它不是一個(gè)主觀的架構(gòu),可以隨搭隨拆、而是“代表著一個(gè)客觀的,最高的而且是根源的問題”。正是在這個(gè)問題上,可以說東圣西圣,心同理同。而“東圣”,即中國傳統(tǒng)儒釋道三家的生命的學(xué)問,正好使康德哲學(xué)中,不穩(wěn)定的變?yōu)榉€(wěn)定,隔絕的變?yōu)閳A融,主觀設(shè)定的變?yōu)槿缛缋尸F(xiàn)之真實(shí)。
超越的區(qū)分,用《大乘起信論》里的話來說,就是“一心開兩門”。所謂二門,一為真如門,一為生滅門.說到底,中西哲學(xué)都是一心開二門,此為共同的架構(gòu),客觀的架構(gòu)。海德格爾研究存在問題,是受到由于存在被遺忘而產(chǎn)生的種種后果的刺激。,他要通過“詩”與“思”清理人的存在的基地,這就是在開真如門;而存在的遺忘及其種種后果,則屬于生滅門.胡塞爾把伽利略造始的近代科學(xué)精神,用“懸擬”的數(shù)學(xué)文本猜測自然現(xiàn)實(shí)的方法論,看作希臘科學(xué)原本方向的一種轉(zhuǎn)折,既是發(fā)現(xiàn),又是掩蓋。他的現(xiàn)象學(xué),則是要把這些用括號括住暫時(shí)封存起來,以便向希臘的理性主義源頭回溯,同樣是開真如門。可以說,所有的哲學(xué)都是在現(xiàn)實(shí)的生滅門中“逆覺體證”以開真如門的努力。當(dāng)然,將現(xiàn)實(shí)的生滅門疏理清楚,安排妥當(dāng),分別其源流,辯白其部居,亦可為開真如門作一準(zhǔn)備,在此意義上,講生滅門亦能成哲學(xué),如科學(xué)哲學(xué)即是。
對于開真如門,中國哲學(xué)的傳統(tǒng)向來能夠正視,十分著重,意識得很清楚,了解得很通透,并能把它充分展示出來。一言以蔽之,態(tài)度是積極的。牟宗三對康德哲學(xué)下過畢生的功夫,直至晚年,還把三大批判重譯一過,詳加評注。他又在中國哲學(xué)中長期浸潤,深悉精察,獨(dú)有心得,故能在這兩個(gè)概念文字截然相異的系統(tǒng)之間,看出它們的基本共同處,從而使它們互相補(bǔ)充,互相溝通,互相發(fā)明。《現(xiàn)象與物自身》一書,依儒釋道三家文獻(xiàn)和實(shí)踐,充分證成“人雖有限而可無限”,“人能有智的直覺”,“物自身可知”等等之義。儒家的良知,佛家的如來藏自性清凈心,道家的玄智(分別相對于習(xí)心、煩惱心、成心),都是自由無限心;道德踐履以致良知,明心見性而證如來,守靜致篤煉神還虛,都是達(dá)成自由無限心的途徑。中國哲學(xué)向來有知行合一的性格,無論儒釋道,其最高境界,都須默而識之。在此境中,能所不立,物我并泯,天地萬物粲然明備而又渾然一體。牟宗三則以其深厚的文獻(xiàn)和思考功力;出入諸家,辯而示之,用明確肯定的概念和花爛映發(fā)的文字,將此種境界表出。他的詮表,旁人礙難作簡單重述而本遺失精神。筆者當(dāng)然無此奢望,惟欲指出一點(diǎn):牟先生在《現(xiàn)象與物自身》中主要以佛家語說二層存有論,(執(zhí)的存有論與無執(zhí)的存有論;以無執(zhí)的形上心開本體界,此為無執(zhí)的存有論;以識心之執(zhí)開現(xiàn)象界,此為執(zhí)的存有論。)但是他的整套系統(tǒng)的骨干,特別是自由無限心之達(dá)成,則主要依據(jù)儒家內(nèi)圣之學(xué)。至于自由無限心坎陷為知性我,早在《認(rèn)識心之批判》講因果性一節(jié)中,就已對儒為一方、釋道為另一方作過比較。
儒家是從道德自律方面來理解和實(shí)踐自由的。但儒家的道德實(shí)踐決不限于庸言之信庸行之謹(jǐn)之類,決非外在行為規(guī)則因傳承和長期習(xí)練而內(nèi)在化。儒家的道德自律乃以“先立乎其大”的心體為本;而另一方面此心體又須依自律自決的道德踐履來實(shí)證和達(dá)成。兩者之間的相互依存關(guān)系是吊詭的自我關(guān)系。此心體既立,就開出了展露本體界的道德進(jìn)路。“以自由足以契接之來規(guī)定物自身”,這本是康德和牟宗三共同的思理方向,但康德欲以邏輯知解的方法來一一建構(gòu)其中的環(huán)節(jié),工作艱難而終于不能落實(shí),只能依靠設(shè)定來過渡。牟宗三則依傳統(tǒng)文獻(xiàn)作創(chuàng)造性的詮釋而證成之,故能達(dá)于圓融之境。
自由是價(jià)值意味的概念,物自身則極易被從事實(shí)方面來理解,所以要詮表明白“那知萬物的,是由于道德踐履而達(dá)到自由狀態(tài)的無限心”此一命題,實(shí)在也頗費(fèi)周折。好在中國傳統(tǒng)生命學(xué)問的深厚資源,現(xiàn)成俱在,牟宗三的“創(chuàng)謂”,自有儒家義理之“當(dāng)謂”作其根據(jù)。
舉例來說。朱子與王陽明對《大學(xué)》的解釋不同。朱子講“格物致知”,陽明講“致知格物:”在陽明,格者正也,致知格物即“致吾良知干事事物物以正之”。但不管分歧多大,朱子所謂的“知”與陽明所謂的“知”,兩個(gè)“知”都是“智的直覺”之知,對物自身之知,而非知性之知,此甚顯然。朱子主張下學(xué)上達(dá),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久而久之,終于會起一飛躍,達(dá)到豁然開朗,“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可謂知之極致。但卻不能理解為原子、分子、基本粒子,統(tǒng)統(tǒng)都見到了,明了了,因?yàn)檫@根本是兩路。到了這“無不到”、“無不明”的階段,再去格別物,便是王陽明所說的“致知格物”了。
陽明游南鎮(zhèn),一友指巖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于我心亦何相關(guān)?”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shí),此花與汝心同歸于寂,你來看此花時(shí),則此花顏色一時(shí)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不能將陽明與貝克萊、馬赫之類的唯我論、感覺論等同起來。“此花與汝心同歸于寂”是關(guān)鍵語,反轉(zhuǎn)說就是“此花與汝心同時(shí)明白”。所以心不僅單單位于你的腔子里,心也在萬物之中。”心體萬物”,不僅是指心能體會萬物,進(jìn)也指心乃是萬物之體;天心、道心、人心,如其不隔,自為一心。心體萬物,且能體物無遺,自然心外無物。此是人能達(dá)到的境界,也即是知物自身的境界。如若隔了,心隔在了腔子里,便不能說心外無物。認(rèn)識心是一種有隔的人心,故物自身在它之外,不為它所知。張橫渠說:“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聞見之狹。圣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心可大,也可小,可以有外,也能做到無外.人雖有限,而可無限,成圣、成佛、心無外、知物自身、意志自由,等等,都是一個(gè)意思。
八、人雖有限而可無限
人能不能無限?中國哲學(xué)與西方哲學(xué)兩個(gè)傳統(tǒng)最大的分歧恐怕就在這里。許多現(xiàn)代西方哲學(xué)家,雖然否認(rèn)笛卡爾式二元對立中的主體性,要求人超越自身溶入一客觀的“主體間性”(intersuUectivity)中去,融入傳統(tǒng)中去,但畢竟為人規(guī)定了上限。例如哲學(xué)闡釋學(xué)將“經(jīng)驗(yàn)”一概念視為人類最重要也最難以理解的概念之一,將它從實(shí)證主義經(jīng)驗(yàn)主義的簡化和歪曲之中解救出來,賦予它豐富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的含義,結(jié)論則是“真正的經(jīng)驗(yàn)就是這樣一種使人類認(rèn)識到自身有限性的經(jīng)驗(yàn)”,“真正的經(jīng)驗(yàn)就是對我們自身歷史性的經(jīng)驗(yàn)”。簡言之,人有限,不能無限。很顯然,過去的基督教傳統(tǒng)也是否認(rèn)人能無限、人有神性的。倒是現(xiàn)代西方宗教神學(xué)顯示出一種變化,上帝在淡化,人的精神在凸現(xiàn),人神隔絕在消泯。蒂利希強(qiáng)調(diào)對“上帝存在”一命題應(yīng)作“本體論”的理解,不能作宇宙論的理解。馬丁·布伯《我與你》一書,教人超越“我與它”的有限世界,進(jìn)入“我與你”的無限世界:“‘世界在此,上帝在彼’,這話乃屬于它之語言”,“上帝即是我們直接無間親切厚摯久久不滅之相遇者”分明有了人可無限之意。西方哲學(xué)傳統(tǒng)中,康德最接近于正視人的無限性、人的神性。
自由無限心,乃三教之共法,是會通的產(chǎn)物。但牟宗三搞會通卻不是掏漿糊。會通乃以判教為基礎(chǔ),對義理系統(tǒng)的界定和區(qū)別,分判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例如辨佛儒之別,他這樣說:“空卻定相而為空如無相的緣起,則無執(zhí)的主體便是般若智。因此,相應(yīng)般者智而言,定須是以空如無相為實(shí)相。縱使言到真常心,亦仍是如此。然而在此卻并透不出道德意識來,故佛家至此而極。因此,儒家的道德意識遂顯其特殊。相應(yīng)于道德意識中的知體明覺而言,則空如無相的幻化緣起即轉(zhuǎn)為‘實(shí)事,與‘實(shí)物、,而并非幻。此實(shí)而非幻乃是由于知體明覺中之天理而貞定住的。故此義乃是高一層者,此并非是以空如無相的緣起為緣起之在其自己,乃是轉(zhuǎn)進(jìn)一步,以實(shí)事為事之在其自己,以實(shí)物(其自身即為一目的之物)為物之在其自己”。
這一段話抓住了儒區(qū)別于佛的關(guān)鍵,儒家對人生、俗世充分肯定,在佛家只看到緣起幻化的地方,卻看到了實(shí)事實(shí)理。儒家是要就著人生、俗世,就著生滅門,向上開理想之門,通真如界。而佛家雖也承認(rèn)世俗義諦,卻只是講方便。即使天臺宗那種吊詭的“圓具”,也還缺乏儒門的積極。佛家只是承認(rèn),儒家則敢肯定。
象儒家這樣通過肯定人生導(dǎo)著人生走上理想之路的哲學(xué)倫理之教,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可謂絕無僅有。佛教的苦諦,基督教的罪業(yè)意識,都是否定人生,就是現(xiàn)代海德格爾的哲學(xué)也不能象儒家那樣在肯定人生中討回本真的存在,雖然他對現(xiàn)實(shí)人生的現(xiàn)象學(xué)的描寫深獲人心。海德格爾否定人生的態(tài)度集中表現(xiàn)在對科學(xué)技術(shù)的否定上。他悲觀地認(rèn)為精神失落是現(xiàn)今技術(shù)時(shí)代無可挽回的必然宿命。他不認(rèn)為技術(shù)是中性的,全看人怎么運(yùn)用它。他斷定技術(shù)對人的威脅不來自龐大的機(jī)器和毀滅性的武器,而來自技術(shù)的本質(zhì)存在即“阱架”本身:“阱架的統(tǒng)治威脅人,竟使人再無路轉(zhuǎn)入更原始的去蔽并從而得以經(jīng)驗(yàn)更原始的真理指令。因而,阱架統(tǒng)治之處,有至高的危險(xiǎn)。”所以人是無望的,只能等待滅亡,或等待拯救,最多,為拯救的來臨作一些準(zhǔn)備,“就技術(shù)的本質(zhì)存在來經(jīng)驗(yàn)它”不能擺脫它,至少亦不受它蒙蔽以便拯救來臨時(shí)能夠從本質(zhì)上拋棄它;似乎人的得救,人的回到存在之家,就意味著要把歷史上得到的文明成果都摧毀,在認(rèn)識上也就意味著要把具體的科學(xué)都抹煞。海德格爾雖未這樣露骨地明言,但正如PauI Ricoeur所批評的:“讀海德格爾哲學(xué),我們總是忙著回到基地,但這卻是一條不歸路,對怎樣從基礎(chǔ)本體論回到具體適切的人文科學(xué)的認(rèn)識性問題上,我們卻毫無辦法。一種哲學(xué)如果停止了與科學(xué)的對話,就會成為孤家寡人”。
以牟宗三為代表的當(dāng)代新儒家,對科學(xué)的態(tài)度,與海德格爾截然相反。正如傳統(tǒng)儒家一向肯定人生、俗世一樣,牟宗三也從哲學(xué)上充分肯定科學(xué)。儒學(xué)是一種生命的學(xué)問,是人學(xué),但如開不出科學(xué),就“人義不全”。傳統(tǒng)儒學(xué)在這方面的缺陷,并不是方向錯(cuò)了,而是因?yàn)閷ι鷾玳T還開得不夠,肯定得還不夠積極。傳統(tǒng)儒家也重視“見聞之知”,重視“道問學(xué)”,但其主要目的是借“見聞之知”,借“道問學(xué)”為梯航,以通“德性之知”,以“尊德性”;并沒有把見聞之知本身封起來作為一門來正視。傳統(tǒng)儒家把目的看得太直捷,在趨赴德性之知的途中,不肯稍事逗留,少一步盤桓回環(huán),這方面,王陽明的教導(dǎo)最有代表性:知行合一。學(xué)生來問:“如今人盡有知得父當(dāng)孝、兄當(dāng)悌者,卻不能孝、不能悌,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王陽明答道:“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賢教人知行,正是安復(fù)那本體,不是著你只恁地便罷,故《大學(xué)》指個(gè)真知行與人著,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shí)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后又立個(gè)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shí)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后別立個(gè)心去惡。……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悌,方可稱他知孝知悌,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悌的話,便可稱他知孝悌。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就德性之知,或曰德性之知收攝見聞之知為言,陽明說得完全正確。德性本體上,知行原來不隔,一拿了私意去隔,結(jié)果并不是知行為兩,而是根本不知。但如講科學(xué)知識,卻恰恰相反必須要有隔,只有隔,才能知。王陽明“致知格物”之物,乃“行為物”,并非可以作為科學(xué)認(rèn)識對象的物。當(dāng)然,成科學(xué)知識所需要的“隔”,并不是出于“私意”,它確實(shí)需要“別立個(gè)心”,才能成,這便是“知性我”,“認(rèn)識心”。
牟宗三就是要從王陽明知行合一的直筒子上,橫出去開“知性我”,此即自由無限心(道德良知)知體明覺之自我坎陷。坎陷以后的隔,是有來歷的隔,因此也復(fù)可以破隔。此一隔,是開出了一個(gè)新的領(lǐng)域,是生命之歧出,而只要重新回歸,歧出也是擴(kuò)大,是生命趨于圓滿。牟宗三早年與熊十力先生通信討論這些問題,隱隱然表達(dá)了這些意思。熊先生曾回信批評“推求太過”,致熊先生自己的意思,則曰:“知之流通處即是物,……故格物實(shí)非向外”。仍然是陽明不許有隔的意思。這在德性之知上當(dāng)然正確,但對于成科學(xué)知識,卻不中肯。熊先生久欲作《量論》,而終于不能成功,其故或正在于此“隔”與“不隔”之一間,尚有未達(dá)歟?
“如何坎陷”?這在有關(guān)的討論中是最常提出的問題,而且好象還是最重要的問題,然而這卻是一個(gè)假問題,偽問題。提問者似乎想要求得一個(gè)現(xiàn)成的方法,照此做去,自然而然就開出了科學(xué)與民主。如若提出坎陷說的牟宗三卻提不出這樣的方法,那么坎陷說就被駁倒了。
然而須知,哲學(xué)并不負(fù)責(zé)寫方法論說明書和操作規(guī)程,“哲學(xué)就其本性從不使事情變得容易些,反而是使它們變得更難些”。道德良知坎陷為知性我,只是為知性我提供一根源的說明,并辯示智的直覺可在向根源的回溯中達(dá)到。至于知性我的運(yùn)用怎樣去具體地研究問題、解決問題,這本來是每一個(gè)人的事,不是哲學(xué)的事。“知性我”在康德那里主要屬于“呈現(xiàn)原則”,“存有原則”,即它本來如此,從娘胎里帶出來就有,是超國度、超文化、超時(shí)代的。傳統(tǒng)中國人照樣有“知性我”,有時(shí)空直觀,有因果范疇;只是當(dāng)把立“知性我”與開科學(xué)、民主、法制等聯(lián)系起來講時(shí),這就屬于實(shí)現(xiàn)原理,創(chuàng)造原理了,需要人去努力,才能做到“西方人開出現(xiàn)在這種樣子的科學(xué)與民主,也是很晚的事。這不是哲學(xué)家所能包辦的。
依筆者的理解,良知坎陷以立知性我,雖然有良知暫處一邊暫被遮蔽的意思,但是究其實(shí),知性我之正大發(fā)達(dá),也可成為張載所謂“大其心”之一部分,知性我之知物,也可成為無限心體物的一種重要方式;換言之,缺了這部分,缺了這種方式,心反而不大,反而有外。
舉例來說,當(dāng)此社會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劇烈變動的時(shí)期,政策變化大,互相矛盾的政策并存多,人們由于自身利益的動機(jī)而有贊成或反對的態(tài)度,乃事理與情理之常,不難理解。但人們在表示贊成或反對態(tài)度時(shí),往往掩蓋實(shí)質(zhì)的利益動機(jī),卻假借公正的名義,表現(xiàn)道德的激情和義憤,忘了自己乃牽扯于利益格局中,贊成或反對的動機(jī)是主觀性極強(qiáng)的利益或心理。在這種激情和義憤下的人,是無法體物的,排拒性極強(qiáng),哪里談得上“萬物皆備于我“。但如能堂堂正正立起一個(gè)知性我,掌握了經(jīng)濟(jì)學(xué)知識和分析能力,客觀地、科學(xué)地認(rèn)識經(jīng)濟(jì)世界的現(xiàn)狀及其趨勢,那就能夠排除掉沖動的、虛偽的、意識形態(tài)的、掩蓋主觀利益的“道德”激情或義憤,以一種平衡穩(wěn)健的心態(tài)來說話行事。知性我有主體性(因?yàn)榕c物兩立),無主觀性(因?yàn)槿巳私酝焕鎰t純?yōu)橹饔^性,無主體性(可因?yàn)槔娴霓D(zhuǎn)移而轉(zhuǎn)移立場)。有了“知性我”客觀科學(xué)的認(rèn)識,我人就能對哪怕是損害我利益的人和事有一種如實(shí)的理解和如理的寬諒,這不就是擴(kuò)大我心以體萬物過程中的一個(gè)進(jìn)步嗎?反之,如沒有這種科學(xué)客觀的認(rèn)識,知性我不立,只受心理情緒氣機(jī)之鼓蕩,和主觀利益之驅(qū)動,而又以道德激情或義憤的偽裝出現(xiàn),那就越講道德,越與人隔絕,自我世界,及膚而止,哪里還有“大其心”,“體天下之物”可言呢?
文章分頁: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