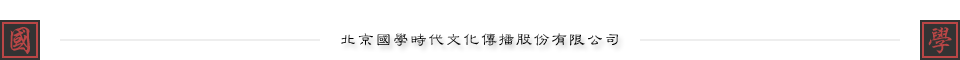聶紺弩先生為什么沒講真話
《就“施耐庵之謎”訪周夢莊先生》于2010-11-18 04:49:56貼出后,有博友感嘆:“可嘆!又是一筆糊涂賬!周說將抄件交聶,而聶又說絕無此事,同行多人為證。時間過去不久都搞不清楚了,何況幾百年前的事情!”
問題其實并沒有后人想象的復雜。早在見到周夢莊先生之前,我就相信這事情是真的了。1981年2月,我從南京跑到大豐,王同書陪我搭小航船,過獨木橋,從白駒到大營,再從大營到施家橋。一位施氏后裔,從門中沖出來,一把揪住我的領口,說:“你是徐放嗎?你把我們老祖的東西拿走,為什么至今不還?”原來,他是把我當做1952年調查組的人了。這一幕1987年3月26日被我寫進為王同書《施耐庵之謎新解》所作序中,可以方便地從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9年版中查到。
最直接的證據是:當年陪同聶紺弩調查的蘇北文聯丁正華,1982年9月翻檢“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而又發還之資料,中有周夢莊《水滸傳本事考》抄件,施耐庵《秋江送別》遺曲赫然在目。1952年調查組成員徐放,1982年7月31日致書劉冬,告知《施耐庵生平調查報告》稿已找到;后寄來南京,發表于《明清小說研究》第4輯(1986年12月),所錄《秋江送別》遺曲,與丁正華抄件完全一致。事實證明:“周說將抄件交聶”,是真話;“聶又說絕無此事”,不是真話。
那么,在這件事上,聶紺弩先生為什么沒講真話呢?
我沒有會過聶紺弩先生,但——
首先,我相信他是敢講真話的人。有材料介紹說,馮雪峰評論他:“這個人桀驁不馴,都嫌他吊兒郎當,誰也不要,我要!”自評:“我這個人,既不能令,也不受命。”時時處處抱“我不在內”態度的聶紺弩,當有人攻擊馮雪峰,卻馬上站起來,將攻擊者駁得啞口無言。吟詠其獄中《沁園春·贈木工李四》:“馬恩列斯,毛主席書,左擁右攤。覺唯心主義,抱頭鼠竄;形而上學,啞口無言。滴水成冰,紙窗如鐵,風雪迎春如沁園。披吾被,背《加皮塔爾》(注:《資本論》),魚躍于淵。? 坐穿幾個蒲團,遇人物風流李四官。藐雞鳴狗盜,孟嘗賓客;蛇神牛鬼,小賀章篇。久想攜書,尋師海角,借證平生世界觀。今老矣,卻窮途罪室,邂逅君焉。”同樣經歷過監獄生活的我,不覺莞爾而笑。
其次,我相信他是真正的學者。他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主持整理出版了《水滸傳》《紅樓夢》等古典名著及一批古典文學選本,自己又寫了幾十萬字的研究論文。他是解放后古典文學研究的草萊開辟者。他的《水滸五論》我曾認真拜讀,且寫了評論《貢獻與疏誤》,刊于《水滸新議》之中。他詠林沖的佳句:“男兒臉刻黃金印,一笑身輕白虎堂。”更是一般人寫不出來的。
再次,我相信聶紺弩先生當年對南下調查,態度是積極的,路子是對頭的,而且是大有收獲的。
《水滸傳》是最先整理出版,最受推崇的古代小說。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歌頌“農民起義”這一新的價值判斷,讓《水滸傳》立即獲得新體制及其意識形態的認可,弄清楚《水滸》作者施耐庵的生平,乃是古代文學研究工作者的神圣使命。正是在這一認識的驅動下,以聶紺弩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調查組,1952年10月南下后,先后調查了興化城、淮安城、大岡鄉、施家橋、施家舍、施家莊、白駒鎮、安豐鎮等處,又跑到蘇南的江陰、常熟一帶,歷時四十馀天。其中的甘苦,我相信誰也沒有三十年后隨劉冬同志沿著他們當年的路線又跑了一遍的我,體會得真切。
回想當年,每次出差,劉冬同志癱瘓在床的夫人顧影,把糧票與錢一一交到我手,回來后再和她結帳。1982年1月31日,我陪劉冬同志冒雪去興化,住在條件極差的招待所,夜間寒風從門縫吹進,冷得渾身打顫。2月1日去施橋看《施廷佐墓志銘》,返抵興化已近暮,晚飯以一碗豆腐腦代替了事。我日記寫道:“在施耐庵墓前攝影留念,接著看了施廷佐墓志銘,出土的瓷陶噐與磚。又到地里去了解發現經過,搞了拓片,辨認了上面的字,收獲很大,劉冬同志始終沉浸在興奮狀態中。肚中餓極。三點才返新垛公社吃到了午飯。”發現的快樂,讓我們忘卻了饑餓與疲勞。退回去三十年,1952年的中國,無論交通、食宿,條件會更加艱苦,而聶紺弩他們一來就是四十馀天,又值隆冬時節,沒有一番科研探索的熱情,是不可想象的(我們每次出差,一般不超過十天)。
文化部調查組在聶紺弩領導下,查閱了大量地方文獻,訪問了許多遺老和施氏后人,記錄了許多民間口碑。在施家橋調查尤為細致,幾乎逐戶走訪。由于路子對頭,又得到廣大群眾熱情支持和積極協助,獲得了許多珍貴資料。其中即包括謝興堯請范煙橋寫信、由周夢莊提供的施耐庵散曲抄件,興化督學張存儀在施氏后裔處抄得的全部材料,施文秀獻出的1946年拆毀施氏宗祠時請回家的“蘇遷施氏宗”木主,等等。如果不是認為對揭開“施耐庵之謎”有重大價值,他們會興師動眾地把這一大批文物史料運回北京嗎?
徐放的表現更說明問題。如果不是認為有價值,他會不顧個人安危,把《施耐庵生平調查報告》稿保存下來嗎?如果不是受他的感染,塔灣大隊女書記王力華會不惜開除黨籍,將文稿藏匿下來嗎?
那么,聶紺弩先生為什么還是不講真話呢?
只要看他給鹽城地委宣傳部的復信就知道了:“我等調查所得材料,均已由錢鋒同志經手,交與文化部,由文化部辦公廳主任趙沨同志點收,以后又由我向中宣部副部長胡喬木同志一再作了經過匯報,形諸筆墨者,喬木同志均認為是風影之談,無可依據,不可發表了事。”
既然“一再作了經過匯報”也無用,便只好說“蘇北連施耐庵的影子也沒有”了。
2010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