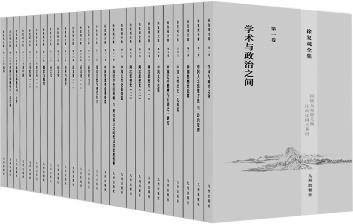徐復(fù)觀: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的責(zé)任
我認(rèn)為知識(shí)分子和技術(shù)人員是應(yīng)加以區(qū)別的。以其知識(shí)影響社會(huì)的是知識(shí)分子;以其技術(shù)建造機(jī)械,使用機(jī)械的是技術(shù)人員。當(dāng)然,有許多知識(shí)分子而兼技術(shù)人員,也有許多技術(shù)人員而兼知識(shí)分子,以致二者的分別并不明顯。但只要想到技術(shù)的效用是無(wú)顏色的,所以技術(shù)人員,可以為各種形態(tài)的極權(quán)專制者所容,甚至為他們所需要,而知識(shí)接觸到實(shí)際問(wèn)題時(shí),經(jīng)常是以批判之力,發(fā)生推進(jìn)的作用;所以知識(shí)分子必然被各種形態(tài)的極權(quán)專制者所排斥,他們經(jīng)常運(yùn)用閹割大腦的手術(shù),以一批被閹割大腦的人來(lái)冒充知識(shí)分子。由此便應(yīng)當(dāng)了解把知識(shí)分子與技術(shù)人員加以區(qū)分,實(shí)有其重要意義。更由此可以了解,凡不是生長(zhǎng)在民主制度下的知識(shí)分子,必然是帶著悲劇性的命運(yùn)。而此悲劇性的命運(yùn),也成為真知識(shí)分子與假知識(shí)分子中間的檢證器。
由上面的陳述,應(yīng)當(dāng)可以導(dǎo)出一種結(jié)論,即是: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的責(zé)任,乃在求得各種正確知識(shí),冒悲劇性的危險(xiǎn),不逃避,不詭隨,把自己所認(rèn)為正確而為現(xiàn)實(shí)所需要的知識(shí),影響到社會(huì)上去,在與社會(huì)的干涉中來(lái)考驗(yàn)自己,考驗(yàn)自己所求的知識(shí)的性能,以進(jìn)一步發(fā)展、建立為我們國(guó)家、人類所需要的知識(shí)。
僅僅這樣說(shuō),對(duì)問(wèn)題還沒(méi)有交代清楚。
許多人說(shuō),凡是知識(shí),都是科學(xué)的;凡是科學(xué),都是無(wú)顏色的;并且在追求知識(shí)時(shí),應(yīng)當(dāng)保持沒(méi)有顏色的態(tài)度。假使這種說(shuō)法不隨意推廣,我也同樣地加以承認(rèn)。但我們要知道,只要是一個(gè)活生生的人,便必然有顏色的,亦即是必然有某種人生態(tài)度的。無(wú)顏色的知識(shí)的追求,必定潛伏著一種有顏色的力量,在后面或底層,加以推動(dòng)。此一推動(dòng)力量,不僅決定一個(gè)人追求知識(shí)的方向、成果,并且也決定一個(gè)人對(duì)知識(shí)的是否真誠(chéng)。簡(jiǎn)言之,嚴(yán)肅的知識(shí)追求,不管追求者的自身意識(shí)到或沒(méi)有意識(shí)到,必然有一種人格作他的支持的力量;否則會(huì)如今日許多人一樣,經(jīng)常玩弄著以詐術(shù)代替知識(shí)的把戲。而人格必然是有顏色的。
說(shuō)到以知識(shí)影響社會(huì),首先必須知識(shí)和自己的人格融合在一起,知識(shí)形成人格中的一部分,才會(huì)感到有此要求。所以進(jìn)入到此一階段,以人生態(tài)度為內(nèi)容的人格高下,更有決定性的作用。就現(xiàn)狀說(shuō),較好的知識(shí)分子,常常知識(shí)是知識(shí),行為是行為,應(yīng)付是應(yīng)付。較壞的知識(shí)分子,便常常歪曲知識(shí),以作趨炎附勢(shì)、奪利爭(zhēng)權(quán)的工具。要憑著自己所把握的知識(shí)去影響社會(huì),在知識(shí)后面,更要有人格的支持力量。
但我國(guó)有二千年的專制歷史,有千多年的科舉歷史。這兩種歷史因素,一起直接壓在中國(guó)過(guò)去的“讀書人”身上,于是在士農(nóng)工商的四民中,以“士”的人格最為破產(chǎn);在歷史中,由知識(shí)分子所發(fā)出的壞的作用,絕對(duì)大于好的作用。專制科舉的遺毒,應(yīng)當(dāng)由民主、科學(xué)來(lái)加以掃除。但不幸的是,在軍閥的混亂中,一部分性急的人,卻與極權(quán)主義接上了種,于是歷史的遺毒,不僅借尸還魂,并且現(xiàn)代極權(quán)主義的各種技巧,更為遺毒來(lái)“如虎添翼”;他們連民主、科學(xué)也一并吞下,拉出不能作肥料的毒性廢物。這就是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現(xiàn)時(shí)的“置境”。
在上述“置境”中的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為了要盡到以知識(shí)影響社會(huì)的責(zé)任,我認(rèn)為首先要盡到使自己成為一個(gè)“堂堂正正的人”的責(zé)任。
如何是一個(gè)堂堂正正的人?這難用概念來(lái)下定義,而只有從消極積極兩方面略加描述。
消極方面:一、不投機(jī)取巧,不趨炎附勢(shì)。二、不假冒知識(shí),不歪曲知識(shí),更不以權(quán)勢(shì)代替知識(shí)。三、不以個(gè)人現(xiàn)實(shí)中的名利出賣自己的學(xué)術(shù)良心,淹沒(méi)自己的學(xué)術(shù)良心。
積極方面:一、將自己解消于自己所追求的知識(shí)之中,敬重自己所追求的知識(shí),也敬重他人所追求的知識(shí);經(jīng)常感到知識(shí)高于一切權(quán)勢(shì),貴于一切權(quán)勢(shì)。二、自己的精神,與自己的國(guó)家民族,有自然而然的“同體之感”,有自然而然地在自己的本分內(nèi)獻(xiàn)出一分力量給自己的國(guó)家民族的要求。
有的人可能把我上面所描述的“堂堂正正的人”,和近代的個(gè)人主義,對(duì)立起來(lái),因?yàn)槔锩嫒狈?quán)利義務(wù)的觀念。我的看法是:中國(guó)圣賢立教,對(duì)“士”自身的要求,常常遠(yuǎn)嚴(yán)格過(guò)對(duì)一般社會(huì)的要求。作為一個(gè)知識(shí)分子,在面對(duì)權(quán)勢(shì)時(shí),應(yīng)當(dāng)堅(jiān)守自己的權(quán)利,限定自己的義務(wù)。在面對(duì)社會(huì)時(shí),則應(yīng)當(dāng)忘記自己的權(quán)利,擴(kuò)大自己的義務(wù)。西方個(gè)人主義所以能發(fā)生進(jìn)步性的功效,是因?yàn)橛胁簧俚闹R(shí)分子,忘記了自己的個(gè)人,以要求成就社會(huì)上的每一個(gè)人。若知識(shí)分子成為自我中心的個(gè)人主義者,必然地一轉(zhuǎn)眼便會(huì)變成奴才主義者。對(duì)權(quán)勢(shì),自己是奴才;在自己可以支配的范圍以內(nèi),把他人當(dāng)作奴才。因此,我愿意這樣地說(shuō):“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lè)而樂(lè)”的知識(shí)分子,才是知識(shí)分子個(gè)人主義的“正種”。
堂堂正正的人,只是一念之間,一念提撕警惕之間的精神狀態(tài)。此精神狀態(tài)應(yīng)貫注于自處與處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應(yīng)貫徹于求知與用知之上。這是知識(shí)分子為了能盡其他各種責(zé)任的發(fā)射臺(tái)。沒(méi)有此一發(fā)射臺(tái)的營(yíng)營(yíng)茍茍的知識(shí)分子,除了追求個(gè)人的飽食暖衣、蠕蠕而動(dòng)、偷偷以息之外,還能談什么責(zé)任呢?
《徐復(fù)觀全集》書目
一、《中國(guó)人之思維方法·詩(shī)的原理》
二、《學(xué)術(shù)與政治之間》
三、《中國(guó)思想史論集》
四、《中國(guó)人性論史·先秦篇》
五、《中國(guó)藝術(shù)精神·石濤之一研究》
六、《中國(guó)文學(xué)論集》
七、《兩漢思想史》(一)
八、《兩漢思想史》(二)
九、《兩漢思想史》(三)
十、《中國(guó)文學(xué)論集續(xù)篇》
十一、《中國(guó)經(jīng)學(xué)史的基礎(chǔ)·周官成立之時(shí)代及其思想性格》
十二、《中國(guó)思想史論集續(xù)篇》
十三、《儒家思想與現(xiàn)代社會(huì)》
十四、《論智識(shí)分子》
十五、《論文化》(一)
十六、《論文化》(二)
十七、《青年與教育》
十八、《論文學(xué)》
十九、《論藝術(shù)》
二十、《偶思與隨筆》
二十一、《學(xué)術(shù)與政治之間續(xù)篇》(一)
二十二、《學(xué)術(shù)與政治之間續(xù)篇》(二)
二十三、《學(xué)術(shù)與政治之間續(xù)篇》(三)
二十四、《無(wú)慚尺布裹頭歸·生平》
二十五、《無(wú)慚尺布裹頭歸·交往集》
二十六、《追懷》
徐復(fù)觀簡(jiǎn)介
徐復(fù)觀先生(1903—1982),湖北浠水人,出生于湖北省浠水縣徐家坳鳳形塆。原名秉常,字佛觀。八歲從父執(zhí)中公啟蒙,續(xù)在武昌高等師范及國(guó)學(xué)館接受中國(guó)傳統(tǒng)經(jīng)典訓(xùn)練。1926年參加國(guó)民革命軍。1928年赴日留學(xué),大量接觸社會(huì)主義思潮,先入明治大學(xué),后就學(xué)于日本士官軍校。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發(fā)后,激于民族義憤,提前返國(guó)。七七事變后,投身抗戰(zhàn),親身參與娘子關(guān)戰(zhàn)役及武漢保衛(wèi)戰(zhàn)。1943年,任軍令部聯(lián)絡(luò)參謀,派駐延安。數(shù)月后返回重慶,任蔣介石侍從室機(jī)要秘書,擢升少將。1944年謁熊十力先生于重慶北碚勉仁書院,并拜入其門下。熊先生特為更名“復(fù)觀”,取義《老子》“萬(wàn)物并作,吾以觀復(fù)”。與共產(chǎn)黨高層多次直接接觸。在熊先生的開導(dǎo)下,重啟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信心,并從自身的實(shí)際經(jīng)驗(yàn)中,體會(huì)出結(jié)合中國(guó)儒家思想及民主政治以救中國(guó)的理念。1949年5月,遷臺(tái)。年近五十而志不遂,1951年轉(zhuǎn)而致力于教育,擇菁去蕪地闡揚(yáng)中國(guó)文化,并秉持理念評(píng)論時(shí)事。1955年起,出任東海大學(xué)中文系教授。1970年后遷居香港,誨人筆耕不輟。徐教授于1982年4月1日辭世。他是新儒學(xué)的大家之一,亦是臺(tái)、港最具社會(huì)影響力的政論家,是二十世紀(jì)中國(guó)智識(shí)分子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