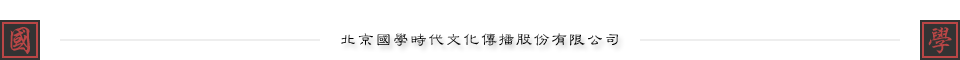國學大師錢穆的一生
“為錢家保留幾顆讀書種子”
“東南財賦地,江浙人文藪”,錢穆的故鄉在江南水鄉無錫的七房橋。父親錢承沛考中秀才后,因體弱多病,無意科名,但對兩個兒子卻寄予厚望,希望他們能讀書入仕。錢穆7歲那年,被送到私塾讀書。12歲時,41歲的父親撒手塵世。孤兒寡母,家境貧困不堪。母親寧愿忍受孤苦,也不讓孩子輟學,她說:“我當遵先夫遺志,為錢氏家族保留幾顆讀書的種子……”于是錢穆得以繼續就讀。
無錫蕩口鎮果育學校,是辛亥革命前無錫開風氣之先的一所典型的新式學校。學校師資力量極佳,既有深厚舊學根底的宿儒,又有從海外學成歸來具有新思想的學人。當時教體操的老師是21歲的錢伯圭,曾就讀于上海南洋公學,思想激進,系當時的革命黨人。他見錢穆聰敏早慧,就問他:“聽說你能讀《三國演義》?”錢穆作了肯定的回答。老師便借此教誨道:“此等書以后不要再讀。此書一開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之類的話,此乃中國歷史走上了錯路,故有此態。如今歐洲英、法諸國,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亂。我們當向他們學習。”此番話給年僅十歲的錢穆以極大的震動,日后他在回憶此事時說:“此后讀書,伯圭師言常在心中。東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問題內。”
1907年,他升入常州府中學堂。學校監督(校長)屠元博(孝寬),為著名歷史學家屠寄的長子。監督之下設有舍監,類似以后的訓導長。首任舍監劉伯琮為人和藹友善,對學生循循善導,深受大家的喜歡。后來換了新的舍監陳士辛,教學生修身課,與學生相處不好。錢穆所在的四年級在年終大考前,全年級集體提議,請求校方對明年的課程作些改動,要求減去修身課,增加希臘文課等。學生公推錢穆等五人為代表與校長商談,又以集體退學相要挾,結果均為校方拒絕。錢穆作為學生代表,性格倔強,于是拒考,填退學書,自動退學。
在這次學潮的五位代表中,除錢穆外,還有兩位后來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一位是創辦《國故》月刊的常州張壽昆(張煊);另一位是江陰的劉壽彭,即“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大名鼎鼎的劉半農;還有一位是校長屠元博的三弟屠孝寔。比錢穆低兩個年級的瞿秋白也在常州府中學堂就讀,以聰慧聞各全校。
錢穆因鬧學潮退學,回到了七房橋老家。由于錢穆國文和歷史的成績為同學之最,年齡又是最小,所以,校長屠元博雖將他除名,但對這位年幼倔強、聰敏伶俐的學生很欣賞的,他推薦錢穆到南京鐘英中學就讀。
顧頡剛慧眼薦才
世事多變,錢穆在南京鐘英中學求學不久,就爆發了推翻滿清王朝的武昌起義。學校停辦,錢穆輟學了。他自知家貧,升學無望,雖“心中常有未能進入大學讀書之憾,但并沒有因此而意志消沉。矢志自學,閉門苦讀。年十八,即輾轉鄉村,執教謀生。”十年鄉教,十年苦讀,十年求索,為他以后的學術研究奠定了深厚扎實的基礎。這十年中,他在國學的研究方面成果也不少。后來,他又在朋友的介紹下,開始在無錫、蘇州等地的中學教書著述,在刊物上發表了不少學術論著。
晚清以來,隨著社會歷史條件的深刻變化和大規模的西學東漸,諸子之學的研究逐漸興起。特別是“五四”前后,諸子研究蔚然成風。錢穆早年步入學術之門,也是在這一背景下,從子學入手,研究先秦諸子思想及諸子事跡考辨,最終完成了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名作《先秦諸子系年》。這部著作對先秦諸子年代、行事及學術淵源,以及對戰國史的研究,都作出了極大的貢獻,深得學術界的好評。陳寅恪稱其“極精湛”,“自王靜安(國維)后未見此等著作”。顧頡剛則稱贊其“作得非常精煉,民國以來戰國史之第一部著作也”。當時年長錢穆一歲的顧頡剛,已是中國學術界大名鼎鼎的人物,雖與錢穆素昧平生,但讀《系年》稿后,對他的史學功底和才華大加贊賞,并說:“君似不宜長在中學中教國文,宜去大學中教歷史。”
錢穆最高的文憑僅為高中(尚未畢業),完全是靠自學成才的。1930年,因顧頡剛的鼎力相薦,才使他離開鄉間,北上燕京大學,開始任國文系講師。
燕京是一所教會大學,在北平各大學中,非常有名氣。當時校務主要由監督司徒雷登主持。一天,司徒雷登設宴招待新來教師,問大家到校印象。錢穆在會上直抒己意:“初聞燕大乃中國教會大學中最中國化者,心竊慕之。及來,乃感大不然。入校門即見‘M’樓、‘S’樓,此何義?所謂中國文化者又何在?此宜與以中國名稱始是。”事后,燕大特開校務會議,討論此一意見。最終采納了錢穆的建議,改“M”樓為“穆”樓,“S”樓為“適”樓,“貝公”樓為“辦公”樓,其它建筑也一律賦以中國名稱。
錢穆在燕大教大一、大二國文。他以扎實的國學功底和妙趣橫生的演講,贏得了學生們的肯定和歡迎。但是執教一年后,錢穆終因不適應教會大學的環境,辭職南歸了。
當時的錢穆與顧頡剛兩人,在學術地位上相去甚遠,其研究方法、學術觀點等也不盡一致,但是顧氏對錢穆的學問非常佩服, 1931年3月18日,他給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寫信,極力推薦錢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顧頡剛在信中說:“……我想,他如到北大,則我即可不來,因為我所能教之功課他無不能教也,且他為學比我篤實,我們雖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對我補偏救弊。故北大如請他,則較請我為好,……他所作《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萬言,實近年一大著作,過數日當請他奉覽。”
錢穆終于到北大任教了。客觀地說,除了顧頡剛的鼎立相薦,這與文學院長胡適的首肯是分不開的。北大是當時中國最有名的大學,是錢穆心中長久向往的地方。他早年常以未能進入北大讀書為憾,此次能到北大執教,自然樂于接受。
“北胡南錢”
在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上,有兩位“但開風氣不為師”的思想家,一位是梁啟超,一位就是胡適。錢穆在蘇州時,就曾與到蘇州中學作學術演講的胡適見過一面。當時胡適是他時時充滿敬意、景仰不已的一代學人。錢穆對諸子學的研究,有不少得益于胡氏的啟發。而胡適對錢氏也“尊重有加”。錢穆在北大史學系講中國上古史(先秦史),有人問胡適關于先秦諸子事,胡適總是說可去問錢穆,不要再問他。
北大學風自由,教師在課堂上提出自己的觀點,學生常設疑問難,競相爭論。當時學術界討論老子問題日趨熱烈,胡適主張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問學于老子;而錢穆、顧頡剛則主張老子在孔子后。三位先生在課堂外大家互相討論學問,是朋友;在課堂中則把自己的學術主張灌輸給學生,并且當眾批評對方的觀點。比如胡適對錢穆的《劉向歆父子年譜》的考據謹嚴,十分佩服,常常對學生們做義務的宣傳;但是,在課堂上,他對錢穆等人的關于老子和《老子》一書的時代論爭,卻也慷慨陳辭,奮力抨擊。錢穆在講課中,也隨時聯系批評胡適的一些論點,常說:“這一點胡先生又考證錯了。”學生們或主胡說,或贊錢說,彼此爭論不斷。有一次,贊同老子晚出之說的同學認為胡適“在老子時代問題上有成見”,胡適憤然地說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會有成見呢?”不過他的態度仍很客觀,隨后又對同學們說,“在大學里,各位教授將各種學說介紹給大家,同學應當自己去選擇,看哪一個更合乎真理。”
錢穆在北大講授通史課,事實性強,不騁空論,有據有識,簡要精到,并能深入淺出,就近取譬。如他比較中西文化,喻秦漢文化猶如此室的四周遍懸萬盞明燈,打碎一盞,其余猶亮;羅馬文化為一盞巨燈,熄滅了就一片黑暗。當時錢穆將通史課的教室設在北大梯形禮堂,面積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滿,盛況空前”。課堂之大,聽眾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襯得下面講臺上穿著長衫的錢穆似乎更矮小了。但這位小個兒導師,卻支配著全堂的神志。一口洪亮的無錫官話,震撼了在座的每一位學生的心。他自己也說過,他上課“幾如登辯論場”。他對問題往往反復引申,廣征博引,使大家驚異于其淵博,更驚異于其記憶力之強。在北大,他與胡適都因以演講的方式上課而馳名學校,成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學生中即有“北胡南錢”之說。
分道揚鑣
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軍全面侵華。八九月間,日軍進占北大校舍。北方各高校紛紛南遷,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并,在長沙組成臨時大學。錢穆將歷年講授中國通史增刪積成的五六厚冊筆記裝入衣箱底層夾縫,在十月與湯用彤、賀麟等人同行南下,轉道長沙,開始了抗戰時期流轉西南八年的學術生涯。
與在北大時期一樣,錢穆在西南聯大主講中國通史,吸引了大批學生。他的《國史大綱》新義迭出,創見尤多,被定為全國大學用書而一紙風行。所以內遷西南的各個高校都紛紛請他講學。
抗戰勝利后,北大的復校工作開始緊張進行。南京政府任命胡適為北大校長。當時胡適遠在美國未歸,即由傅斯年代理校長之職,負責北大接收、復員和北遷事宜。當時舊北大同仁不在昆明者,均得到信函邀請返回北平,而錢穆卻沒有得到邀請。
傅斯年曾是國學大師黃侃門下的高足,也是胡適最得意的學生之一。他曾留學歐洲,被譽為史料學派的舵手,主張殷墟發掘,倡導“史學便是史料學”而名著當時。30年代,錢穆任教北大時,即與傅斯年相識。錢穆早年作為考據名家,被傅斯年視為史料考證派的同志,二人彼此往來問學,保持著不錯的關系。但是錢穆與他在學術觀點上又是同不勝異的。在錢穆看來,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將古代典籍拋之腦后,這做法與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樣有害,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西南聯大時期,隨著錢穆自己史學理論體系的日漸成熟,對史料考據派進行了全面批判。為此,作為學派領袖的傅斯年對錢穆的攻擊自然不會高興。北大復校,錢穆不在被邀之列,這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事實上,錢穆的見解與史料考據派的觀點并非絕對對立,兩者是可以互為補充的。然而,二者之間最終未能成為 “同志”,這種現象的確可引發近現代學術界的反思。
居港辦學
抗戰勝利后,錢穆重返北大的愿望因傅斯年所阻沒有實現,但是由于他早已名重學林,所以各高校爭欲聘他。他往返于昆明、無錫之間,在昆明五華學院、云南大學、無錫江南大學講學著述。 1949年春,在無錫江南大學任教的錢穆只身南下廣州,受聘于廣州華僑大學。是年秋,又隨華僑大學一道移遷香港。入港后, 錢穆與唐君毅、張丕介等人一道,懷著為中國文化延續命脈的真精神,在“手空空,無一物”的艱難困苦下,興發“千斤擔子兩肩挑”的豪情,在香港創辦了新亞書院,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頁。 錢穆講學七十余年,其中最艱苦,最忙碌,也最顯其精神的一段,就是在港辦學時期。錢穆居港辦學成績卓著,為港臺地區培養了大批學術人才,而且學問也不斷精進,先后完和和整理出版了 20多部學術著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老子“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人生態度和精神境界為錢穆所欣賞。當新亞書院加入香港中文大學( 1963年10月),成為中大三個基本學院之一,學校有了一個長久發展基礎的時候,蓽路藍縷、創辦新亞的錢穆卻毅然決定引退了。 1965年6月,他正式卸去了書院院長職務。 隨后潛心學術,再創學術新生命,寫下了五大冊的煌煌巨著——《朱子新學案》。
臺灣晚年
1967年10月,錢穆定居臺灣,開始了晚年居臺20多年的著述講學生涯。1986年6月9日, 92歲高齡的錢穆在外雙溪素書樓家中為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班的學生上告別杏壇的最后一堂課。在這堂課中,他殷殷寄語后學:你是中國人,不要忘了中國,不要一筆抹殺、全盤否定自己的文化。做人要從歷史里探求本源,要在時代的變遷中肩負起維護中國歷史文化的責任。諄諄教誨,感人至深。
錢穆自 1949年4月南走香港,就再也沒有踏上大陸的土地,再也沒有回過那塊生他養他的故鄉。但是他對神州故土的懷念,對那里的親人、師友的思念,卻沒有因兩岸的隔絕而減弱。1980年夏天,86歲的錢穆在夫人胡美琦的陪同下來到香港,與闊別32年之久的、在大陸的三子一女相見,海天相隔數十年,終于團聚。1984年7月,錢穆夫婦赴港參加新亞書院為他舉行的90壽慶活動,與大陸來港的子女團聚一月,享受天倫之樂。作為20世紀享譽海內外的著名學者,錢穆對兩岸的時局也十分關心。1986年,92歲高齡的錢穆發表《丙寅新春看時局》一文,他以一位歷史學家高遠深邃的識見,發表了對時局的看法,提出了兩岸和平統一的主張。他說:“我是研究歷史的,我更看重歷史的傳統文化精神。我所說的和平統一,是根據我一生鉆研歷史對傳統文化的了解言,這是我們的民族性。將來的中國,不論由誰一政府來領導,我認為如果此一政府違背了歷史文化傳統文化的民族性,恐怕都難以成功。”并對“臺獨”思想提出批評,認為“臺獨”主張是出自對中國歷史的無知,必無出路。此文刊出后,備受注目。
1990年8月30日,錢穆先生在臺北杭州南路寓所無疾而終,平靜安詳地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一刻。一代大師隱入歷史,享年96歲。
摘自《錢穆傳》 陳勇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文匯報》2002年5月14日(文中最后二部分有增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