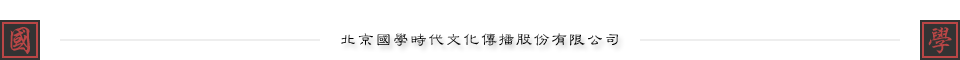學養涵厚襟懷遠大的一代學術大家——痛悼傅璇琮先生
首次得晤先生,是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此時,先生已譽滿海內。《唐代詩人叢考》、《唐代科舉與文學》、《黃庭堅和江西詩派資料匯編》、《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河岳英靈集研究》等一本本的開創性的或奠基性的唐詩學論著,使我對先生的學術成就和學術思想有了較多的了解,也產生更多的仰慕之情。九十年代中,我應邀在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任客座,得知先生亦在新竹的清華大學任教,幾次打算去新竹請教,皆臨時有事耽擱下來。直到有一天在臺灣大學不期而遇。自此兩人熟稔后,在臺北的近半年歲月中,先生不吝賜教,使我明白了大陸唐代文學各個學術流派的淵源、成就,代表人物的學術經歷,特別是各位名家的之間的學術碰撞、師承、以及學術個性,皆非紙上資料所能檢索覓得,非沉潛其中、深諳其道的長者所能述備。在其期間,先生又像識途老馬,領我穿越臺灣唐代文學研究的迷津、叢林,結識了羅聯添、楊承祖、汪中等一批古典文學耆宿和領軍人物,李善馨、彭正雄、邱鎮京等學海、文史哲、文津等臺北著名的文史類出版商。在臺大的校園里,在新坑的茶敘時,在“寧福樓”的宴請中,我得以了解到臺灣唐代文學的研究歷程,其中代表人物及其學術成果,尤其是臺灣古典文學優長與不足,兩岸學術的相似與差異以及各自特色,也獲贈相當一批臺灣學者的研究成果:專著和論文集,這都成就了我后來的那本《海峽兩岸唐代文學研究史》,為這本小書提供了最直觀也最可靠的第一手資料。
在臺期間,最能體現先生的學術胸懷、使命感和感召力的,是他和臺灣唐代文學領軍人物羅聯添先生共同發起編纂的《唐代文學論著集成》。這部論著分為“著作提要”和“論文摘要”兩大類別,主要反映近五十多年來我國兩岸三地學者唐代文學研究成果,其時間上限大陸和港澳地區為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臺灣自1945年從日本占領軍手中收復以來;下限至2000年二十世紀結束。入選對象是這個時段最富學術含量、最有代表性的論文和著作。由兩岸三地從事唐代文學研究的十五位學者共同參加選編撰寫。主編為先生和臺灣大學的羅聯添教授。大陸學者有安徽師范大學余恕誠教授、華南師范大學戴偉華教授、西北大學閻琦教授、廣西師范大學張明非教授、安徽大學陶新民教授;臺灣方面有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李豐楙研究員、東吳大學王國良教授、臺灣師范學大學王基倫教授、中正大學鄭阿財教授、彰化師范大學黃文吉教授、成功大學楊文雄教授;港澳方面則有澳門大學鄧國光教授。這部著作歷時五年,于2004年在西安三秦出版社出版,共八卷十冊,四百多萬字。據我所知,到目前為止,仍是兩岸三地合作進行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參加學者人數最多、成果卷數最多、字數最多的一次。這套專著的完成,從最初構想到發起組織,從編寫體例到審稿,乃至出版細務皆是先生親自過問操辦,因為經費并不充裕,編輯內容又不斷豐富擴展,很多家出版社都是開初滿懷興趣,最后婉拒。因此最后承印的三秦出版社也是先生反復磋商后才落實的。
這套論著,出版至今已八年,但從籌劃到編寫,先生所付出的種種努力,至今仍歷歷在目:
那是二十世紀快結束的最后一個冬季,先生正應新竹清華大學之邀在中文系任客座。一個星期天,學海出版社社長李善馨先生約我們去臺北市郊的一個風景區石碇小聚。石碇在臺北縣的東南,巍峨的皇帝殿拱衛其北,著名的玄奘大學座落其右,是一個自然風景、文化氛圍俱佳的游憩之地,臺北學術界一些同仁皆喜盤桓其間。善馨先生特意選了個既有山野小店風味又廚藝精致的“福保飯店”讓諸位歡聚。南國之冬,猶如中原之初夏,花木扶疏,綠草綿芊。當時在座的有傅先生夫婦,臺灣大學的羅聯添先生,東海大學的楊承祖夫婦,交通大學的詹海云先生,成功大學的楊文雄先生,李善馨先生和我。出于學者的習性,閑聊之中也不離本行。大家歷數近百年來學術大家及其成就,仰慕之中也深深為目前古典文學研究的困境而嘆息。尤其是五十年來的阻隔,使兩岸學者對對方的學術觀點、研究成果都極為陌生。記得當時傅先生曾舉臺灣中研院院士嚴耕望先生的《唐代交通圖考》為例,這部積三十七年心血而成的煌煌巨著,臺灣的專業人士幾乎無人不曉,大陸學者卻很少有人知道。羅先生也提到當時大陸正激烈爭論的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真偽,其原委始末,臺灣學者也不甚了了。基于如此現狀,傅先生覺得可否以唐代文學研究為窗口,兩岸學人先做一些溝通交流的具體工作,比如編一套論著提要,將大陸、港澳、臺灣五十多年來唐代文學研究中優秀的、富有代表性的著作和論文選編出來,分別寫成“提要”和“摘要”,使兩岸學人首先了解掌握對方學術思想和學術成果的精華所在。此倡議立即得到在座諸人贊同,羅先生答應臺灣方面由他出面張羅并任臺灣方面主編。聚會后,傅先生向我進一步解釋了他的設想:之所以選擇1949至2000這五十年,是由于上個世紀百年當中的后五十年是研究觀念變化最巨,研究隊伍波動最大,研究成果也最為豐碩的時期。從兩岸來說,也以這五十多年隔閡、疏離最巨,因此,我們先著手選編這后五十年。待是書發行廣泛聽取意見后,再積蓄力量,編選前五十年,以期把百年學術完整地交給后人。這既體現了先生遠大的學術眼光,也反映出先生不忘前人勛業又為后人著想的學術襟懷。正是這種襟懷和使命感,才使他主動承擔起這種“為他人作嫁衣裳”的既吃力,又繁難之務,當然這也是他一貫的為學、為人風格。因為傅先生一貫重視古典文學學術史的研究,一直強調中國的古典文學研究要走出去,要加強海外、國外的學術溝通和交流,要注意吸收新的觀念、新的手段來改造古典文學研究中的傳統觀念和研究模式。早在1982年的唐代文學首屆年會上,傅先生就鑒于當時國內唐代文學研究的迅速發展,發出了重視唐代文學學術史研究的倡議,對包括唐詩學在內的中國古典文學學術史作出整體思考;1992年,先生首次就任會長的第五屆唐代文學學會年會首次向海外開放,日本、美國、韓國以及臺灣、港澳地區的專家學者共35人參加了會議,占全部與會人員三分之一還強;2000年在武漢召開的第十屆年會上,傅先生著重安排討論如何加強唐代文學研究的海外和國際交流,在跨入新世紀之際古典文學如何適應信息時代的新變化和新要求。傅先生的上述呼吁和倡導,皆是出于改善唐代文學乃至整個古典文學研究的生存環境的緊迫感和使命感,皆是出于使古代文學研究向更完備、更有成效方向發展的深層思考,皆表現出先生擴大的襟懷和深遠的學術目光,就像先生在我那本小書《海峽兩岸唐代文學研究史》“序”中所說的那樣:“我們更應該進一步擴展視野,建立開放型的文學研究,把海峽兩岸唐代文學研究擴大到全球范圍。以唐代文學來說,我們應該研究唐詩、唐文是怎樣傳播出去的,特別是古代的日本、朝鮮,在接受唐代詩文后對本國起了什么樣的作用;另一方面,東亞及歐美各國從幾個世紀前到現在,是怎樣來研究唐代文學的。這對于我們來說,更是開拓學術領域,提高學術境界,使之成為中國文學的傳統研究與世界現代文明相關協調、相接軌的一條途徑”
先生對此不僅振臂高呼,而且也身體力行。眾所周知,先生在1980年出版的《唐代詩人叢考》,是新時期古典文學研究復蘇后的發軔之作,它不僅資料豐富、論證周嚴而聲聞海內外,而且在古典文學研究中倡導和開創了一個新的研究范疇和研究觀念。該書“前言”,第一句話就是:“若干年前,我讀丹納的《藝術哲學》,印象很深刻”,接著就提及丹納的詩人群體理論以及與地域之間的關系。接著,先生寫道:“由丹納的書,使我想到唐詩研究”:“唐代詩壇上,往往會有這樣的情況,即每隔幾十年,就會象雨后春筍一般出現一批成就卓越的作家群”,先生在其論著中亦著重就作家、作品與出現的時代、社會乃至地域的關系進行探討。在“序”也再次引用丹納對此的解釋:“個人的特色是由于社會生活決定的,藝術家創造的才能是與民族的活躍的精力成比例的”。也就是說,《唐代詩人叢考》的研究觀念和研究方法,其中一部分乃導源于國外的研究觀念和研究手段的吸納和創新。
圍繞這部《唐代文學論著集成》的編纂,先生在2000年春節前回大陸后,先是在大陸期間主持兩次編寫會議,參加編寫的各地的學者匯聚合肥和武當山下,討論落實大陸部分的編寫體例、編寫提綱,并寫出樣稿。傅先生對此逐一提出自己的看法,然后一一敲定。我則在2001年春節后又來到臺灣,在臺灣大學續做了一年客座。按先生的安排,將大陸方面的編寫體例、提綱和學者們的建議、意見帶到臺灣,將臺灣方面的編寫計劃按先生的想法,同羅聯添先生溝通,逐一落實。在臺灣也召開了兩次編寫會議。傅先生和大陸部分編寫人員余恕誠、張明非等也飛過海峽,一起參加研討。
隨著對先生欽佩的加深,上個世紀末,我一直有個想法,寫一本關于先生的學術評傳,一是作為一個世紀里,中國學術大家的一個縮影、一個代表;另外也讓先生的學術思想和成就在世界學術框架內有個定位。就像先生在上述的學術期待中所呼吁的那樣:“開拓學術領域,提高學術境界,使中國文學的傳統研究與世界現代文明相關協調、相接軌”。為此,在內地以及臺港、日、韓和德國訪學時也就此搜集了不少資料。只是想到先生春秋正富、碩果連連,想等一等再做總結,再加上手頭事情老是處理不完,就這樣拖了下來。新世紀開始后,先是收到傅明善先生的《傅璇琮學術評傳》,繼而是先生家鄉寧波出版的《傅璇琮學術評傳》,北京社科名家文庫編輯出版的《治學清歷·傅璇琮自選集》,安徽教育出版社的《當代學者自選文庫·傅璇琮卷》。我想,已無需我再蛇足了。但是,關于先生的道德文章,在讀過上述評傳、專輯后,仍感意猶未足,還是想強調一下我感觸最深的幾點:
首先,自然是先生獨具慧眼、扎實淵深的文獻學貢獻。朱熹曾感慨陸九淵的為學,提到“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鵝湖寺和陸子壽》)。我竊以為,先生的舊學新知、已達邃密深沉之境。只要讀過先生的《唐代詩人叢考》、《唐代科舉與文學》、《李德裕年譜》、《李德裕文集校箋》、《唐翰林學士傳論》等考論性文字者,都會得出如此結論。其中每一部專著,皆有學者寫過專評,作過專論,無須我再一一列舉。我只想談談我在閱讀時的總體感受:先生上述諸著,新見迭出,使我如見夜空中閃爍的繁星點點;其洶涌的思辨,又使我如臨先生家鄉邊萬頃波濤之東海;其文字的簡潔智慧,更使我如行山陰道上,山花滿眼,目不暇接。每讀一過,皆是一次莫大的享受。先生曾坦陳:“精思劬學,能發千古之覆”(《治學清歷》)這是先生的治學經驗,更是先生的治學精神,他是一種學術自信,更是一種人生境界。更需特別提出的是,對于先生,不存在寫作高峰期,而是一如既往、一以貫之,而且老而彌堅、老而彌深。譬如最近,我因為在寫《安徽文學史》,常翻閱先生等主編的《全宋詩》。發現我竭力從安徽的方志、碑刻和地方尚存的佚書殘卷中發現的資料,很大一部分早已被輯補到《全宋詩》這位作家的名下,如南宋華岳《翠微南征錄》今存詩10卷,391首。《全宋詩》又從明代《池州府志》、《貴池先哲遺書》以及劉克莊的《后村千家詩》中輯得詩26首。南宋小家徽州人程垣,有詩七卷,已佚。《全宋詩》則從劉克莊《后村集·跋程垣詩卷》、陳起《江湖后集》扒梳輯出14首。另一位南宋小家宣城人程炎子的《玉塘煙水集》,亦已佚。今存僅《江湖后集》收錄的詩作十六首,《全宋詩》又從嘉慶《寧國府志》輯詩一首。
其次,是先生敢為天下先的學術勇氣,“但開風氣不為師”的創新精神。比起先生扎實淵深的文獻學貢獻,我覺得這點更加可貴。因為前者,乾嘉學者、清末民初大家已經給我們提供了不少范例。而后者則是先生獨特的學術個性、學術眼光和學術貢獻,也是我們今日更為缺乏、更加需要的。先生在《李德裕年譜》的“自序”中,引用了法國作家雨果的一句名言:“藝術就是一種勇氣”。在后來出版的《當代學者自選文庫·傅璇琮卷》“自序”中,又再次引用了這句名言,并加上自己的體會:“真正的學術研究,同藝術創作一樣,是需要探索和創新勇氣的”。我們在先生的《唐代科舉與文學》、《唐翰林學士傳論》《唐五代文學編年史》等一系列享譽海內外的論著中,都可以看到這種學術勇氣和創新精神的張揚。如前所述,《唐代文學論著集成》是迄今為止兩岸三地合作進行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著中,參加學者人數最多、成果卷數最多、字數最多的一種。《唐五代文學編年史》亦是這種精神的體現和實踐。傅先生早在1980年出版的《唐代文學叢考》中,就有對當前文學史編寫現狀的不滿:“我們的一些文學史著作的體例,對于敘述復雜情況的文學發展,似乎也有很大的局限。我們的一些文學史著作,包括某些斷代文學史,史的敘述是不夠的,而是像一個個作家評傳,作品介紹的匯編”。接著先生提出自己的理論設想:“為什么我們不能以某一發展階段為單元,來敘述這一時期的政治經濟,這一時期的群眾生活和風俗特色呢?為什么我們不能這樣來敘述,在哪幾年中,有哪些作家離開了人世或離開了文壇,而又有哪些年輕的作家興起;在哪幾年中,這一作家在做什么,那一作家又在做什么,他們有那些交往,這些交往對當時以及后來的文學具有哪些影響;在哪一年或哪幾年中,創作的收獲特別豐碩,而在另一些年中,文學創作又是那樣的枯槁和停滯,這些又都是因為什么?”先生說:“我想,如果我們能這樣研究和敘述文學史,可能會使研究更深入一步”。二十年后,先生終于將自己的理論設想付諸實踐:主編了一套《唐五代文學編年史》。這套“編年史”的創新之處主要有兩點:一是不同于通常那種以鋪敘生平著述和議論評析成就為主的寫作模式,而是突出資料性和實證性,簡潔而實用。更為重要的是:它把唐代的文化政策、作家的活動、重要作品的產生,作家間的交往,文學上的重要論爭,以及相鄰的繪畫、音樂、舞蹈等藝術樣式,乃至宗教活動、社會風尚等,擇取有代表性者,逐年加以編排,以求“立體交叉”(《唐五代文學編年史》“自序”)地體現當時的文學全貌,并用文學發展和變化貫穿于全書的始終,從而為文學史的編寫提供新的思路和范式。其中顯露的亦是先生“敢為天下先”的理論創新勇氣。先生的《唐代科舉與文學》、《唐翰林學士傳論》也皆可作如是觀:《唐代科舉與文學》為我們提供許多唐代進士試的具體細節,似乎是細碎的考據。但正是這些細碎的資料如一個個環扣將唐代的進士與文學緊緊扣到一起,進而拓展到科舉與文人的生存狀態、精神面貌,再進而擴展到唐代文人所賴以生存的社會條件、時代氣氛,從而讓讀者感受到在科舉制度產生后的“一千三百多年里,沒有那一項政治文化制度像科舉制度那樣,在中國歷史上如此長久地影響知識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態”(《唐代科舉與文學》自序),從而在一個時代風貌的勾勒中完成從文學到社會,從文學文化批判到社會政治批判的飛躍。《唐翰林學士傳論》也同樣沒有停留在翰林學士一職的職責范圍、建制沿革,翰林學士們的任職經歷考辨等文獻學層面上,而更多地對他們的生存狀態、思想變化和文學交往等進行動態式研究,更多地體現人文思考,更多地展示宏闊的文化視野。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在一些學者視為能展示自己鉤沉考辨小學功力的考據類著作中,先生也能著重于創新精神和歷史的整體審視,如前面曾談到的《唐代詩人叢考》,先生在“前言”中作出了一種新研究體式的設想:要著重敘述這一時期的政治經濟、群眾生活和風俗特色,并將作家的交游、行跡、創作逐年編排于其中,以此來探討文學興衰的規律,從最闊大的視野來考察時代社會對文學的影響。在論著中,先生有意識地運用丹納的地域學說和詩人群體理論,“從文學藝術的整體出發”,通過扎實的考證論證了這批中小作家在唐代時代精神和詩歌風格形成中的作用,揭示了他們與詩人群體及地域之間關系。首開了群體研究之風,示范一種新的研究手段。從此,《關中士族與文學》、《大歷詩人研究》以及初唐宮廷詩人群研究、貶謫詩人研究、縣尉詩人研究、唐末香艷詩人研究、襄陽詩人群落研究、湖州文人集團研究、大歷時期江南地方官詩人群落研究等地域文學與詩人群落研究接踵而起,形成天下云合響應之勢。其振臂首倡之功,亦是上述創新思考的實踐。至于《李德裕年譜》,正如羅宗強先生所指出的那樣:“在對紛繁復雜的史料深見功力的清理中,始終貫穿著對歷史的整體審視。而且是一種論辯是非充滿感情的審視。這其實已超出一般譜錄的編寫范圍,而是一種整體的歷史審視了”(《唐詩論學叢稿·序》)。
第三,是在唐代文學學科建設和研究隊伍組織建設的杰特貢獻。
先生是唐代文學年會的第一屆常務理事,1984年第二屆年會上推選為副會長,1992年第五屆年會上擔任會長,直至2008年第十四屆年會上改任名譽會長。先生任職的這二十年間,是唐代文學學會成長最快、成果最豐、學術活動最為活躍的一個時段,學會也是國內所有的民間學術組織中隊伍最為壯大,影響最為巨大的組織之一。作為學會的領軍人物,先生的貢獻首先是對唐代文學學科建設既有前瞻性又有當前問題的針對性的規劃和建議上。1984年在西安召開的第二屆年會上,剛推選為副會長的先生就對學會會刊《唐代文學年鑒》的總體規劃提出四點設想:針對當時唐代文學研究的迅速發展,“應當抓住研究的新的趨向,如實地及時地把他們反映出來”;建立資料館,搜集國內外唐代文學方面的研究資料;創立唐代文學研究史;“充分注意、重視中青年研究者所作的努力,對他們近些年來的貢獻和成就要有充分的估計”(《年鑒工作要有一個總體規劃》《唐代文學研究年鑒1984》),這實際上也成為學會工作的主導方針和發展方向。在先生擔任會長的第五屆年會首次向海外開放,參加會議的港臺和國外學者達到三分之一,使唐代文學學會年會變為國際性唐代文學學術會議,從此,這種會議性質和參加成員比例成為唐代文學學會的一個定例。據我所知,每屆學會除總結檢閱兩年來唐代文學的研究成果,展望今后的研究方向和發展規劃外,還集中討論當時的一些研究熱點或重大議題,如在蘭州召開的第二屆年會即以邊塞詩討論為重點;在洛陽召開的第三屆年會著重討論了白居易和新樂府運動,唐代文學與洛陽的關系;在太原召開的第四屆年會會則重點討論了唐代的山西作家,以及學會如何組織人力完成一些唐代文學研究中的重大課題;在南京召開的第五屆年會是首屆唐代文學國際學會討論會,因此著重安排了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學者介紹本國、本地區的唐代文學研究情況,進行國際間學術交流;在廈門召開的第六屆年會則關注《全唐五代詩》和《全唐五代文》等唐代文學重大課題的編篡情況;在浙江新昌召開的第七屆年會則實際考察了“唐詩之路”;在西安召開的第八屆年會主要研討唐代文學學會的各分會和兩個會刊的活動及編輯出版情況,進行組織整合;1998年在貴陽召開的第九屆年會是二十世紀唐代文學學會最后一次年會,年會集中就二十世紀的唐代文學的研究成果進行回顧、總結和評價,并對唐代文學研究發展方向和研究方法的改進進行了探討和展望;2000年在武漢召開的第十屆年會,著重討論在新世紀如何加強唐代文學研究的海外流播研究和進行國際學術交流,古典文學在跨入新世紀之際如何適應信息時代的新變化和新要求。
學會讓學人矚目的還有一項工作,就是先生倡議發起并組織海內外唐代文學乃至整個古代文學研究者完成的一些“大型工程”,如1987年啟動,2005年完成的五冊《唐才子傳校箋》,由25位唐代學者參加;1999年發起,2004年完成的八卷十冊《唐代文學論著集成》,有大陸、臺、澳十五位學者參加;1988年發起,1998年完成的《唐五代文學編年史》,由五位學者歷時十年而成。這還不包括先生完成的《黃庭堅和江西派資料匯編》(1978),《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合著,1982),《唐人選唐詩新編》十三種(1996);作為主編之一的歷時十年的七十二冊《全宋詩》(1998),《中國古典小說珍秘本文庫》(1998),《續修四庫全書》(2002),七卷本《中國古典文學通論》(2005);十二冊的《書林清話》文庫(2005);四編、四十冊的《全宋筆記》(2008),以及《唐詩研究集成叢書》(1996)、《中國古典文學史科研究叢書》(1996),《宋登科記考》(2009),《中國古籍總目》“史部”、“叢書部”(2009)等。
時下,在民間組織過多,學術會議過濫,甚至變成拉關系、推銷自己或單位的平臺,許多務實的學者已不勝其煩、左右支絀之際,唐代文學的年會的通知仍要因接待條件有限,限制與會人數,年輕才俊也仍以能成為唐代學會會員而感到榮幸,這與學會的影響力和凝聚力密切相關,而這種影響力和凝聚力的產生,又與先生對學會工作的殫精竭慮、傾心盡力,與先生對學科建設的前瞻性與針對性,與先生作為領軍人物的氣魄和才具,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人格魅力關系極大。這種人格魅力,不僅表現在對整個唐代文學研究隊伍的集結、整合、提高,以及學科建設的組織、規劃、實踐上,更表現在關懷扶植后進、樂于揚人之美的愷悌君子之風,因而形成如水之歸趨、“天下人爭識其面”的凝聚力。這在一些中青年學者的回憶文章,如龔延明的《學界的風范:記傅璇琮先生二三事》、查屏球《鍥而不舍,予人以善》,戴偉華《興逐天梯上九重》、盧盛江《大氣彌海內,潤物細無聲》,吳在慶《我與傅璇琮先生的交往與學術合作》、伊永文《唯有德者能之》等心儀感激的述論,證明這已是天下共識。至于樂于揚人之美,我還想再舉兩個小例:一是《唐才子傳校箋》第五卷的出版。先生主編由中華書局出版的這本專著原只有四卷,第一卷出版于1987年,到1990年9月,原定的四卷本已出齊。但在這前后三年中,陶敏、陳尚君等學者陸續著文,對校箋中一些疏誤進行訂正。先生對此不但不忌諱回避,反而邀請這兩位學者專門為此著 “補正”,作為第五卷于1995年出版。此舉盡顯了先生只求有益于讀者、有益于后人的坦蕩的襟懷和樂于揚人之美的君子之風。另一件事是先生在《李德裕年譜》新版題記中,有段話涉及與他合著《李德裕文集箋校》的周建國先生:“這里我要特別提出的是,這次修訂,得力于周建國先生之助不少。他幫我通覽了全書,有不少問題是他發現的。周建國先生于八十年代在復旦大學做研究生時,就發表過關于牛李黨爭的學術論文,很有見地。近十年來,我們在李德裕研究上合作很有成效。他比我年輕,但治學上多有勝我之處”。有次,我與建國兄在安慶師院講學時相遇,晚上散步時我提到先生上面這段話。建國顯得很激動,對我說:“先生完全說反了,那段時間是先生帶領我做學問,也是我長進最快的時期。我還沒有來得及說感激,先生倒說起來了。難怪司馬遷會感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先生上述種種嘉言懿行,使我想得很多很多。他使我想到:一個學者,首先要有使命感,要有為學術、為理想、為蒼生,生命不息、奮斗不止,無尤無悔的悲憫情懷;他也使我想到:一個有作為的學者,還要有“敢為天下先”的學術勇氣和創新精神,要有探龍穴、采驪珠的斗膽,要有“發千古之覆”的志氣,更要有要高瞻遠矚的目光和“歷史的整體審視和把握”襟懷。傅氏學術之所以讓人仰慕、給人震撼,并不在于《唐代詩人叢考》考出了戎昱或李華的生卒年,也不在于《李德裕年譜》梳理清楚了李德裕一生的行止,甚至不在于通過《唐代科舉與文學》,讓人們更清楚唐代科舉與文學的關系。與這些學術上的具體成果相較,更在于那種敢于涉足前人尚未涉足的學術領域,善于發現前人未曾覺察或理解的某種關聯,從而給我們研究方向上的啟迪,方法論上的示導;他更使我想到:一位學術界的領軍人物,應該如何為人、為學,如何對待榮譽,如何對待異見,如何對待后進和后生。因為學術乃天下之公器,它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物樹立一個正人、正己、正天下的標準和尺度。作為執此公器的領軍人物,首先就必須作上述思考并以自己的言行作出答案。這在時下更顯得必要:因為在社會的急劇變型轉換和商業大潮的沖刷下,這個為學者們千百年所尊奉并形成學術傳統的信條正在不斷被撕裂和毀壞。我們生存的環境,總是在用各種不同的手段迫使或誘使學者偏離這個軌道,將名山事業的把握和操守上的自持讓位于浮躁淺進和急功近利:或是用商業炒作的方法來進行學術研究,或是用唯我獨尊和以圈子劃線作為學術評價的標準,或是以學術外的攻訐和手段置換正常的學術爭論,或是以庸俗的互相捧場取代嚴肅的文藝批評。面對新世紀的波詭云譎、物欲橫流,向先生那樣,不改學術人格、堅持學術操守來重鑄學術品格,以此獲得永恒的學術生命就顯得尤為重要。面對大千世界的光怪陸離、潮起潮落,絕不像被網民們卑之為“磚家”、“叫獸”那樣去“曲學阿世”;去爭名于朝、爭利于市,不時在媒體來個“訪談”、“博客”,圖個“臉兒熟”,混個人氣;既不迎合世俗以求“名”,也不操弄商機以求利;既不自吹自擂或互吹互擂“填補空白”、“重大突破”;也不浮躁淺薄處心積慮去制造“轟動效應”;既無門戶之見,又無輩份之分。這種學術人格的重鑄乃是學者的學術追求所必需,因為學術研究的終極目標是使人類愈臻善境,去預示和追求一個遠比現實更為美好的未來,所以學者首先就必須是個“善”者。這種學術人格也是我們深入了解研究對象所必需,因為作品與人品是密切關聯的。
這就是我由先生的學術人品所引發的思考!
今日,學養涵厚、襟懷遠大的一代學術大家離我們而去了,但這塊當代學術史上的豐碑會永遠矗立在中國學術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