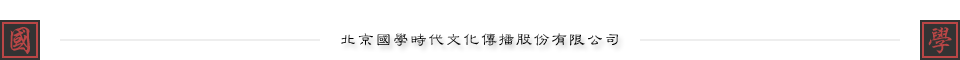王志清:我師傅璇琮
我之為學,最大的不幸是出非名校,從無名師。雖然,所幸的是還有不少大儒碩彥垂青于我。
傅璇琮先生,就是一個視我為嫡出而我視為業師的文壇大匠。
我2000年10月,才調入高校,一切都遲了,成為一個遲入的學界“古惑仔”。拙著《縱橫論王維》緒論的第一句話就是“我來遲了”。
因為學非正門,是個野路子,是個玩文字的雜家,且自甘于文字雜耍。故而,我的學問做不上去。即便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而做了點什么,也不能入人法眼。
特別難堪的是,參加學術活動,或是學者相聚而談時,讓我極其難堪。人家十分自豪地這樣地推介說:我是某某的碩士生,某某的博士生,后來又跟某某讀了博士后。
而我呢?出非名校,從無名師,無言以對,羞慚之極!
有兩回,我也想鼓起勇氣這樣認真地自我介紹說:我師傅璇琮,我是傅璇琮先生的學生。
可是,至今我終于沒敢說出口,生怕受人白眼,遭人恥笑。
你憑什么算是傅璇琮的弟子呢?中國傳統特別講究師徒名分,你行過拜師禮嗎?傅璇琮先生在清華大學帶博士,你考到先生門下了嗎?
嗨,都沒有。名不正則言不順也。于學術上似乎沒有個歸宿感。
我是傅璇琮先生的弟子嗎?我似乎也沒有了這份信心。
其實,我真是深得傅璇琮先生之垂愛的,他對我甚至比對他們的親弟子還要親。
我第一次走近傅璇琮先生,是2006年,在北京寬溝的北京市政府招待所,唐代文學的年會上。當時,傅璇琮先生是唐代文學學會的會長。
傅璇琮先生是我心儀已久的大儒巨匠,我戰戰兢兢地地走近傅先生。清晨,在如詩如畫的寬溝散步,巧遇也在散步的傅先生。我們似乎是同時向對方走去的。
看來,傅先生似乎也懂我的“底細”,也知道我沒有多少的“底氣”。可是,他沒有輕慢我,更沒有讓我感到一種居高臨下的、不值一談的蔑視。在比較深入的交談后,我貿然提出與先生合影的要求,先生非常爽快,讓我恭敬地與一個學術巨匠站在一個取景框內了。
這些年的學術活動,我接觸的學壇名家巨匠也不少,或者說,也大有讓我攀龍而附鳳的機會。可是,有些學者也只是稍稍有了點名氣,就把自己不當作人看了。因此,我便自覺地敬而遠之,與這些“腕兒級”的學者們至今抑或形同陌路。
傅璇琮先生是讓我走得最近的幾個大學者中的一個。我也是一個心氣頗高的人,是個自尊心極強的人,不是一般的人可以當得了我的老師,也不是一般人能夠讓我心悅誠服地呼其為老師的。
我是投師,不是投靠,更不是投機。因此,假如傅先生不是那樣的親切平易,假如傅先生不是那樣的熱心提挈后進,假如傅先生不是那樣的以學術為天下公器,我的個性是絕對不會讓我走近他的,更不會讓我對他生成五體投地的誠服的。
我走近了傅先生,雖然算不得“入室弟子”,總可算是個“記名弟子”吧。雖然沒有名正言順的“法定”的關系,但仿佛有一份心心相印、兩情相系的師生情緣,因此也有了鴻雁往來的溫馨交流。
2011年,接到傅璇琮先生八十華誕籌備組的邀請函,要我寫點與傅璇琮先生交往的回憶文章,也許是來者知道我與傅璇琮先生還有“那一層”關系吧。
我思來想去,覺得回憶錄,是不夠格的。我便回函曰:我寫篇賦吧。我要用賦頌我心中所仰止的高山。
2012年4月,賦成,題為《學壇大匠賦——為傅璇琮先生八秩華誕作》,即發給籌備組。籌備組旋傳給傅先生,先生讀后,馬上給我電話。通話的內容有兩層意思:一是說他沒有我寫得那么好;二是感謝我花了很大的功夫。
我平生第一次用賦來為人作頌。這篇賦,先后在《中華辭賦》、《中國辭賦》發表,后來又在香港的《華夏紀實》與《夏聲拾韻》兩個雜志發表,并收入《傅璇琮先生學術研究文集》,商務印書館2012年出版。
《傅璇琮先生學術研究文集》由傅先生的入室弟子盧燕新、張驍飛、鞠巖主編,分為三個部分,一、學術思想與學術成就綜論;二、著作書評;三、學術活動瑣憶。匯集了當下著名學者如周勛初、郁賢皓、董乃斌、余恕誠、趙逵夫、張明非、閻琦、陳尚君、尚永亮、戴偉華、吳在慶、陳友冰、王兆鵬、陶敏、李浩、蔣寅、陶文鵬、葛兆光、羅時進、胡可先、盧盛江、畢寶魁、張劍、杜曉勤、木齋、吳懷東、吳承學、張安祖、楊慶存、呂正惠、李德輝、傅明善、程國賦、竺岳兵等,都是些當下學界特別活躍的學壇中堅。我所以要將這些作者的名字一一掇列,意在說明傅璇琮先生的高度,說明先生是眾望所歸。
收入這部研究文集的,還有我的另一篇文章《傅璇琮的書序研究》。我文章原來的正標題是“領袖風范,人梯品格”。由于先生特殊的地位和經歷,也由于先生的謙遜而坦誠的為人,自然深受到學者們的衷心擁戴,自然形成了先生在學界的領袖地位。因此,學人們也都以傅璇琮先生序書為榮耀。傅璇琮先生的《學林清話》(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是一部序的匯編,全書共收序73篇。其中所序的著作有陳貽焮的《杜甫評傳》、鄧紹基的《杜詩別解》、吳汝煜《唐五代人交往詩索引》、孫映逵《唐才子傳校注》、陶敏《全唐詩人名考證》、郁賢皓《唐刺史考全編》、羅宗強《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陳振濂《宋詞流派的美學研究》序、曹道衡《中古文學史論文集續編》、趙逵夫《先秦文學編年史》、方勇《南宋末年遺民詩人群體研究》、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陳良運《周易與中國文學》等,其所序還有那些正年富力強的學者如陳尚君、程章燦、戴偉華、張宏生、程國賦、畢寶魁、胡可先、陳飛、劉明華等。筆者有幸,其中也收入了先生為拙著《縱橫論王維》寫的序。
璇琮先生因為學界的領導地位,接觸面廣,交游也多,朋友遍及學界的各地各個層面。另一方面,他又因為在學界任職多,自己還有很多大的研究項目要做,非常忙碌。但是,他的學術成就和學術地位,令年青學人高山仰止,求序者夥夥。作序這類事情,勞而無功,有些大學者往往是不愿做的。而傅先生卻義不容辭,大多樂意承擔。尤其是先生絕不敷衍,絕無逢場作戲或者東拉西扯的應付。很多書序,因為書的內容不熟悉,撰寫時甚感艱難,而需要先生反復研讀書稿。先生每作序前,必通讀原稿,于落筆之際,又慎重斟酌,且嚴守學術立場,不作空泛的虛美之論。先生的序中,往往都充溢著前輩學者對后學的熱切關懷與扶持的熱情。我們在其序中還讀出,有不少的求序者,原本與先生素未平生,而先生對于寄稿求序者,不論熟識與否,只要其書有可取處,都不遺余力予以褒揚,既充分肯定他們的新著所取得的成就,又不失時機地提出針對性意見以供參考,表現出可貴的學術度量和嚴正的治學態度。讀其序,即讀先生其人,真切感受到先生的思想學識、眼光胸襟、才情氣度,深深為他熱忱學術、真誠助人的精神所感動。
我與傅璇琮先生之間建立師生關系,不需要隆重的拜師禮儀加以確認。先生似乎也有了一份責任似的對我格外關照。2008年,我的《縱橫論王維》修訂再版,原序乃復旦大學陳允吉先生所作。我電話懇請傅璇琮先生為修訂版序書,傅先生肯定是為了激勵我的研究熱情,他不顧年老體邁而在半月內寄來新序。這讓我感激不已,即成長句以記錄當時的心情:
江湖誤入亂趨馳,欲取真經拜懿師。
仰乎燕許如椽筆,羨也韓歐革故詞。
且受西昆珠寶暖,更蒙東閣墨緣慈。
惶惶若我邯鄲步,不憾追風詩佛遲。
我所在的南通大學古代文學團隊,在學科帶頭人周建忠教授的號召下,人人于學術研究之余寫點散文的文字,承蒙周先生的厚愛,將收編成集的任務交給我。第一本散文集《文心雕蟲》是請中國散文學會會長林非先生作序。第二本《儒林心史》編罷,我便想到傅璇琮先生。傅璇琮先生非常爽快地滿足了我的要求。我在在《儒林心史》的后記中寫道:
先生年近耄耋,且手腳微有殘疾,行動不便,而接到書稿后的第二天即出差上海,旋即寧波,復歸北京。先生將書稿帶在身邊,沿途有暇時便隨即翻閱研讀,寫成三千字之序文。傅先生右手不便書寫,而手書竟達十頁,且字跡清晰,秀朗而不失遒健,誠可作硬筆書法之杰作收藏也,然而,其艱難程度也可想而知。先生之隆情厚誼,炙我深刻矣。
先生對我有求必應,讓我真切感受到他已經自覺地擔起了對弟子的一份提挈的責任。譬如,有些唐代文學的高端活動,先生也不忘了要我參加。2011年11月5日,杭州湘湖賀知章學術論壇在美麗的湘湖之畔舉行,來自全國知名高校的學者與浙江省內的本土專家約50余人。省外的專家是傅璇琮先生欽點的,就七八個人,陳尚君、孫昌武、陶敏、戴偉華、盧盛江,也讓我忝列其間。會議期間,我們去紹興旅游。紹興的臭豆腐乃紹興一絕,聞名天下。我是個臭豆腐的偏嗜者,行到炸臭豆腐處,饞癮難耐,呼同行者一嘗為快。傅璇琮先生也不破壞大家的興致,這么大的一個學者也跟著我們坐在紹興小弄的路邊上,邊說笑邊美食也。
我是個見佛便拜的人。行到一處廟宇,我恭恭敬敬地伏地三扣頭。同行者告訴我,看到你拜佛的那種專注,傅璇琮先生在你背后翹大拇指呢。我從未問及先生是否也信佛。我說不上信佛,更不是佛教徒,憨山大師說:“拜佛容易敬心難,意不虔誠總是閑。”拜佛求的是一種虔誠,清凈而不生妄念,以至于能夠始終保持一種恭敬之心與敬畏之心。拜佛,即拜自己。先生理解我心也。
先生雖然從未有過你要怎么、你必須怎么的諄諄教導,卻也真是把我當弟子看了,有什么特別高興的事情,給我電話,讓我分享他的喜悅。2012年元月,春節前夕,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與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長劉云山等下午要去看望傅璇琮先生。傅先生得到消息后給我電話,我從聽筒里聽到了先生天真無邪的笑聲。他不是炫耀,更不是賣弄,他是讓他的弟子分享,是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對知識分子關懷而感動。他甚至跟我商量,在家中接待行不行?先生家比較簡陋,也容不下七八個領導人的局窄,于是決定放在他曾經當領導的中華書局的辦公室進行。過了三四天吧,我即收到先生寄來的五張七寸照片,是與中央領導人交談與合影的照片。我很驕傲,拿著照片給幾個要好的朋友看,也覺得自己很有面子。
2012年11月3日,又是蕭山會議。這次會議的主題是“從義橋漁浦出發——浙東唐詩之路重要源頭研討會”。我成為會議的主要策劃者。外省的專家,是我點名的。請到傅璇琮先生,他一點也不矜持,外省學者中,還有董乃斌、陳尚君(訪日,耽誤,未到場)、蔣凡、吳在慶、羅時進、張中宇等。會前,傅璇琮先生早兩天出發,先去上海古籍出版社,再從上海到蕭山的。天氣預報,北京突遭寒流襲擊,雪下得很大。我自南通出發前,估計傅璇琮沒有帶上冬裝,便買了一件鵝絨衫帶去。傅璇琮先生試裝后,正合身,他很激動,我也很高興,不僅是因為傅璇琮先生到會,也有我的一份面子,而主要是我能夠盡我弟子的一份孝心。
2013年6月29日,收到傅璇琮先生寄贈的新著《濡沫集》(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3年5月)。我即去電話,表示感謝。傅先生不在家。從師母口中得知,他昨夜列車去上海了,應周勛初先生之邀,為《全唐五代詩》定稿的事。時間已是9點半,昨夜的火車,估計今晨6:30到,不知道什么原因,沒有給家中一個“平安到達”的口信?師母說:接站人的對話再打也不通。傅璇琮先生已是杖朝之年,且頸椎病嚴重,引起一手一腳的殘疾,抓握不穩,行動不便。他又不會用手機。聯系不上。怎叫師母不急的?
我是無意去電話感謝的,見師母干著急,便反復打那個接站者的號碼聯系。而打過去的反應是:“正在通話中,請稍后再撥。”將近一個小時,終于打通了接站趙先生的手機,然而,傅璇琮先生已經忙會去了,沒有說上話,便給北京久候而心懸不穩的師母報了個平安。
傅先生學問好,做人更好。尤其是平易近人,從不擺架子,給我的賀卡、或者贈書題簽都呼我為“摯友”,真讓我難以自容。南開大學古代文學學科帶頭人盧盛江教授曾給我說起一個細節,有一次,南開博士答辯,請他為答辯委員會主席,要派人去接傅璇琮,他不同意。但是,考慮到先生行動不便,就派了一個他的學生尾隨,達到保護的目的。結果,讓先生發現了,還發了脾氣。傅璇琮先生每年幾十次應邀外出的活動,一是不要邀請方接送,二是從不帶家屬到會。這讓我自然聯想到當下學界,有些年富力強的學者卻非常“排場”,不僅要求對方派專車接送,還往往帶上夫人,帶上子女,浩浩蕩蕩的一行。這么一比,讓人對傅璇琮先生要不感動也不行。
這幾年,我在學術上進步比較快,特別是在我走近了傅璇琮先生之后。
然而,我還是來遲了!
傅璇琮先生曾經主編《續修四庫全書》,續修并增補,參與工作的專家學者近千人,其量近兩倍于紀曉嵐主編的《四庫全書》。要不是我來遲了,我也肯定能夠忝列其麾下的。
傅璇琮學術曾經主編《全宋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共72冊,收詩人8900人,是全唐詩的4倍;總字數4000萬,是全唐詩的12倍。要不是我來遲了,傅先生肯定會邀請我參加的。要不是我來遲了,我也肯定能夠擠入其浩大的編寫團隊的。
傅璇琮先生曾經主持編纂《中國古籍總目》五卷,主編《唐才子傳校箋》與《中國古代文學通論》《中國藏書通史》等。要不是我來遲了,我也是肯定能夠加入其中而做點助手的雜事的。
哎,我來遲也!
即便是我來遲了,我也獲益匪淺,得利夥夥。
俗諺謂“投師如投胎”。傅先生這樣對我,真不知道還算不算我的老師?其實,我真沒有必要為我出非名校、從無名師而遺憾。在我的一生中,如同老師,勝過親師愛我助我影響我的老師,我還可以列數出一二十個來,難道我從無名師嗎?
我的書房“三養齋”,就是我的“名校”。我的那些很講究的書櫥里,裝滿了古今中外的學術名著,于是,我左右逢源而置身于頂級名師之中,我浸漬于并飽吮著營養豐富的學術乳液,我呼吸著自由創造的新鮮空氣。
我想,日后如果有人問起我的導師是誰,我也大膽向別人自我介紹:我的導師是傅璇琮!
抑或,我仍然不好意思這樣說。
但是,我從心底里卻是這樣確認了:我師!傅璇琮!
草于2013年7月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