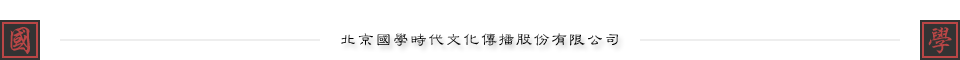王陽明的儒教風采
王陽明是中國第一個有人文精神的教育家,他的獨特教育思想基于鮮明的人文心學。王陽明在《大學問》中就把“心”界定為“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心學中的“靈明”,實際是指“良知”,即人的道德理性,也就是說,救世的法寶不是物質(zhì),而是人的良知和理性,教育的根本在于轉(zhuǎn)變?nèi)藗兊木袷澜纭?/p>
至樂之境
“至樂”即“孔顏之樂”,是王陽明一生追求的人生境界。“至樂”雖出自于“七情之樂”,但已是一種超越于此的崇高精神境界。這個“樂”就不只是一個情感范疇,更是一個境界范疇。他說:“樂是心之本體。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欣合和暢,原無間隔。”所謂“仁人”即圣人,作為心之本體的“樂”也就是圣人。陽明先生本名“守仁”,取自荀子的《不茍》:“君子養(yǎng)心莫善于誠,致誠則無它事矣,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
儒學中的“圣人”,是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并“怡神養(yǎng)性,以游于造物”。王陽明《自樂》詩云:“閑觀物態(tài)皆生意,靜悟天機入窅冥。道在險夷隨地樂,心忘魚樂自流形。”那種超越時空、消融物我的高度自由的精神境界,同時又是“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完全擺脫個人名利、貧富窮達的無私境界。這種境界是王陽明的立人根基,也正是“孔顏之樂”的精神實質(zhì),在其“樂”中,審美主體就實現(xiàn)了社會與自然、理性與感性、必然與自由的高度統(tǒng)一,達到了充實活潑的自由怡悅的“至樂”境界。
王陽明正是從這一“至樂”境界出發(fā),來闡釋善與惡、美與丑的。他認為美與善是統(tǒng)一的,美是“理”的感性顯現(xiàn)。他說:“禮字即理字。理之發(fā)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既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文也者,禮之見于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于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之,文也。是所謂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者也。”(《傳習錄》)
所謂“禮字即理字”,亦即“心”(良知)是體現(xiàn)為社會與天地萬物的準則,尤其是存在于心中的道德律令,即“《六經(jīng)》為吾心之常道”,就是善的內(nèi)容。這種“禮”是抽象的,理性的,不可見的。所謂“文”是“禮”的外在表現(xiàn),亦即良知在個體生命中的表現(xiàn)形式。而“文”在中國古典美學中,自先秦孔孟荀、《易傳》以致后來的劉勰等講的“文”,都已明顯地包含有“美”的意義。因此這里的“文”也就是美的內(nèi)容。
王陽明認為,作為理性內(nèi)容的善(禮)和作為感性形成的美(文)是統(tǒng)一的,“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也就是說,善要表現(xiàn)在美的形式之中,而美的形式同時也正是善的表現(xiàn),具有善的意義而非外在于善的東西。他說:“《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吾心”即良知、禮,是善的內(nèi)容,而樂、詩只能是“吾心”的外在感性形式。
同時,在他看來,“禮”存在于感性個體生命之中,是體現(xiàn)人的主體意識和人格精神的道德律令的,即對人的存在價值和意義的肯定。這里體現(xiàn)了中國美學從道德境界走向?qū)徝谰辰纾嗉催_到“天人合一”的“至樂”境界的重要特征。也正是從“至樂”境界出發(fā),他認定作為本然狀態(tài)的“良知”是無善惡、無美丑的。他說:“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才過當些子,便是惡了。不是有一個善,卻又有一個惡來相對待也,故善惡只是一物。”(《傳習錄》)
王陽明的心學,曾遭到權(quán)貴們別有用心地攻擊,被誣為“異端邪說”。于是先生理正辭嚴地進行了駁斥:“是故明倫之外無學矣。外此而學者,謂之異端;非此而論者,謂之邪說;假此而行者,謂之霸術(shù);飾此而言者,謂之支辭;背此而馳者,謂之功利之徒、亂世之政。”(《萬松書院記》)
為了解除心靈的障蔽,他提出“致良知”,要求人們應在“過與不及之處”多下功夫,以致“中和”,并使美丑、善惡自融。“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團圓永無缺”,顯現(xiàn)出心靈瑩徹的“至樂”境界。又說:“良知本來自明。氣質(zhì)不美者,渣滓多,障蔽厚,不易開明。質(zhì)美者渣滓原少,無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瑩徹。”(《傳習錄》)
自得之美
王陽明以為,教育兒童應根據(jù)兒童生理、心理特點,從積極方面入手,順導兒童性情,促其自然發(fā)展。他說:“大抵童子之情,樂嬉游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傳習錄》)。意思是說兒童性情好動,喜歡嬉戲玩耍,而害怕受拘束和禁錮,就像草木剛剛萌芽,順其自然就會使它長得枝葉茂盛,摧撓它則很快會使它衰敗枯萎。因此對兒童進行教育,必須注意順導兒童性情,不宜加以束縛和限制。他反對單調(diào)偏詁的蒙學,不贊成專重句讀課,而忽略意志的培養(yǎng)和情感的陶冶,更反對鞭撻兒童如同獄卒鞭撻囚犯一樣,使兒童視學校如囹獄、視蒙師如寇仇,致使教育適得其反。
為了達到倫常道德教化的目標,王陽明有《教約》規(guī)定。首先設置“考德”一門課程,并列在每天五堂課的第一堂,以顯示其重要性。因為兒童早起頭腦清醒,最易于接受蒙師的教誨和訓誡,最宜于反省自己的過失。課程的教法亦很特別,并非蒙師之一言堂,而呈現(xiàn)師生互動狀:“每日清晨,諸生參揖畢,教讀以次遍詢諸生:在家所以愛親敬長之心得無懈忽,未能真切否?溫清定省之儀得無虧缺,未能實踐否?往來循衢,步趨禮節(jié),得無放蕩,未解謹飭否?一切言行心術(shù)得無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篤敬否?諸童子務要各以實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教讀復隨時就事,曲加誨諭開發(fā)。然后各退席肆業(yè)。”這種方式有利于從小訓練其道德行為習慣。
在教學內(nèi)容上,王陽明主張給兒童以歌詩、習禮、讀書三方面的教育,陶冶兒童的思想和性情。一是“誘之詩歌”,他主張以唱歌吟詩的方式來教,這樣不僅能激發(fā)他們的志向,而且還能消除他們的頑皮,使其多余的精力有發(fā)泄的機會,也能解除兒童內(nèi)心的愁悶,使他們開朗活潑起來,并能適度地表達其情感。二是“導之習禮”,他主張以學習禮儀來教育兒童,使兒童養(yǎng)成一定的禮儀習慣,而且還能通過禮儀動作,“動蕩血脈”,鍛煉身體,健壯體魄。三是“諷之讀書”,他主張通過讀書,開發(fā)兒童的智力,增加兒童的知識,同時還能“存心宣志”,形成兒童的一定的道德觀念和理想。
王陽明充分地意識到各門學科的內(nèi)容和性質(zhì),以及學童的性情、興趣、注意力等精神心理因素的相關(guān)性,主動地做到調(diào)動各種積極因素,充分地發(fā)揮學童的主觀能動性,“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王陽明主張讀書不在貪圖數(shù)量之多,而在質(zhì)量之精熟,強調(diào)因材施教,留有余力,使學童在讀書之中獲得快樂感和成就感,這樣才能在循序漸進的過程中專心致志,熟讀理解,開其心智,陶情冶性。“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援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至于習禮、歌詩,具體的教學與練習,可通過觀摩、競賽的方式進行,在欣賞與交流的過程中提高學習興趣,潛移默化地使綜合素質(zhì)得到升華。王陽明的蒙學教育,正是通過情感、態(tài)度等非智力因素的激發(fā),做到事半功倍。
王陽明主張師生之間應以朋友之誼相待,提倡學生對老師直言相諫,教師應歡迎學生的批評,這樣可使師生雙方都能得到提高。他指出“凡攻我之失者,皆我?guī)熞玻部梢圆粯肥芏母兄酰磕秤谠馕从兴茫鋵W鹵莽耳,謬為著者從于此,每終認以思,惡且未免,況于過乎?事師無犯無隱,而遂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直不至于犯,而婉不至于隱耳。使吾而是也因以明其是,吾而也,因得以去其非,蓋教學相長也”(《傳習錄》)。先生除鼓勵學生“諫師”外,對學生也非常和善,毫無道學家的樣子。炎夏之時,學生侍坐于其身邊,雖有扇子,卻謹守禮節(jié)而不用,王守仁則親將扇子遞給他們消暑,并說:“對人之學,不是這等捆縛苦楚的,不是裝做道學模樣。”節(jié)日之間,王守仁與眾弟子歡聚宴會,席間師生談笑風生,無拘無束,一起表演節(jié)目,或演奏樂器,或舞蹈歌唱,或即席賦詩,體現(xiàn)了親密無間、融洽和諧的師生關(guān)系。
五行之喻
五行是中國古代的一種物質(zhì)觀,多用于哲學、中醫(yī)學和占卜方面。五行指金、木、水、火、土,大自然由五種要素相生相克衍生變化所構(gòu)成,隨著這五個要素的盛衰,而使得大自然產(chǎn)生變化,不但影響到人的命運,同時也使宇宙萬物循環(huán)不已。它強調(diào)整體概念,描繪了事物的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和運動形式。如果說陰陽是一種古代的對立統(tǒng)一學說,則五行可以說是一種古老的普通系統(tǒng)論。
王陽明有別于其他儒學家,在于強調(diào)生命本身的靈明體驗,包容儒、釋、道傳統(tǒng)三教思想,創(chuàng)造出特殊而新穎的“心學”面目。他在《傳習錄》中關(guān)于良知的教育言論,是富有形象的“五行”喻說,十分生動活潑。可以形成“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的循環(huán)狀態(tài)。
心如水,良知為水之源。陽明先生坐在水塘邊,旁有一水井,遂以之向大家勸說修學的道理:“與其為數(shù)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為數(shù)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窮”(《答陸原靜書》)。此喻看似因時因地而偶發(fā),若聯(lián)想到朱熹那首著名的“源頭活水”之有感詩篇,自然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水有行止,即為動靜。心靈的變化,也是如此。先生說:“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于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于寂然、感通也”(《答陸原靜書》)。先生又說:“人心是天,淵。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是一個天,只為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個淵,只為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今念念致真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了”(《門人黃直錄》)。他指出心靈的最大障礙,就是人的私欲。《論語》中子曰:“逝者如斯(水)。”先生加以闡發(fā):“然。須要時時用致良知的功夫,方才活潑潑地,方才與他川水一般;若須臾閑斷,便與天地不相似。此是學問極至處,圣人也只如此”(《門人黃直錄》)。他說流水的作用就是“激濁揚清”,即:“譬如奔流濁水,繞聹在缸里,初然雖定,也只是昏濁的;須矣澄定既久,自然渣滓盡去,復得清來。”(《門人黃直錄》)
心如木,良知為木之本。陽明先生一日出游禹穴,顧田間禾曰:“能幾同時,又如此長了!”范兆期在旁曰:“此只是有根。學問能自植根,亦不患無長。”先生曰:“人孰無根,良知即是天植靈根,自生生不息;但著了私累,把此恨戕賊蔽寒,不得發(fā)生耳”(《門人黃直錄》)。他說得好,“良知即是天植靈根”,是曰根本。先生說:“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發(fā)端處。抽芽然后發(fā)干。發(fā)干然后生枝生葉。然后是生生不息。若無芽,何以有干有枝葉?能抽芽,必是下面有個根在。有根方生。無根便死。無根何從抽芽?父子兄弟之愛,便是人心生意發(fā)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便是發(fā)干、生枝、生葉”(《門人徐愛錄》)。他巧將心靈的成熟與樹木的生長通融了。又說:“是分下學上達為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于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門人陸澄錄》)。這是樹木與治學的類比,同為一理。總之,先生說的一切,都是歸本溯源而已。“學者一念為善之志,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刊落。然后根干能大。初學時亦然。故立志貴專一”。(《門人薛侃錄》)
心如火,良知為火之光。“光”字從火,火能生光。所謂“明”者,太陽和月亮也。先生說“汝只要在良知上用功;良知存入,黑窸窸自能光明也。”先生妙以一日氣象比喻人世境界:“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怍,淡然平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巖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后,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zhàn)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門人黃省曾錄》)。他說追求良知,好比棄暗投明。“喜、怒、哀、懼、愛、惡、欲,谞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所有的,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著力斫,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雖云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云能蔽日,教天不要生云”(《門人黃省曾錄》)。陽明先生的遺言是:“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心如土,良知為土之藏。陽明先生說:“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這是一切生命的歸宿,所謂“返土歸藏”:“物動則萌,萌而生,生而長,長而大,大而成,成而衰,衰而殺,殺而藏,圜道也。”(《答季明德》)《周易》曰:“地勢坤,厚德載物。”心靈這個方寸之地,乃使萬物賴以生長。王陽明引用朱熹的話說:“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而水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一個人的誠信就像是五行之中的“土”一樣,默默無聞,沒有(浮華的)地位,沒有(顯赫的)威名,然而五行之中的水、金、木(等元素)沒有不依賴土而存在的。
心如金,良知為金之明。所謂鑒,水盆也;鏡,銅面也;皆可照人。唐太宗說:“以銅為鑒,可正衣冠;以古為鑒,可知興替;以人為鑒,可明得失。”陽明先生以為,良知如同明鏡:“圣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略無纖翳,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斫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為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即是無所住處”(《答陸原靜書》)。金者,鏡也。他以磨鏡、拂塵比擬儒學的存養(yǎng)工夫:“圣人之心如明鏡,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蝕之鏡,須痛磨刮一番,盡去駁蝕,然后纖塵即見,才拂便去,亦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答陸原靜書》)。磨鏡的過程,就是保養(yǎng)鏡子的應物不藏的性能,其中牽涉到人的變化氣質(zhì),乃至整體人格培育。陽明先生雖言“心上用功”,但其實著重的卻是“事上磨練”,在人情事變上磨練,在遭遇大故時磨練。
詩教之道
“潛魚水底傳心訣,棲鳥枝頭說道真”(《夜坐》)。陽明先生創(chuàng)立心學,畢生傳道,他說自己好比是一條自由的魚,一只快樂的鳥。講學是歷代大儒弘道的主要形式,這種精神真是可與日月同輝,流芳萬古。南大吉在稽山書院親設尊座,恭迎陽明先生并自稱門生,又以紹興府的名義,在恩師的故居上立陽明書院,會兩地講學,聚八方彥士,一時蔚為大觀。
盛大的講學中,陽明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四句教:“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這是他在晚年進行的一次思想變革,最終完善了“致良知”即心學體系,其核心是“良知”,即是天理,亦是道,可以解釋為人對于善惡的自我認識,是人所特有的能動表現(xiàn)。
于是,陽明先生闡明了良知即準則、即主宰、即睿智、即自覺、即自信的命題,他喜歡寫詩,特別重視詩教的作用,《詠良知四首示諸生》影響極大,這是將心比心的啟示與勸勉。其一:“個個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說明良知是求真,須自我更新。)其二:“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卻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指出良知是自知,須內(nèi)心省察。)其三:“問君何事日憧憧,煩惱場中錯用功。莫道圣門無口訣,良知二字是參同。”(點撥良知是修心,須自省覺悟。)其四:“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拋棄自家無盡藏,沿門持缽效貧兒。”(啟迪良知是睿智,須清醒獨知。)
詩句通俗明暢,而且富有理趣,可見先生施教的獨特風格。他啟發(fā)學生說:“不離日用常行內(nèi),直造先天未畫前”(《別諸生》)。詩句的意思是,那些平常說的大道理,就在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就在他們與身俱來的行為習慣里。先生還告誡學生:“改課講題非我事,研幾悟道是何人”(《春日花間偶集示門生》)。詩句意在說明,我的講學方法是鼓勵大家自主探討事物與尋求哲理,絕不是照本宣科的。
陽明先生的講學方式,令人想起孔子的杏壇,講學不是教書,可以不拘形式,除了正襟危坐的面授外,其他行走坐臥、飲宴游樂皆可。而且?guī)熒g可以互動,是交談式與討論式的,學生是人人暢所欲言,先生則善于啟發(fā)與點撥。正是:“講習有眞樂,談笑無俗流。”(《諸生夜坐》)
1524年八月中秋,師生歡聚一堂,酒酣樂盛,諸生各盡其興——投壺、擊鼓、舞劍、撥琴、賦詩、泛舟。先生即興吟《月夜》一詩:“處處中秋此月明,不知何處亦群英?須憐絕學經(jīng)千載,莫負男兒過一生。影響尚疑朱仲晦,支離羞作鄭康成。鏗然舍瑟春風里,點也雖狂得我情。”他對門生作了一番解說:“昔者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世之學者,沒溺于富貴聲利之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脫。及聞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乃豁然脫落。但得此意,不加實踐,以入于精微,則漸有輕滅世故、闊略倫物之病,雖比世之庸庸碌碌者不同,其為未得于道一也。諸君講學,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見此,正好精詣力造,以求至于道,無以一見自足,而終止于狂也。”此刻,陽明先生儼然是“吾與點也”的孔子了,他的晚年在紹興講學成為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
王陽明作為杰出的教育家,他有一套嚴格的師道與學理,詩曰:“古之教者,莫難嚴師。師道尊嚴,教乃可施。嚴師唯何?莊嚴自持,外內(nèi)合一,匪徒威儀。施教之道,在勝己私,孰義孰利,辨析毫厘。源之不潔,厥流孔而。勿忽其細,慎獨謹微;勿事于言,以身先之。教不由誠,曰惟自欺;施不以序,孰云匪愚?庶余知新,患在好為。凡我?guī)熓浚髓b于茲。”(《傳習錄》)
除了強調(diào)“師道尊嚴”,陽明先生還提倡三個重要的方法:一是“學貴自得”,需要得之于心;二是“循序漸進”,必須日積月累;三是“知行合一”,善于潛移默化。正是嚴師出高徒,所以他的弟子皆能身體力行。
原刊《紹興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