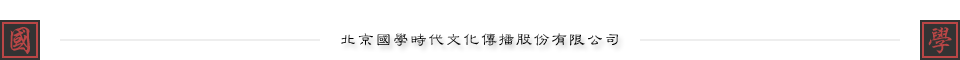劉咸炘《中書》思想研究
內(nèi)容提要:民國劉咸炘在“學為人也”的為學宗旨下,結(jié)合史學研究的客觀需要,創(chuàng)造出一系列概念,建立了一整套別具一格的學術體系和治學方法。本文將以《中書》為依托對此加以分析。
關鍵詞:劉咸炘;《中書》;執(zhí)兩用中;觀風察變;明統(tǒng)知類
作者單位: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甘肅蘭州 730000
一、劉咸炘的生平、學術大旨及其研究狀況
劉咸炘(1896—1932),字鑒泉,別號宥齋,四川雙流縣人,民國時期著名學者。曾歷任敬業(yè)書院哲學系主任,成都大學、四川大學教授。他在短暫的一生中著述頗豐,凡論著二百三十五部,四百七十五卷,總號《推十書》。(成都古籍出版社于1996年曾擇選其要選刊65部以紀念先生百歲壽誕)其內(nèi)容囊括文學、哲學、社會學、歷史學、物理學、方志學、校讎、道教研究、諸子研究等多項領域,書中精妙圓融之語甚多,往往發(fā)前人所未發(fā)。先生終其一生雖足跡未嘗出川,然而其學名卻早已為時人所推。廣西梁漱溟嘗語人云:“余至成都,惟欲至諸葛武侯祠堂及鑒泉先生讀書處。”[1]并轉(zhuǎn)載其《內(nèi)書·動與植》一文于《中國民族自救運動最后覺悟》中,作為附錄。修水陳寅恪,抗日戰(zhàn)爭時期來蓉講學,搜訪購買先生著作,遍及成都書肆,謂其識見之高,實為罕見。浙江張孟坸亦宗稱其著作“目光四射,如珠走盤,自成一家”[2]。鹽亭蒙文通與先生有雅故,嘗慫其重修宋史,亦謂“其識骎骎度騮驊前,為一代之雄,數(shù)百年來一人而已”[3]。錢穆在臺灣曾對學生說,若見劉咸炘的著作,“應仔細翻看”。[4]當代著名學者龐樸也盛贊“其文知言論世,明統(tǒng)知類,于執(zhí)兩用中、秉要御變之方法論方面,尤有獨特貢獻,為中國近代思想史上不可多見的學術珍品,值得仔細玩味”。[5]另外在成都古籍出版的三冊《推十書》的序文中收錄了著名學者蕭萐父、吳天墀、蒙默對其一生成就地位的評價,雖然以上三人均為四川籍,但他們絲毫沒有受鄉(xiāng)土之誼左右,多持中切當之語。
近年來,國內(nèi)研究“保守主義“學者的勢頭方興未艾,劉咸炘就是備受關注的一位。目前國內(nèi)劉咸炘研究現(xiàn)狀尚處在起步階段,水平也不是很高。國內(nèi)劉咸炘研究的中心在四川大學和西南大學,其次是武漢大學,另外在東南沿海(例如南京大學)也有學者從事該類研究。前年,關于劉咸炘研究的第一本專著《劉咸炘學術思想研究》問世,使得對劉咸炘學問的研究越來越向?qū)W術化方向發(fā)展。這本著作是四川大學周鼎博士的博士論文,其中多精言妙語,尤其是對于劉咸炘“道”這一層面的研究,堪稱獨斷。或許是先生學問體系過于龐雜抑或是周先生學力所限,該書亦有美中不足之處。首先劉咸炘的學問中最精華處在于義理與史法,作者卻只是偏重于對其思想源流的剖析,于先生史學一途言之甚少,甚至只是一言帶過而已,這樣就背離了先生“持兩用中”、“經(jīng)史縱貫”的治學大旨。也許是周先生認為劉氏之學就是“知行合一”的,故而只要把握其“道”,其術即可迎刃而解?其次,在先生看來史學、經(jīng)學與校讎學是密不可分的,在《學綱》中還被表示為“明統(tǒng)知類”甚至探尋經(jīng)義的關鍵。在本書中,校讎并未列入討論的范疇,這就使得“明統(tǒng)知類”四字顯得尤為突然。這些年來關于劉咸炘研究的論文也逐漸多了起來,主要有以下諸篇:1蕭萐父:《推十書》影印本序2.吳天墀:《劉咸炘學術述略》3.歐陽禎人:《劉鑒泉先生的“性說”研究》、《論劉鑒泉先生的“為學之法”》4.徐有富:《試論劉咸炘的成才之路》5.謝桃坊:《論劉咸炘的國學觀念與學術思想》6.王化平:《劉咸炘先生目錄學成就淺述》、《劉咸炘和章學誠的目錄學思想比較研究》7.劉復生:《表宋風,興蜀學——劉咸炘重修<宋史>簡論》8.周鼎:《邊緣的視界:劉咸炘對進化論的批判》、《文化保守主義與基爾特社會主義:從中心到邊緣》9.慈波:《別具鑒裁,通貫執(zhí)中——<文學述林>與劉咸炘的文章學》。另外還有一些在文史類雜志上發(fā)表的一些短篇論著,就不計算在內(nèi)了。通過對上述文章的考察,我們大致可以發(fā)現(xiàn)學者研究的角度多是一種“因事名篇”的態(tài)度,而這一點只能作為學術研究的第一步,并不是最終目的。我認為以后對劉咸炘的研究首先應該將其放在整個蜀學的大背景中進行,而不是僅僅就劉咸炘而論劉咸炘。其次,在論述劉咸炘的學源時應該更加注重其中蘊含的浙東學派的影響與“劉家道”思想之間的互動關系,這也是理解劉氏著作的一條路徑。最后,理解劉咸炘的學術結(jié)構(gòu)需要更多的借鑒同時代相關學人的著作加以佐證,比如柳詒徵的《國史要義》中就有好幾次提到劉氏史學,再者,張舜徽先生在其《史學三書平議》一書中就兩次引用劉咸炘的著作,再如蒙文通的《評<學史散篇>》、《道教史瑣談》等文章都曾載有劉咸炘的星星點點的資料,而將它們整理起來的任務正是我們以后努力的方向。
二、《推十書》與《中書》結(jié)構(gòu)分析
《推十書》是劉咸炘畢生學術的結(jié)集,共涵括各類書目凡二百三十一種,一千一百六十九篇,四百七十五卷,三百五十冊。劉咸炘在其《推十書類錄》一文自述了推十書修撰的目的及其構(gòu)成。他說:“舉心得以授徒,不得不著于紙墨,積久成冊,亦或刊行,或云著書,謹謝圣明。仿俞蔭甫《春在堂全書類要》之例,自定二目,使諸徒得以類求。凡分七類:甲綱旨。乙知言,子學也。丙論世,史學也。丁校讎。戊文學。均依《學綱》次第。已授徒書。庚祝史學·····甲子年定,乙丑年諸生編《系年錄》,復取此本增訂之,并雜作及札記未定者,亦存其目,并為辛壬二類。”[6]劉過世后,門下弟子徐國光和王道相所編的《雙流劉鑒泉先生遺書總目》中基本上沿襲了前者的劃分方法,所不同的只是后者收入了許多劉咸炘三十歲之后的文論,使得內(nèi)容上更加豐富罷了。
《中書》是整部《推十書》的開篇作。之所以名之《中書》,筆者以為有兩個原因:一方面是在稱謂上有所區(qū)別于《內(nèi)書》、《外書》、《左書》、《右書》。另一方面則是對其地位加以強調(diào)(劉氏主“執(zhí)兩用中”,故《中書》比其余各書更加接近劉氏學問的核心)。正如劉氏在《中書·自記》中寫道:“《中書》之名,對左右書而言也。《左書》曰知言,右書曰論世,如車兩輪,《中書》則其綱旨也。”[7]該書現(xiàn)存兩卷,凡十篇文論,分別是:第一卷:《三術》、《學綱》、《廣博約》、《一事論》,第二卷:《認經(jīng)論》、《本官》、《醫(yī)喻》、《左右》、《同異》、《流風》。它們是劉咸炘陸續(xù)完成的,其最終定稿時間大致在1927年12月左右(詳見《系年續(xù)錄》)。不過上述的篇目的確定也是由許多篇目省并增添而得的,關于省并篇目的具體經(jīng)過,劉氏在《中書·自記》中記道:“壬戌(1922年,劉氏時年27歲)八月始集十一篇刊行其目,一《知言論世》、二《明統(tǒng)》、三《本官》、四《言學》、五《經(jīng)教》、六《左右》、七《縱橫》、八《故性》、九《正命》、十《流風》、十一《流風余義》。其后復有《學綱》、《一事論》。又糅貫《言學》、《經(jīng)教》而增之為《認經(jīng)論》。繼作《醫(yī)喻》、《廣博約》。丁卯年十二月乃合而更定之,移《故性》、《正命》入內(nèi)書,除《流風余義》(實際上附之《流風》之后,名曰《流風附記》)。刪合《知言》、《論世》、及《明統(tǒng)》為三術,修改《左右》、《流風》(即附上《流風附記》),擴《縱橫》為《同異》,共為十篇刊之。”從上面的材料我們能夠發(fā)現(xiàn),《中書》的篇目變化很大。原本屬于先天論述的《故性》和《正命》兩篇被移入專論子學的《內(nèi)書》。這樣一來就使《中書》的先天論證就顯得很薄弱。故而劉氏就采取另寫《學綱》和《一事論》的方式來彌補這一點。有些篇目則由于擁有共同的終極追求而進行了合并,如統(tǒng)一于“學為人也的”這一旨趣的《知言》、《論世》和《明統(tǒng)》三章被整合為《三術》、以經(jīng)義為價值判斷的《言學》和《經(jīng)教》兩篇被合并為《認經(jīng)論》。另外,劉咸炘又根據(jù)具體的需要在原有的基礎上創(chuàng)作了其他篇目來對方法論和價值觀進行了細致論證。
筆者認為其變化正是劉氏學術思想逐步走向系統(tǒng)化的例證,同時也是我們把握劉咸炘學問構(gòu)成的一個楔子。[8]從上面的篇目上我們可以看到,劉咸炘在創(chuàng)作上并不全是隨手亂寫,而是有其內(nèi)在結(jié)構(gòu)的。這種結(jié)構(gòu)用劉咸炘自己的概念來說,就是一方面在內(nèi)容上具有鮮明的道器分工,另一方面在形而上層面上具有明確的“先天”和“后天”之別。《學綱》、《一事論》和《認經(jīng)論》是《中書》中的最重視“先天”人性論、并以“先天”人性論為基礎來強調(diào)先天人性論與后天方法論之間關系的部分,同時也是《中書》中形而上層面建構(gòu)的主體內(nèi)容(即論“道”的部分)。而與此相反,另外的章節(jié)主要是對上述三章內(nèi)容的具體操作層面上的方法論建構(gòu)和論證罷了。“先天”是道家的概念,一般認為是先天地而出現(xiàn)的,具體稱謂上常常被稱為“道”,屬于形而上層面上的內(nèi)容。與此相反,后天則是指先天所生發(fā)的一切,往往被稱為“器”,屬于形而下層面上的建構(gòu)。前者是基礎,決定著后者的存在形式及其存在的時空范圍;后者由前者生發(fā),對前者不斷在具體可操作層面上加以豐富和印證。 “道”與“器”、“先天”和“后天”盡管是不同層面上的兩對概念,但在一般情況下,每一對概念中雙方都是密不可分的,不僅在《中書》中是如此,甚至在整部《推十書》中也是如此,這一點劉咸炘自己也認識到了。劉氏在《三十自序》中寫道:“吾之學,《論語》所謂學文也。學文者,知之學。所知者,事物之理也。所從出者,家學祖考槐軒先生,私淑章實齋先生也。槐軒言道,實齋言器。槐軒之言,總于辨先天與后天;實齋之言,總于辨統(tǒng)與類。凡事物之理,無過同與異。知者,知此而已。先天,與統(tǒng)同也;后天,與類異也。槐軒明先天,而略于后天,實齋不知先天,雖亦言統(tǒng),止明類而已,又止詳文史之本體,而略文史之所載。所載廣矣,皆人事之異也。吾所究即在此。故槐軒言同,吾言異;槐軒言一,吾言兩;槐軒言先天,吾言后天;槐軒言本,吾言末而已。”[9]具體到《中書》來看,第一卷圍繞著《一事論》組織行文,第二卷則圍繞《認經(jīng)論》理論鋪陳。二者均是以儒家倫理為本位,針對于“學為人也”這一宗旨進行組織的,故而《一事論》與《認經(jīng)論》在“先天”層面的上是一致的。它們都是對劉咸炘學問的最終宗旨和形而上依托的所進行的交代,二者又通過《學綱》達成了從形式到內(nèi)在的統(tǒng)一。其結(jié)構(gòu)大致可以用以下模型表示。
↗左右 (執(zhí)兩用中)↘↖
→故性→正命→認經(jīng)論→明統(tǒng) →一事論(學為人)→ ←學綱
↘縱橫(觀風察變) ↗↙
儒家認為人稟天地氤氳之氣而生,在本質(zhì)上是和天地之道(先天)相合的,因而皆可以通過學習而達到圣賢境界。特別是后來理學強調(diào)所謂的“一本萬殊”,更是形象的將人和道溝通了起來,人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了達道之器。劉咸炘的祖父劉沅深受《性命圭旨全書》的影響,在儒家心性論的基礎上融合了道家“貴生”思想創(chuàng)立了劉家道性命雙修之大基。[10]劉咸炘更是將其自覺應用于治學的方方面面,這一點以《學綱》、《一事論》二文最為明顯。不過與劉沅不同的是,劉咸炘把“學為人也”的途徑更多的放在后天之學上。總體看來,后天之學主要包括史學和子學這兩個主體部分。兩者一橫一縱,一時間一空間,構(gòu)成了一個二元化的道器不離的結(jié)構(gòu)。在他看來史學是“御變”的對象,多是縱向?qū)用嫔系膶W問;子學則是各執(zhí)一端之詞,多是橫向?qū)用娴膿袢 W者通過對它們的把握可以全面地了解一個時期的精神風貌和文化主題。而從不管是從橫向?qū)用孢€是縱向?qū)用嬖诒容^擇取的過程中,自然會牽涉到同異之辨,正確處理的方法無疑是尋找一個合適的參照系。“執(zhí)兩用中”的出現(xiàn)就有了現(xiàn)實的需要。劉咸炘指出:“史子皆統(tǒng)于經(jīng),史衍經(jīng)各異之體。傳其外,猶子之于父,不必肖也。子分經(jīng)一貫之義,傳其內(nèi),猶弟于師,不必全也。”[11]二元結(jié)構(gòu)下的《推十書》基于涵蓋范圍的廣泛以及史學子學的天然分離,必然要求有一個形而上的原則將其統(tǒng)一起來。劉氏不談釋教,故而這一理論建構(gòu)的重任就落在老莊與儒學之上。然而他認為道家“出于史官,秉要執(zhí)本,以御物變”,盡管在諸子中最高,然而官失道裂后,卻不如經(jīng)過孔子整合后的儒家那么制度井然、張弛有度,再加上他認為儒家經(jīng)書在整個傳統(tǒng)學問體系中作用是無比尊崇的,故而引入儒家的“執(zhí)兩用中”來整合二者就自然而然了。這樣不僅與劉咸炘所堅持的儒家人性觀是相契合的,同時也是“明統(tǒng)知類”的現(xiàn)實依托(與章學誠的后天之學對六經(jīng)的尊崇相符)。與此相應,“觀風察變”與“明統(tǒng)知類”都是劉咸炘在具體操作層面上的創(chuàng)舉。它們與“執(zhí)兩用中”關系十分密切,三者是整部《中書》甚至整部《推十書》的核心觀念,也是《中書》中最重要的理論創(chuàng)造,更是溝通《中書》和《推十書》的紐帶。
三、《中書》中牽涉的主要概念及其分析
眾所周知,劉咸炘的學術思想一般都被歸結(jié)為“執(zhí)兩用中”、“觀風察變”、“知類明統(tǒng)”十二個字。這些詞大多可以直接在《中書》中找到劉咸炘對相應概念的闡釋,只是在具體的范疇的限定、各部分之間的關聯(lián)性的考量以及在劉氏學問體系中的定位上,學者多未論及或論述簡略,故補而述之。實際上,筆者認為這十二字不僅的確是劉咸炘學問上的獨特標識,更是劉咸炘在兼顧道器、統(tǒng)合先天與后天的需要。最好的例證具體到《中書》就是《一事論》中所講到的“為人之學”。此篇一開頭就講到“莫非人也,莫不學也,何以為人,何當為學,千萬方千萬年千萬人唯此一事而已。”[12]隨后劉咸炘更是直接引用劉沅的話“學者學為人而已,故雖窮研萬事萬物要以關于人者為的。”[13]對此加以佐證。接著他融合了傳統(tǒng)的“天人感應”學說與陽明學派的“知行合一”理念,再結(jié)合追求人自身的情意(即價值)的現(xiàn)實需要加以統(tǒng)合。這樣不僅使得“學為人也”這一目標理論性十足,也使得劉氏的學說具有深切的人本氣息,同時更加明晰了其學問構(gòu)成中的主次。劉咸炘更是廣泛借鑒了西方社會學、宗教學、哲學的基本理論,對傳統(tǒng)的“天人感應”、“知行合一”等諸多概念加以說明,不過劉的運用卻帶有明顯的以我為主,兼收旁采的味道,以至于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許多類似于錢穆等新儒家學者對中西文化比較所得出的論斷。
明晰了劉氏學問的主題,下面我們再對劉氏的一些關鍵性詞語進行界定。首先,“執(zhí)兩用中”,這里的“兩”狹義上指的即是《左右》章所講述的論點,具體到內(nèi)容上即是子史二學;擴充到整個《推十書》的理論體系中則指的是知言與論世的統(tǒng)一,不過這里的兩卻也包含御變的部分(實際上,論世本來就是“御變”的的內(nèi)容)。而“執(zhí)兩用中”實際上成為了劉咸炘最高的方法論。著名學者龐樸在其著作《淺說一分為三》一書中,實際上已經(jīng)對上述概念做了詮釋,只不過龐先生的解釋更加注重形而上理論建構(gòu)罷了。他指出:“中國式的思維方法不是一分為二的。一分為二只是她思維過程的一個階段。與分析相對,是綜合,中國哲學并不主張用綜合去取代分析,而是‘綜合’其綜合與分析,此之謂整體性思維。與天人相分相對,有天人合一,中國哲學也不用天人合一來排斥天人相分,而是‘合一’其合一與相分,這才是天人之學。就是說,再一分為二之后,還要合二為一。這個合成的一,已是新一,變原來混沌的一而成的明晰的一。在儒家叫做‘執(zhí)兩用中’;在道家,叫做‘一生二,二生三’,或者叫‘得其環(huán)中,以應無窮’。”[14]提到“中“必然會牽涉到一個概念,那就是執(zhí)“中”所需把握的“度”。著名美學家李澤厚在《歷史本體論》一書中指出,他認為“度”本身是人的一種創(chuàng)造,一種制作,是“人類學歷史本體論的第一范疇”[15],“從上古以來,中國思想一直強調(diào)‘中’、‘和’,‘中’、‘和’就是度的實現(xiàn)和對象化(客觀化),它們遍及從音樂到兵書到政治等各個領域。”[16]接著,李又進一步更加指出了“度”的重要性,將它看作是“生存、延續(xù)而維系族類的存在”(學為人也的來源)。劉氏的經(jīng)學理論盡管是作為核心價值觀出現(xiàn)的,但更多的卻只是道的層面上的建構(gòu),真正達道之器(即劉氏學問的主體)仍然是史學。甚至就連經(jīng)學在某種程度上也被劉咸炘融進廣義史學的大門(這一點或許跟劉氏師淑章學誠關聯(lián)甚大,他同樣推重六經(jīng)皆史的論斷)。因此這個“中”在思想構(gòu)成上可以看做就是經(jīng)學為主體的,進一步說就是原始儒家的價值標準為主要內(nèi)容的,而其直接服務的對象卻是史學本身。這么一來,不僅“執(zhí)兩用中”在體用層面上都得到了詮釋,劉氏撰寫《認經(jīng)論》的原因也顯而易見了。
如果說劉咸炘在價值上評判標準的建構(gòu)后,我們再來看看“觀風察變”,這一具體操作上的建構(gòu)。這里的“風”包括“時風”(時間)(縱向)和“土風”(空間)(橫向)兩部分。劉氏首先對“時風”與“土風”給出了定義。他指出:“氣象以下之感人心者為土風,群史之感人心者為時風”[17]。首先,上述兩個概念都是作為劉氏研究的具體對象被提出的,而非方法論的存在。劉咸炘指出:“今以學所研究之對象為類,凡三物二事。感于身者易知,感于心者難曉。今略注之,有直接感于心,有間接由身以達心。”[18]隨后,劉氏提出了自己對“感心者”的分類。實際上就是他對整個天人系統(tǒng)的豐富發(fā)展,更是他的認識論和知識論的集中體現(xiàn)。最終他得出“感于心者有三,欲究遺傳,即在本身心理中,故并本身遺傳環(huán)境,則為心理、土風、時風三科”的結(jié)論。[19]這段話包含了很深的中國傳統(tǒng)思維方式的影子,正如劉氏在隨后辨析中西哲學思維之間區(qū)別時所提到的內(nèi)容一樣,他認為“中西之異,在于分物合心,根本不同。中之哲學本主人生,以心御物,以理御事,以綜貫為長”。不管“時風”還是“土風“實際上都是以人的心理為依托的,或者可以說是人的心理決定著“時風”和“土風”的具體內(nèi)涵和表現(xiàn)形式。對于這一點,劉咸炘在論辯歷史發(fā)展的決定因素時曾指出過。他說:“……馬克斯遂謂一切皆決定于經(jīng)濟,其他各學者亦各張其門庭,或重生物之遺傳,或重地形氣候,至今言社會學者乃知根源在心。……反觀中國先哲則皆歸重心理。”對上述的材料的綜合考量后,我們能夠很清楚的找到鏈接“執(zhí)兩用中”與“觀風察變”的關鍵,實際上就是人的主體性存在(當然這也就是儒家性命之學的具體要求)。顯然“觀風察變”從可具體操作層面上解釋了劉咸炘的為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即“執(zhí)兩用中”和“觀風察變”的統(tǒng)一,這一點恰恰是符合“一分為三”的)。二者在內(nèi)容上統(tǒng)一宇宙之理(即人事學,本質(zhì)上即是“心理”),[20]而劉氏正是依靠對二風的研究來把握一時代的主題內(nèi)容以及其變化方向,正合蒙文通所謂“觀史當觀其波瀾處”[21]之意。劉氏更是撰寫了一系列專文來對其具體操作加以說明,主要都在專言史學的《右書》中收錄。其中內(nèi)容大多涉及士風變化與世風變化,其來源往往是劉氏在通識關照下所擇取的一個個典型事例或個人,能夠讓讀者一目了然的把握整個歷史大潮的走向。“風”的表現(xiàn)往往是駁雜錯亂的,一代有一代之風,甚至就連一代之風里也包含著不同的地域性差異(土風的空間作用),不過故而二者的具體操作上就需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材料擇取與編排方式,故而“明統(tǒng)知類”就應運而生了。
從來源上說,這一詞無疑是借鑒自章學誠的校讎學理論,對此劉氏也毫無諱言。[22]正如劉咸炘本人所說:“章先生之學至深者,一言曰‘為學莫大乎知類’。劉咸炘近以一言曰‘為學莫大乎明統(tǒng)’。類族辨物,必本于四象兩儀也。請略舉學文所得以明之。諸子統(tǒng)于老孔;校讎論文統(tǒng)于七略;史法統(tǒng)于三體;詩派統(tǒng)于三系。明于老孔而后諸子之變可理;明于七略而后四部可治文體可辨;明于三體而后史成體;明于三系而后詩合教。”[23]我們可以看出“明統(tǒng)知類”產(chǎn)生的直接動因是為學的需要,進一步說就是能夠更好的研究學問。而劉咸炘的學問主要是指統(tǒng)一于“學為人也”宗旨的史學與子學的兩個方面。[24]再結(jié)合《中書·學綱》一文前面的體系劃分來看,“史學”與“子學”實際上與“用中”和“御變”相對應的。因而“明統(tǒng)知類”就是對史與子的具體分析的需要,同時也是“執(zhí)兩用中”與“觀風察變”的在方法論上的具體表現(xiàn)。這么一來,三者之間的關系就顯而易見了。“執(zhí)兩用中”是更多的是價值層面上的界定,它不僅指導“觀風察變”的具體內(nèi)容,而且也是“明統(tǒng)知類”的形而上層面上內(nèi)容的直接來源。相應的,“用中”與“察變”是在明統(tǒng)知類的前提下進行的,而其中的“統(tǒng)”和“類”也是在方法論上融合二者的的介質(zhì)。“觀風察變”受“執(zhí)兩用中”的指導,立足于“明統(tǒng)知類”的基礎上,是作為與史學相應的方法論而存在的(不過這個史學的含義卻是混含史學和子學的)。這三者若是從內(nèi)容上以上來看,除了“用中”的一些內(nèi)容外,大部分是針對后天層面上的論述,它們的直接目標也是為了研究。不過若是從劉氏學問的主體來看的話,卻主要是以一個個人為依托的。而且劉咸炘在進行論證時經(jīng)常會從天人關系入手,對先天與后天進行整合,看似強調(diào)先天,實際上卻是在增加后天的可信性(當然這一點也是相互的)。這一點從他學問的構(gòu)成就可以清楚看到,主要是注重現(xiàn)實的史學(六經(jīng)皆史,而子學本來就是史學的內(nèi)容)。劉咸炘將三者均統(tǒng)一于“學為人也”的學問宗旨,以史學研究為直接動因,統(tǒng)合先天和后天,逐步建構(gòu)了《中書》甚至整部《推十書》道器合一的體系。
注釋:
[1] 劉伯谷、朱先炳:《劉咸炘先生傳略》(見《劉咸炘學術論集:文學講義編》,黃曙輝編校,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第358頁)。
[2] 同上,第358頁。
[3] 同上,第358頁。
[4]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0年,第270頁。
[5] 龐樸:《一分為三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頁。
[6] 劉咸炘:《推十書類錄》見《劉咸炘學術論集·文學講義編》,黃曙輝編校,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327頁。
[7] 劉咸炘:《推十書·中書·自記》,成都古籍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7頁
[8] 同上。
[9]劉咸炘:《劉咸炘學術論集·文學講義編·附宥齋自序》,黃曙輝編校,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327頁。
[10] 詳見周鼎《劉咸炘學術思想研究》第二章第一節(jié)。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08年1月版。
[11] 同上。
[12]劉咸炘:《推十書·中書·一事論》,成都古籍書店影印,1996年11月版,第11頁。
[13] 同上。
[14] 龐樸:《淺說一分為三》,新華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4頁。
[15] 李澤厚:《歷史本體論》,三聯(lián)書店,2002年2月版,第3頁。
[16] 同上。
[17] 劉咸炘:《中書·一事論》,成都古籍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16頁-第17頁.
[18] 同上,頁16.。
[19] 同上,頁17。
[20] 詳細參見《一事論》的分類。
[21] 蒙默:《蒙文通學記》,三聯(lián)書店,2006年11月版,第1頁。
[22] 劉咸炘:《劉咸炘學術論集·文學講義編·附宥齋自述》,黃曙輝編校,廣西師范大學出版,2007年7月版,第279頁。
[23] 劉咸炘:《推十書·中書·三術》,成都古籍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8頁。
[24] 劉咸炘:《推十書·中書·學綱》,成都古籍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