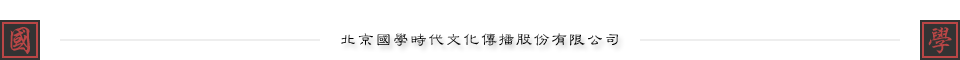《賈奉雉》與中國“仙傳”文學傳統
【內容摘要】《聊齋志異》中具有科舉批判意義的名篇《賈奉雉》沿襲了“遇仙-游仙-返回人間”這樣的情節模式,屬于中國“仙傳”文學傳統。“仙傳”情節模式形成于西晉葛洪的《神仙傳》,在唐人傳奇和明代擬話本小說創作中多有沿用,形成了一個穩定的文學傳統,《賈奉雉》屬于這一傳統中杰出的作品。它打破了以往追求長生和幸福的世俗化原則,具有《聊齋》小說所共有的“孤憤”情懷和現實批判精神,作家將個人情感和人生遭際融入其間,為“仙傳”傳統注入了前所未有的主體性和個性化特征。
【關 鍵 詞】仙傳;遇仙模式;文學傳統
【作者簡介】段宗社(1966-),陜西鳳翔人,文藝學博士,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主要研究中國古代文學與文論。
蒲松齡“搜神談鬼”(《聊齋自誌》)特色的創作無疑以中國志怪文學傳統為背景。在志怪文學傳統中,有一類“仙傳”小說,近年來為學界所關注。孫昌武先生指出,從西漢末劉向的《列仙傳》到西晉葛洪的《神仙傳》,這期間產生了眾多的神仙故事小說,都可以命名為早期“仙傳”小說,它們為后世小說中的神仙道化故事提供了大量可資借鑒的主題、人物事典和情節模式[1]。就情節模式而言,從漢晉“仙傳”小說、到唐人傳奇、明人擬話本小說、再到《聊齋志異》,存在著一個相對恒定的情節模式;以這樣的情節模式為標志,在中國文學史上存在一個“仙傳”文學傳統。《聊齋志異》中作為科舉批判名篇的《賈奉雉》正是這一傳統上最杰出的創作。朱一玄先生在《賈奉雉》的“本事編”中收錄葛洪《神仙傳》中的《呂文敬》、唐人皇甫氏《原化記》中的《采藥民》和薛用弱《集異記》中的《李清》,這些小說在情節上都有“遇仙-游仙-返回人間”這樣的恒定模式(簡稱“遇仙模式”)。聶石樵先生在《聊齋志異本事旁證》一文中就《賈奉雉》本事收錄了《呂文敬》一篇,并加按語云:“這類故事,神仙志怪等書中記載很多。賈奉雉在郎某的引導下去深山洞府的經歷,即在這類故事的影響下寫成的。但《賈奉雉》一篇的意義并不在此,而在于揭露科舉制度的腐朽和官場的黑暗,權貴之排斥忠良等。”[2](P365)代表了較為普遍的重視現實批判意義而輕視傳統文化價值的批評傾向。聊齋批評應在結構主義、“互文性”等理論觀念的啟迪下拓展新的視野。一篇作品不能單獨顯示意義,在與歷史上同類作品的比較中,作家的藝術匠心以及作品對文學傳統的獨特貢獻方能獲得透徹理解,應該把《聊齋》小說置于它所屬文學傳統中。本文擬先論述中國“仙傳”文學傳統及所確立的情節模式,再從“遇仙”模式出發對《賈奉雉》作具體解讀,最后論述這篇小說在“仙傳”文學傳統中所達到的藝術高度。
一
中國人之神仙意識起于長壽的渴望與祈求,《山海經》中“不死之國”、“不死之民”的記載所顯示的“不死”觀念即神仙說的濫觴。屈原《遠游》為游仙詩的雛形:“聞赤松之清塵兮,愿承風乎遺則。貴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楚辭章句》卷五)赤松子傳說是掌管風雨的天神,炎帝的女兒曾追隨他成仙而去[①],屈原也渴望追隨赤松子成仙。《淮南子·道應篇》秦代術士盧敖游歷北海時遇見仙人若士,并與之交談,為較早的遇仙故事。從魏晉時代開始,中國進入“新神仙思想”[②]建構時期,“遇仙”、“游仙”成為民間最普遍的想象模式,“成仙”遂有了一個簡單契機,即不用服食和經歷繁瑣的修煉,亦無需高貴的帝王身份,只需與仙人相遇、游歷仙界而最終成仙。葛洪《神仙傳》諸多故事即在表明“神仙可得,不死可學”(葛洪《神仙傳序》),其中《呂文敬》一篇即為“遇仙-游仙-返回人間”模式的最早最完整的形態。由于以“遇仙”為最初契機,本文擬將這一情節模式簡稱為“遇仙模式”。
《呂文敬》講少而好道的呂恭(文敬)帶一奴一婢在太行山中采藥,在山谷中遇三位仙人,問他:“子好長生乎,乃勤苦艱險如是耶?”追隨仙人兩日得到“不死之方”,后告辭回鄉,仙人告訴他:“公來二日,人間已二百年矣。”呂恭回家,見到自己后世孫呂習,傳授神仙方藥給呂習,呂習“服之即還少壯”,而且“子孫世世不復老死”,呂恭自己重回山中,不知所終。這個故事凸顯了成仙是否要“勤苦艱險如此”的問題,把“不復老死”托付給簡單易行的“遇仙”,正是“新神仙思想”所強調的平民化、世俗化想象特征。在稍后出現的著名的《天臺二女》中,世俗想象甚至有了浪漫特征:劉晨、阮肇在天臺山采藥迷路,所遇不僅是神仙,而且還是兩位絕色仙女,賜予佳肴,同帳而眠[③]。“仙傳”模式演為“艷遇”傳奇,為后來《游仙窟》等唐人小說所本。最早把“仙傳”模式當作學術問題研究的學者是陳寅恪先生,他以為元稹《鶯鶯傳》即是初唐《游仙窟》那樣的神仙故事模式,張生對崔鶯鶯始亂終棄包含著一個古老的情節原型,即來自人間的男性主人公要離開仙境返回人間,結局必然是分離。《聊齋志異》卷三《翩翩》即直接套用劉、阮故事模式,寫浪蕩子羅子浮與洞府仙女翩翩的艷遇與交歡,最后生育一子帶回人間。《賈奉稚》也兩次提及天臺劉、阮。說明蒲松齡對漢晉神仙故事比較熟悉,遇仙模式自然會采用到自己的創作中。
由“仙傳”演繹的“艷遇”傳奇至中唐《鶯鶯傳》徹底人間化,成為唐傳奇中進士故事的一部分,其中“仙傳”痕跡已與世俗場景融合,演變為純粹的文學敘事;《聊齋》中也有眾多書生與鬼女、狐仙相遇交歡的故事,亦與遇仙模式存在著間接的關聯。而另一方面,在日漸成熟并繁瑣化的道教觀念的推動下,神仙小說繼續在道教的方向上發展,而且融合了眾多的民間想象。與葛洪《神仙傳》相比,中唐《采藥民》、《李清》等篇中由神秘山洞通達的神仙世界已經演化為一個國度,有村落、城池以及由金玉做成的宮闕,玉皇是這個國度的統治者,神仙想象導向幸福烏托邦的建構。諸多故事不管場景與細節如何變化,“遇仙-游仙-返回人間”這樣的情節卻被不斷重復。
那么仙游以后為什么還要返回人間?日本學者小南一郎推測這與流行于當時的再生觀念有關。如張華《博物志》記載“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時冢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卷七)再生觀念又可繼續上溯到古老的“祖先顯靈”觀念:死去多年的祖先會通過某種方式在人間顯現他的蹤跡,以接受后人對他的供奉祭祀[3](P183-185)。借用具有濃厚民間化色彩的遇仙模式,作家蒲松齡卻完成了具有強烈主體性和個人色彩的創作,這正是民間模式和文人情懷的融合。
二
在傳統仙傳小說中,主人公與仙人相遇的契機往往是“好服食”或喜長生之術。而在《聊齋志異》中,“遇仙”被安排在人生困窘之時,遇仙故事以悲劇情調展開,這正是有異于世俗化想象文人情懷的體現。《翩翩》中羅子浮,“十四歲為匪人誘去作狹邪游”,原在金陵娼妓家留戀往返,后因金錢耗盡又“廣瘡潰臭”,被驅逐出門,只好沿路乞討,又羞于回家,日暮黃昏之時在一座破廟前遇到仙女翩翩,引入洞府。而賈奉雉的現實際遇是“才名冠一時,而試輒不售”,才華出眾卻無緣功名。“途中遇一秀才”,賈邀他回家,拿出自己的科舉制藝求教于郎生。在看過賈的制藝后,郎生“不甚稱許”,說:“足下文,小試取第一則有余,闈場取榜尾則不足。”“闈場”為縣、府、道“小試”之后的在京城舉行的朝廷高級別考試,考中即可授官。郎生這段評語其實正是蒲柳泉先生對自己科考命運遭際的冥想,也飽含著作家深切的“孤憤”,從而使《賈奉雉》成為最具有作家個人色彩的篇章。順治十五年(1658年),蒲松齡19歲,“應童科之試,以縣、府、道三第一,補博士弟子員,受知于山東學使施愚山,文名籍籍諸生間。”[4](P11)本來是科場上最有希望的人,但以后歷經無數闈場,一直榜上無名,直到72歲才出為“康熙辛卯(1711年)歲貢”,得了一個鄉貢生的空頭功名。為什么會出現“小試第一”而“闈場不中”的情形呢?因為“闈場”文章自有格局,而這樣的格局文章正是作家和他的正直的主人公所鄙棄的。郎生意味深長地告訴他:“君欲抱卷以終也則已;不然,簾內諸官,皆以此等物事進身,恐不能因閱君文,另換一副眼睛肺腸也。”決定士子命運的那些考官都是以濫俗的格套文章晉身的,他們自然也會以濫俗的格套決定誰的文章入選,不會另換一副眼睛肺腸的。這句話出自郎生之口,也是作家對自己半生困頓的痛切反思。這年秋天賈又一次落榜。過了三年,又一次“闈場”將近,郎生出現,拿出所擬的七個題目,讓賈作文,幾次都不合郎生之意。而當“賈戲于落卷中,集其阘冗泛濫,不可告人之句,連綴成文”,郎生才稱許說“得之矣”,讓他熟記勿忘。但言不由衷之句,轉瞬即忘,郎生只好在賈奉稚背上畫符,這次賈奉稚在闈場只記得那些爛俗文句,隨手寫出,而榜發之日,卻“高中經魁”。這樣的結局讓人哭笑不得,之所以如此,正如《司文郎》(卷八)中盲和尚所云:“仆雖盲于目,而不盲于鼻;簾中人(考官)并鼻盲矣。”在《司文郎》中,余杭生的文章讓盲和尚聞之作嘔,卻以此高中;而那些沁人心脾的文章,卻被黜落下第,讓人不能不感嘆“文運顛倒”。作者將此種局面戲稱為:“梓潼府中缺一司文郎,暫令聾童署篆,文運所以顛倒。”作者幻想有位賢明的“司文郎”稱任此職,使“圣教昌明”。《賈奉雉》中的與賈共賞文章神仙以“郎”為姓,當是作家“司文郎”幻想的延伸。但作家沒有想到,文章學術一旦有關于功名利祿,定然會黑白顛倒、良莠不分,神仙都難以扭轉。在郎生和賈奉雉簡約明快、妙趣橫生的對話中,作家以絕佳的立意表明,科舉原為選拔賢能,卻不幸惟以“阘冗泛濫,不可告人之句”方能入選。不惟無以為國選取英才,且使士人道德良知敗壞殆盡,人格缺損;病態士林,即由此造端。從表現方式上看,作家在這部分用的是一種類似于 “荒誕”(Absurd)的手法。科舉制度在明清時代已墮為一種怪誕百出的制度,而不管在《司文郎》還是《賈奉雉》中,作家都沒有直接的揭露,而是借助仙人的參與,有意通過有些夸張的荒誕故事來揭露制度的荒誕。荒誕場景中的郎生,本可以直接施以法術讓賈高中,但作者有意讓兩人切磋制藝以延宕情節。無所不能的神仙在這個故事中成為專心應付人間科考的書生,郎生亦由此獲得了一種人間化的人格魅力,與以往“仙傳”小說中的神仙不同。
賈奉稚以為憑這樣的文章博取功名,實為“以金盆玉碗貯狗矢”。“無顏出見同人”,遂有“遁跡山丘,與世長絕”之意。郎生第三次到來,帶他離開塵世,來到一處別有天地的洞府。賈奉雉之遁世,并不具有世俗化的長生欲求,而具有中國隱逸文化傳統的典型特征,即“隱居以求其志”、“回避以全其道”(范曄《后漢書·逸民列傳》),作家以其特有的文人情懷改造了對世俗文學傳統。所以小說并沒有展示“洞天福地”的歡樂祥和,他所到達的地方無窗無門,唯有一幾一榻,凄清冷落,大有蘇軾所謂“高處不勝寒”的意味。賈奉雉初來乍到,拜堂上孤坐的老叟為師,老叟告誡:“汝既來,須將此身并置度外,始得。”賈在洞府精舍只過了一夜,而人間以逾百年。這一夜中,賈經歷了兩件事,一是一只老虎來到床前,“遍嗅股足”,雖然有些驚駭,但依然能夠“收神凝坐”。佛教“舍身飼虎”的故事在中國民間流傳久遠,作家在此處構想出老虎“遍嗅足股”,而賈不為所動,表明他可以如洞府老叟所告誡的那樣“將此生并置度外”。二是老虎離去后“又坐少時,一美人入,蘭麝撲人,悄然登榻”,賈奉稚依然能夠做到“瞑然不少動”,但后來終于發覺,美人正是自己的愛妻:“因賈出門不相告語,頗有怨懟。賈慰藉良久,始得嬉笑為歡。”但明倫評云:“神仙可學而成,無奈臟腑空明以后,又有許多驚怖,許多阻撓,許多牽纏,許多掛礙,情緣道念兩相持而不能下,久之久之,洞府清潔之地,變為房幃狹邪之所矣。自己不能做主,愛我者又豈能為力乎。”(見張友鶴匯評本)似乎在責備賈奉雉的靜力不足,不能持守。但他哪里知道,在作家蒲松齡的現實生活世界,也有一位讓他最難以割舍的愛妻劉氏。劉氏十五歲嫁到蒲家,溫謹寬厚,頗得翁姑憐愛;兄弟分家后,“松齡歲歲游學”,劉氏一人帶長子住在所分的三間老屋中,夜晚豺狼進入院落,雞飛豬竄,劉氏一個人守著紡線的孤燈等待天亮。后來在畢際有家坐館,也不能常相陪伴。劉氏71歲病逝,蒲松齡作《述劉氏行實》長文[5](P301),讀者可以看到劉氏一生的辛勞和作家的愧疚與感念,這份情感無疑會投射到《賈奉雉》中。賈在老虎和美女面前都可以不動心,但在妻子面前卻“不覺大動”,終因不能置妻子于度外而破了洞府規矩;妻子被郎生帶入仙界,在現實世界中長眠不醒,共享延年;重返人間后“攜夫人去,設帳東里”,最后升仙時妻子被“引救而去”,一起仙化。——小說中賈奉雉不管落魄鄉里,還是顯達士林,都執意與妻子為伴,其實無不是柳泉先生對愛妻劉氏深情厚意之投影。
當“夜以向晨”之際,忽然聽到老叟責罵聲,妻子只好越短墻而去。不一會,老叟當著賈奉稚的面杖責郎生,對賈下了逐客令。仙界一夜,人間百年。西晉以來神仙故事仙界人間的時間對比模式是游仙而延壽幻想的最現實的表現方式。游仙者如果常駐仙界,不與人世溝通,則人世不知所終;惟有回到人間,游仙成果才得以驗證。而在《賈奉雉》中,作家顯然并不在意于長生和仙界的幸福安樂,所以呈現了一個凄清世界和嚴厲的老叟,并讓妻子的到來成為主人公離開洞府的機緣。
賈奉雉返回的是一個“窮踧”困頓的人間。夫人大睡不醒數十年,月前忽醒。長孫已經去世,次孫也已五十余歲。家口眾多,“苦無屋宇”,度日艱難,雖然有長孫媳婦吳氏苦心供奉,但終不免捉襟見肘。賈只好“攜夫人去,設帳東里”,在鄰村做了教書先生。后來又“復理舊業”,參加了當年的科考,“連捷登進士第”。“又數年,以侍御出巡兩浙,聲名赫奕,歌舞樓臺,一時稱盛。”做到兩浙巡撫這樣的高官。加官進爵是苦戰闈場的目標,而目標實現又會怎樣呢?一是次孫的六個兒子都成為無賴,“橫占田宅,鄉人共患之”。其中一位曾孫奪人新婦,被狀告收監,和次孫一起病死監中,這是做官帶來的家庭悲劇。二是官場上有過節的同僚借機群起而攻之,賈被朝廷革職充軍遼陽,這是做官帶來的人生悲劇。這種讓人有點哭笑不得的結局揭示了官場與闈場一樣,是一出荒誕劇、滑稽劇。賈慨嘆:“十余年富貴,曾不如一夢之久。今始知榮華之場,皆地獄境界。”小說在結尾處徹底消解了中國讀書人苦戰闈場以求榮華富貴的意義。知識分子自古糾結不清的入世與出世的抉擇借助仙傳模式而展示為形象場景,最終的成仙而去基于隱逸傳統而具有了某種哲學意義,這也是以前的仙傳小說所不具有的。
三
綜上所述,《賈奉雉》沿用了仙傳情節模式,但又與傳統仙傳小說的明顯不同,這可以概括為民間世俗趣味與文人思致的不同。文人思致使《聊齋志異》整體上成為對民間世俗模式的提升形態,《賈奉雉》也不例外。
從西晉葛洪《神仙傳》開始,中國神仙小說就與民間信仰有著直接聯系,葛洪本人就是道家煉丹術的鼓吹者;到唐代,道教系統中的神仙譜系更加成熟,人們對仙界的想象趨于人間化。如《采藥民》中主人公所到的仙境儼然就是人間的村落和城鎮。數十人家的村落中,有“桑柘花物草木”,有“耕夫釣童”,只不過“其民或乘云氣,或駕龍鶴”,“其地草木,常如三月中,無榮落寒暑之變”。進入城市,城門口赤色大牛“閉目吐涎沫”,不時地吐出各色寶珠,食之可以長壽。然后被指引見到這個神仙國度的玉皇。玉皇殿上,有北斗七星侍衛左右,又有“玉女數百,侍衛殿庭”,玉帝給這位人間的到訪者賜以玉盤鮮果,以兩手所捧得鮮果的數目賜予玉女,結果得到三位玉女和一處住所。采藥民念及妻子剛生女兒,家貧無以供養,執意回到人間。這樣的唐人傳奇集結了仙丹、玉女、道術等神仙小說慣有的元素,屬于類型化的民間故事;傳奇作家只是民間故事的被動記錄者,毫無個人性情與身世體驗灌注其間,亦毫無主體性可言。在唐代詩歌創作中,能夠將游仙傳統與個人性情及人生失意感完美結合的是“詩仙”李白,他的《夢游天姥吟留別》、《廬山謠送盧侍御虛舟》等詩作,在失意和憤懣等情感體驗基點上寫名山引發的游仙遐想。《賈奉雉》也將傳統與個人做了完美結合。作家在“仙傳”情節中引入闈場、制藝等與落魄讀書人命運攸關的元素,以代替神仙小說的慣有元素,使小說成為中國仙傳文學傳統由民間世俗化想象轉向文人思致、由感性快樂轉向理性哲思的標志。
英國詩人在艾略特《傳統與個人才能》一文中指出,文學傳統是由一系列現存作品聯合起來形成的一個完美體系,“在新的作品來臨之前,現有的體系是完整的。但當新鮮事物介入后,體系若還要存在下去,那么整個現有體系必須有所修改……于是每件藝術品和整個體系之間的關系、比例、價值便得到了新的調整。”[6](P3)蒲松齡《賈奉雉》對中國仙傳文學傳統的調整主要在于由世外烏托邦的建構轉向對讀書人現實生態的關注。主人公不是好道之士,而是才華出眾卻無緣功名的讀書人,神仙郎生也作為機巧的讀書人而現身人世的;賈高中后“與世長絕”、遁入洞府,親歷人間富貴后升仙而去,只因勘破人世間榮華之場的本質。小說套用“仙傳”情節,而推動情節進展的是人世間的現實窘境。以前那種“好道采藥遇仙”故事展示的僅是幻想的非現實的情景,情感舒緩而飄渺,所有小說元素都是類型化的:情節是預先設定的,人物是仙境的被動見證者。見不到任何出自強烈個性沖動的動作,作為杰出小說基本要素的個性自然就無從顯示。而在《賈奉雉》中,仙界被沖淡為冷峻的洞府,現實情懷借助主人公特殊的人生窘境被不斷強化。作家在結撰中充分灌注了個人的情懷和人生經歷,將柔情和悲憤、希望與幻滅相融合,整個情節的進展都是在情感張力的推動下完成的,人世的荒誕體驗最終被恰當地盛裝在遇仙模式中。蒲松齡以文人特有的精致化情懷,為中國仙傳文學傳統奉獻了一篇具有主體性和個性的佳作,如明珠一顆鑲嵌在仙傳傳統的終點處。
參考文獻:
[1]孫昌武. 作為文學創作的“仙傳”——從《列仙傳》到《神仙傳》[J].濟南大學學報,2005,(1)23-30.
[2]聶石樵.聶石樵自選集[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
[3](日)小南一郎.中國的神話傳說與古小說[M].孫昌武譯.北京:中華書局,2006.
[4]盛偉.蒲松齡年譜[M].蒲松齡全集 第三冊.上海:學林出版社,1998.
[5]蒲松齡.聊齋文集[M].蒲松林全集 第二冊.上海:學林出版社,1998.
[6](英)T.S.艾略特.艾略特文學論文集[M].李賦寧譯.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0.
注釋:
[①] 干寶《搜神記》卷一:“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而去。”
[②]“新神仙思想”是日本學者小南一郎用以標示西晉葛洪《神仙傳》思想傾向的術語。他認為在魏晉時期,一種與《史記·封禪書》和《漢書·郊祀志》所記載的神仙術在性質和形態上不同的神仙思想已經形成并廣為流行。帝王神仙術下移到民眾生活與想象中,《神仙傳》中的眾多故事即由此形成。(參閱小南一郎《中國的神話傳說與古小說》,孫昌武譯,中華書局,2006年,第183-184頁)
[③] 這個故事有兩個文本:一是《太平廣記》卷六一注明出自《神仙記》的“天臺二女”,二是劉義慶《幽明錄》第十四則。后者詳盡而有文采,出自劉義慶對前者的有意改寫。
(作者單位:陜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