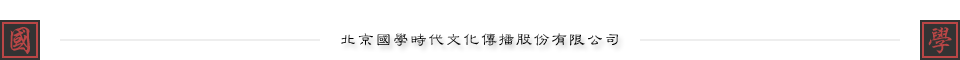究竟什么是紅學——有關紅學概念、本旨、方向、方法的檢討
紅學之繁榮昌盛,貌似已超乎各顯學之上,蓋四野之內,達官顯貴,雅士文人,乃至懵懂村童、走卒健夫,莫不以談紅為趣。然而紅學思想卻越來越混沌,目今對于《紅樓夢》的理解益發莫衷一是,百家百言,見仁見智,人人解的都對,人人解的又都不對,學界甚至失卻了研究目標和研究方向。這不應該是紅學本應有的狀況。紅學思想混沌的一個根源在于人們對于“紅學”這一概念、本旨以及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的理解是非常混沌的。
舉凡討論事物,須首先以“名辯”思想對相應的概念準確界定,正名實,方能別同異、定是非、分白黑、理清濁,若名實不符,概念不清,本旨不明,就會引起思想混亂,甚至導致學術根本方向的錯誤。紅學比之傳統學科涵義特殊,又且隨著時間的磨礪和《紅樓夢》研究的廣泛開展,人們對于“紅學”這一概念的認識反而越來越模糊,因而尤須行“名辯”以澄清本旨,明晰內涵,厘正方向,恢復紅學之本原面貌,回到其本來意義上去。
歷史上,紅學這個概念生成后,很長時間里沒有人認真進行厘定,人們多以為紅學始自清代文人戲謔之辭,蓋未知有《紅樓夢》現,必有紅學發生之客觀必然性,亦未細思紅學與其他文藝作品研究之本質區別。1944年,楊夷發表《紅學重提》提出了“什么是‘紅學’”的問題,他的回答是“關于《紅樓夢》背景的研究,歷來稱之‘紅學’”。后有周汝昌老師將紅學范疇進一步界定為曹學、版本學、脂學、探佚學。時下的主流紅學基本上是在周老師界定的紅學范疇內勤奮工作著。由于主流紅學歷百余年也沒有找到正確的解讀道路,沒能拿出足夠的證據,令人信服地完整解釋《紅樓夢》,故有學者主張紅學應“回歸”文學性研究。
我們考察,紅學萌于清代,成于民初。根據《紅樓夢》早期附批注釋以及周春、戚蓼生等人著述和《清稗類鈔》等資料分析,清朝的《紅樓夢》研究者曾把紅學類同于“治經”,尋找紅樓命意,聽弦外之音,大抵歸為索隱,例如周春的《閱〈紅樓夢〉隨筆》認為《紅樓夢》隱事是“張侯世家”,賈瑞影射洪承疇等等;盡管彼時的大多數索隱因懼文網之禍而往往僅以小道消息形式傳播,但卻是民初索隱紅學繁榮發展的基礎;文學評點不是主要的研究方法和模式。因此,我們反思,紅學肇始,非為其他,終究是因為《紅樓夢》“真事隱去”之故。
“真事隱去”是曹雪芹于《紅樓夢》開篇即明確布告的。可以說沒有“真事隱去”就不會有如此頭緒萬千穿插復雜的《紅樓夢》,沒有“真事隱去”也不會有后來經久不衰的紅學。“真事隱去”是開展《紅樓夢》研討的基礎和出發點,素來作為紅學研究的基本信仰——如同數學之信仰十進位制。只有找到“真事”方有可能真正做到“解其中味”——此為紅學之初衷。
而事實上,作為主流紅學,在先的索隱派和后來的考證派,也的確都是為追索《紅樓夢》“真事”以解其中“真味”而來——所謂的索隱派與考證派,在工作性質上并無差別,都是對“真事”進行索隱以試圖找到《紅樓夢》立意所在。縱然胡適千方百計回避“索隱”二字,把自己打扮成一個科學家,標榜自己“科學考證”,罵索隱是“猜苯謎”、蔡元培是“笨伯”,但他搞出來的“大膽假設”也仍然是承認《紅樓夢》“隱有真事”,他的“小心求證”本質上就是“索隱”,只不過是把“明珠世家”“張侯世家”“皇帝世家”搞成“曹先生世家”,把蔡元培他們搞的“國史索隱”“野史索隱”變成了“自敘傳說”——請注意他的“自敘傳說”是實錄意義上的,不是文學意義上的,胡適的所謂“曹賈互證”,其本質上就是“曹雪芹家史索隱”——這一切亦無非是變換個學術概念而已,工作的性質并無任何改變。
——一個基本邏輯是:《紅樓夢》索隱和考證是一個對立統一,索隱是主要方面,先有索隱后才有考證,索隱是考證的前提,考證是對索隱內容的考證,是為索隱服務的,沒有索隱何來考證?考證什么?胡適或有意或無意回避了這個辯證矛盾。
從古至今,積百余年,主流紅學家們皓首窮經,搜求《紅樓夢》相關資料,展開或國史索隱或野史索隱或家史索隱,且不論其用以解釋《紅樓夢》有無道理,其終極目標皆在于理解作者真實立意,基本目標是還原《紅樓夢》本事,基本手段是在《紅樓夢》文本中,按作者提示追蹤躡跡,大膽假設歷史人物事件與《紅樓夢》表面人物故事的對應關系,附會并考而證之。至于索隱派考證派,無非是在追索目標和工作方法的選擇上各有側重而已——索隱派注重于索解微言大義,史家眼光更足;考證派側重作者身世背景,文人氣質更多些。
剖去現象觀其本質,肇始意義的“紅學”事實上是一個經過了語言簡化的概念名稱,這一名稱的母體應該表述為“《紅樓夢》索解學”,其主要工作是從索隱開始的,本質上也就是“《紅樓夢》索隱學”,本義在于指稱“許多人追索本事解釋《紅樓夢》”這一特殊學術現象,本質意義在于標明“索解《紅樓夢》”這一相別于其他學術研究的特殊內容特殊目的特殊手段。“索解”的實質含義是“索隱并考證以還原本事以便正確解釋作者真實立意”。所以,還原后的紅學概念不是泛泛的所有的“研討《紅樓夢》的學問(馮其庸)”,它至少并不包括《紅樓夢》文學性研究。現在的紅學范疇,是“《紅樓夢》索解學”經過語言簡化后又經過概念泛化形成的。根據紅學表象所理解的“泛紅學”,與肇始意義上的“紅學”概念是有距離的。
對《紅樓夢》的文學性研究事實上更應屬于文學范疇。《紅樓夢》文學性研究具有一般性而不具有特殊性,其與《西游記》文學、《水滸傳》文學乃至任何一部小說的文學性研究目的方式手段沒有實質差異,不具備只特殊適用于《紅樓夢》的研究目標、研究手段、研究性質。在紅學領域,“《紅樓夢》索解學”一直占主導地位,文學性研究處于從屬地位,唯物辯證法認為,事物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事物性質,因此,主張“回歸”文學性研究,認為“文學性研究才是正宗紅學(王蒙)”,就是把處于從屬地位的非主要矛盾人為提升為主要矛盾,違背事物矛盾規律,否定重點論搞形而上學,主次不分,本質與現象不分。
文學性研究與紅學肇始無關,與紅學原初的概念無關,與追索《紅樓夢》本事及作者本旨立意無關,“回歸”文學性研究,是搭便車的要當司機,喧賓奪主——周汝昌老師就曾對此進行過嚴厲批評,甚至一度主張要把文學性研究開除出紅學。“把文學性研究開除出紅學”,這當然有些偏激,不過也反映出當前紅學研究中的學術方向跑偏和學術方法濫用的問題。我并不反對把文學性研究(包括與西方的比較文學研究)納入紅學范疇,但是我主張在索解學的前提下開展文學性研究,因為文學性研究也對全面理解《紅樓夢》有幫助,但不對《紅樓夢》真實立意進行索解,不解決紅學的根本矛盾,純文學性研究可能毫無意義,即便把《紅樓夢》倒背如流,看的仍必是海市蜃樓云山霧罩不知所之。況且,曹雪芹在“賈瑞正照風月鑒”故事中已經明確告知讀者,“只照他的背面”,“照正面”是“死路一條”,那么若只注視正面“公子紅妝”的文采風流,不理解背面“白骨如山”的“信史”及其立意,是難免被曹雪芹罵作“賈瑞一路”的,也一定不能在學問與學術上修成正果。
楊夷紅學概念中的“背景”二字,可以推定其所認識的紅學乃是“紅外學”,與紅學本旨尚有距離。那么周汝昌老師的紅學范疇是否準確指稱紅學現象,準確反映了紅學的本質意義呢?周老師將紅學范疇界定為曹學、版本學、脂學、探佚學——即所謂“新紅學”四大支柱,其紅學理論是以信仰胡適“自敘傳說”為基礎的。胡適的“自敘傳說”本質是“曹雪芹家史索隱”,而“家史索隱”在索解方向上是根本錯誤的——這已經被胡適自己所開創的考證派的無比深入無比廣泛的考據所證實。基礎既已推翻,那么“新紅學”四大支柱也就站不住腳了。曹學、版本學、脂學、探佚學于《紅樓夢》背景研究確有助益,但于索解本事及理解作者立意則太狹窄并偏離方向了,目前于此范疇和方向所作的研究對紅學前途的支撐能力已經十分有限。
“自敘傳說”被證偽后,有學者發明“后自敘傳說”,提出“《紅樓夢》是以曹氏家世為素材創作的小說”,企圖模糊《紅樓夢》索解研究與文學性研究的界限,為已經傾頹的“新紅學”繼續尋找支撐,但實質上其出發前即已否定“曹賈互證”,并否定了“真事隱去”這一紅學基本前提,其立足點比之胡適的“自敘傳說”更不牢靠。“后自敘傳說”顯示出學界對于學術方向、方法已經毫無把握,關于“讀懂”二字已經實在無可奈何。
“自敘傳說”和“后自敘傳說”的偽科學性及其文學氣質干擾了紅學界的史學與哲學視野。缺乏史學和哲學視野是“新紅學”花了近百年時間沒能讀懂《紅樓夢》的根本原因。
如果紅學界仍然堅持在“新紅學”的狹窄范疇和錯誤方向上繼續工作下去,雖則表面“蓊蔚洇潤”,內囊里實心虛氣短,只會在“深有萬丈遙亙千里”的“迷津”中滑向《紅樓夢》“黑溪”的深淵,正如俞平伯前輩反省的那樣,“紅學愈昌,紅樓愈隱”。把主要研究萎縮在作者的身份身世上,或僅關心《紅樓夢》正面故事,研究人物形象人物關系,遺棄“真事隱去”這一基本信仰,避談《風月寶鑒》之背面立意,這是非常危險的,做出來的學術成果,可能根本是反紅學的,離《紅樓夢》作者的思想核心、立意本旨越去越遠,離紅學的初衷越去越遠。忘記了目標的學術,找不到方向的學術,搞不清概念的學術,以及放不開心胸思想的學術,必成無源之死水,學將不學了。
綜上,對于紅學概念的反思和對于紅學方向的反省,使我們不得不回到紅學的肇源上,即《紅樓夢》“假語村言”“真事隱去”。因此,“回歸索隱”才是今后紅學主要的工作方向。無論紅學的大樹長到多高生出多少枝枝杈杈,根子依然在于索隱,惟正確索隱方能解讀文本,惟正確索隱方有正確考證之可能,惟正確索隱方有可能理解作者的真實立意。
當然,蔡元培等紅學前輩把寶黛釵當成《紅樓夢》主角,或附會順治康熙朝人物故事,或糾纏于野史小說的改編,其索隱方法和方向也是有問題的。事實上,寶黛釵只是作者幻形入書,既非可以索隱的歷史人物,也非曹雪芹著意刻畫的《紅樓夢》主角。
《紅樓夢》譬若一個大戲臺,生旦凈末丑,嬉笑怒罵,出將入相,躍馬揚鞭,上演很多劇目,例如“葫蘆僧判斷葫蘆案”,“起嫌疑頑童鬧學堂”,“秦可卿死封龍禁尉”,“魘魔法姊弟逢五鬼”,“柳相蓮暴打呆霸王”,等等等等,演的都是歷史“真事”。不過比舞臺戲劇更進一步的是,《紅樓夢》因特殊的外部環境和作者莫大苦衷,不能明傳其人,不能直抒胸意,無奈中乃以“家庭閨閣瑣事”化裝演示歷史事件,并化妝出紅紅綠綠的各色人物,將真正的主角與歷史事件藏于其間,將“理治之書”化作“適趣閑文”,以悅人耳目并掩人耳目——即作者所謂“真事隱去”“假語村言”“私掖偷攜強撮成”者,乃《紅樓夢》基本藝術手法。
同時,因《紅樓夢》是一部“紀傳體史書”,其演出的“歷史劇目”有很強的相對獨立性——這一點在《紅樓夢》表面故事的獨立性上就可以明顯觀察到,例如“葫蘆僧判斷葫蘆案”“賈瑞正照風月鑒”、“秦可卿死封龍禁尉”“柳相蓮暴打呆霸王”等等故事,去掉了根本不影響《紅樓夢》故事情節發展,有些回目存在著反而使整個小說顯得雜亂無章——為了將各獨立劇目連綴在一起,撮成一套戲,作者安排了一些角色來串場,例如賈雨村,賈雨村等人主演的頭兩回,作用在于作為“副末”開場,介紹劇目和劇本來龍去脈,明宗亮旨;再就是寶黛釵——寶黛釵僅是《紅樓夢》的“樂隊”,配角而已,寶玉敲鼓(敲邊鼓),黛玉操琴(調弦定調,抒發情緒),寶釵只是打板的(和和拍節)。那些“黛玉進府”之類的所謂“重頭戲”既非“真事”,也不是《紅樓夢》欲傳的什么重要篇幅,乃是用以串聯情節及欲蓋彌彰處,即作者所謂“堂前<當前>黼黻煥煙霞”者。寶黛釵的主要作用就在于:一是串聯故事情節,二是作為樂隊吸引耳目,三是借以表達思想感情,四是作為障眼法以避文網之禍。
解讀過程中,一則需要觀者領會紅樓表面“假話”與“真語”之間的對應關系。例如寧國府諧音明國府——指明王朝,榮國府諧音戎國府——指滿清政權;再比如焦大罵人,看似罵寧府通奸養漢,實是罵奸臣誤國;王熙鳳過寧府打骨牌,就是白骨累累的一場侵略掠奪戰爭。二則要辨清主角、配角與樂隊。如果混淆了樂隊和戲臺上的真正的主要角色,對戲臺角色也分不出生旦凈末丑,搞不清戲臺上的角色所扮演的歷史真人,搞不清演出的“家庭閨閣瑣事”與歷史真事之間的關系,那么就會越看越糊涂,最后只能看些樂隊的幾個淑女佳人吹拉彈唱打情罵俏裝瘋賣傻,剩得“白骨如山忘姓氏,無非公子與紅妝”。
事實上,曹雪芹開篇即已經聲明,《紅樓夢》所傳并非子建文君紅娘小玉,在寶玉“續莊子文”處亦已點明“彼釵、玉、花、麝者,皆張其羅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纏陷天下者也”,紅男綠女無非鏡中之幻緣,乃作者“真事隱去”之障眼法耳;同樣的,在《紅樓夢》表面故事中寶黛釵的“戲份”并不多,甚至很多篇章那些所謂的“主角”們根本沒出現,朦朧的“愛情”也只存在于一些讀者和學問家的想象中——所謂的“愛情主線”本屬無稽之談,于“正面”看家族衰落、世事人情亦是誤解紅樓者,而那些執著于“遺簪”“扒灰”“養小叔子”等等淫艷故事之發掘探佚,尤入賈瑞一途,壞人子弟,罪莫大焉。
《紅樓夢》本立意于傳國家信史(明清斗爭史事)與民族文化(即中華之“道”),須進行國史索隱和哲學思想索隱——其間必須通過“意淫”,領悟作者之“假語村言”,剝清必須進行索隱的人物角色與用以串場的配角、伴奏的樂隊,剝清必須進行索隱的故事與用以串聯故事的情節,按照作者提示在史實中“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方能夠索到其隱去之“真事”,明了作者滿腹經綸而甘貧守潔之真情,體會作者寒屋數載血淚著書之“真味”。至于具體如何進行《紅樓夢》索解并能夠索解到什么,我們須另行專文細致討論才好。
參考資料
陳維昭《紅學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王蒙《活說紅樓夢》,作家出版社,2005
馮其庸李廣柏《紅樓夢概論》,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
《蔡元培王國維魯迅點評紅樓夢》,團結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