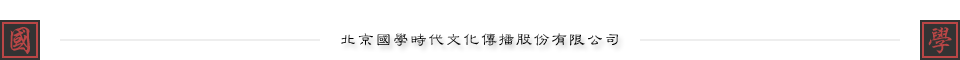《孽海花》中傅彩云對傳統風塵女子的顛覆
曾樸是一個熱衷革命思潮的作家,他將《孽海花》寫成一部歷史小說,全面刻劃中國從1870年直至民國前夕所經歷的政治動蕩。他不愿意采納傳統的敘事形式,更在刻劃賽金花——故事中的傅彩云,表現其對這風塵女子形象的刻劃上,故意對其傳統作出顛覆和背叛。《孽海花》被魯迅列為譴責小說,因其主要的著眼之處是為折射和批判危機深重的社會現實。但因著傅彩云的角色,無庸置疑《孽海花》是包含了“狎邪”的成分。[1]本文會嘗試闡析其中風塵女子形象,對傳統的轉變和顛覆,針對在角色的塑造上。
首先就是孽海花中傅彩云的角色對男主角金雯青的背叛,先后認識瓦德西和名伶孫三等。而傳統上,由唐傳奇《虬髯客傳》的紅拂女,至清初《桃花扇》李香君等妓女,是男主角傾情至相戀。如《虬髯客傳》中紅拂女對李靖的一見傾心,私自投奔:“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未有如公者。絲蘿非獨生,愿托喬木,故來奔耳。”《桃花扇》中弘光皇帝即位后,起用阮大鋮,阮趁機陷害侯方域,迫使其投奔史可法,并強將李香君許配他人。李香君決不從,撞頭欲自盡未遂,血濺詩扇。而《李娃傳》較特別,李娃雖曾參與拋棄滎陽書生的騙局,但之后亦是輔其科舉。而傅彩云對男主角的關系是建基于買賣的,為妾侍,她本身根本不可作出選擇。而可成為狀元的妾侍,也是階層的跳躍,可以脫離青樓的生活。她本是年輕,十五之年歲,自有浪漫好奇的追求,如瓦德西將軍的權力和魅力令她迷倒。主角互相的關系根本不是愛情而是買賣的關系,是傳統納妾制度[2]對女性之不平等。所以傅彩云的背叛是情有可原,更與傳統女主角傾情至相戀不同。
此外,一般妓女的社會地位甚低,但其因脫離傳統婦女的禮教,真性情也表現了個人主義。而孽海花故事里西方的語境,也是確立了個人主義的先例。歷代故事中妓女都不會得到真正的認同,但孽海花因時代處于中西沖突的局面,傅彩云代表的個人主義于西方卻得到鼓勵。她聰明地學習德語和社交禮儀,很快的進入柏林上層的社會。她甚致結織俄國革命者夏雅麗,更結下友情。維亞太太更笑道:“不瞞密細斯說,我平生有個癖見,以為天地間最可寶貴的是兩種人物,都是有龍跳虎踞的精神、顛干倒坤的手段,你道是甚么呢?就是權詐的英雄與放誕的美人。……如今密細斯又美麗,又風流,真當得起‘放誕美人’四字。”(第十二回)有論者指出,這種評價不僅使彩云作為吸引中心欲望眼光的“身體”特質暴露無疑,而更重要的是,它清晰地指示了這放誕的東方“美人”之身所具有的無窮顛覆力[3]。這種顛覆是要在西方的社會語境,才能展示傅彩云放誕美人的形象,推倒傳統上放蕩無禮的評價。反觀傳統婦女,已受禮教所礙,金雯青夫人曾經說過:“聞得外國風俗,公使夫人,一樣要見客赴會,握手接吻。妾身系出名門,萬萬弄不慣這種腔調……”(第八回)傅彩云好動聰明,不拘泥的個人解放特質,在本土則視為有失體統的事。
最后,傳統上看好新情欲的女子視為傾覆國家的紅顏禍水,可是傅彩云的角色卻顛覆了道德和政治的關系。有論著指出,愛欲與政治,女性氣質,與男性主導的國民性之間的辯證關系,必需重新描劃,以回應時代的大變化[4]。傅彩云好于情欲的交往和浪漫的追求,但她對國家的命運不是盲目地一無所知,反之她運用她的身體,在臥寢上勸服瓦德西元帥,使中國免于更加難堪的羞辱,這是她牽于國家衰亡的覺醒,和她能力之內的做法。對于中國新女性的塑造,其文本的角色亦扮演關鍵的作用。
在五四的話語下,譴責小說含有狎邪成分的不復多見,只可在鴛鴦蝴蝶派找到一些繼承,如畢倚虹的《北里嬰兒》和《人間地獄》。《人間地獄》中心內容是柯蓮蓀與清倌人秋波之戀。清倌人即妓中之處女,當然是一種精神之戀。有論文指出,“在何海鳴和畢倚虹的筆下,高等妓院還是一種社交場所。到男女社交公開后,再加上抗戰后的經濟的崩潰,這種交際場所的‘堂子’很快淪落為‘性交易所’;因此,從那種寫‘清游’、‘精神之戀’到寫‘私娼’、‘暗娼’的題材也勢所必然。歷史認為,狹邪、倡門這一曾經是題材大戶至此應該畫上一個大大的休止符!”[5]而鴛鴦蝴蝶派對傳統風塵女子的顛覆卻不復見了。
注釋:
[1]王德威著,宋偉杰譯:〈晚清小說新論——被壓抑的現代性〉(臺北:麥田出版,2003),頁151。
[2]王祖獻:〈孽海花論稿〉(安徽:黃山書社,1990),頁134。
[3]吳曣:《孽海花》與晚清語境中的民族主體建構(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二十二期,2004)
[4]王德威著,宋偉杰譯:〈晚清小說新論-被壓抑的現代性〉(臺北:麥田出版2003),頁149。
[5]〈現代言情小說的先驅者們〉(蘇州:蘇州大學現代中外文化關系研究所www.zwwhgx.com)
(作者單位:香港樹仁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