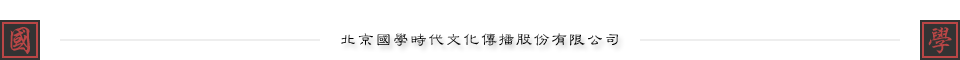國學網二十四史版權案代理詞
北京高警兵律師事務所受上訴人委托,本律師受律師事務所指派,作為中華書局訴北京國學時代傳播公司侵犯“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著作權案的上訴人(一審被告)的代理人,現針對一審判決發表如下代理意見如下:
一、一審判決中認為中華書局公司以分段、加注標點和文字修訂的方式完成的“二十五史”點校作品具有獨創性,這個認定是錯誤的。
(一)古籍“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各典籍是完整的、內容上沒有殘損不全。
一審判決認為:“由于傳承至今的殘損問題、各個底本彼此不一致等原因,……古籍作品的真實原意已經無從知曉”(判決書第32頁第15行至18行),其實事實并非如此。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中國古籍的重要代表,有正史之稱,地位高于其他史籍。自乾隆四十七年《四庫全書》完成后,“二十四史”從順序到內容都已確定,內容保存非常完整,可以說是一卷不缺,一字不損!
在眾多版本的《二十四史》中,其中的武英殿本和百衲本也是中華書局用來作為參考的底本。
武英殿本,即清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欽定二十四史》,是中國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規模匯刻。毛澤東生前仔細閱讀,并做過評點的就是這個版本。毛澤東對此手不釋倦,反復閱讀,與之朝夕相伴24年。
百衲本,是國學大師張元濟先生主持整理,由商務印書館影印完成的。百衲本二十四史精選歷代善本配補、匯合而成,使讀者得以一覽諸家善本的風采,有很高的文獻價值。足以反映二十世紀前期各史通行最善本的面貌。
《編輯學刊》1993年第2期張人鳳的文章《張元濟和百衲本二十四史》中載明“標點本二十四史大部分采用百衲本作底本”,足以證實中華書局是以百衲本為底本的。
中華書局無需對所謂的彌補“殘損”做任何創作性工作中華書局根本不需要進行完善和修補古籍字句的工作。這是一個古籍常識性問題,一審法院認為涉案古籍是殘損不全的,并且認為“中華書局對于完善和修補古籍字句起到了重要作用”,這是對事實認定錯誤。況且,中華書局對古籍殘損和其對于完善和修改古籍所起的作用也未進行舉證,法院的這一認定沒有證據支持。
(二)古籍點校作品表達空間是非常有限的,不同的人對古文進行分段和標點不會有較大差異。
一審判決中關于古籍點校的表達空間問題,認為古文點校作品的表達空間是有較大差異的,這種認識是不正確的。
眾所周知,古籍整理目標是求是求真,恢復古籍內容的原貌。古籍整理者絕對不能“視古籍為己出”,妄自修改古籍內容,或隨意增補字句,甚至將自己的創作風格、技巧融入古籍,改變古籍的內容及表達方式。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古籍文字是前人原創留下來的,為了方便現代人閱讀,通過分段、加注標點和字句修正等方式對古籍進行點校,根據中國語言文字的使用習慣和規則,經點校的各個版本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都是極其近似的,存在著趨同性,點校作品之間根本不會有較大差異。
(三)中華書局對古籍“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進行的分段、加注標點和字句修正工作是依附于古籍本身,而且與古今本身是無法分割和獨立存在的。
一審判決書中認為:“點校者實際上是在用分段、加注標點和字句修正的方式對于其所理解的古籍作品的原意進行表達。這種表達在客觀上可能與古籍作品的原意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但無論客觀上是否一致,亦無論點校者的目的是否要與古籍作品原意一致,其均是在對自己所理解的古籍含義進行表達。雖然這種表達的方式較為特別,但是方式的特殊性并不影響這是一種表達的定性。”(一審判決書第32頁第19行至25行),這種認定是錯誤的。
按照著作權法理論中的“混同原則”,對于“思想”的表達如果只有一種或及其有限的表達。這種情況下,原本不受保護的“思想”和原本受保護的“表達”混在一起,無法在兩者之間劃出明確的界限。如果對語言描述作為“表達”加以著作權保護,會導致“表達”所依附的“思想”本身也被壟斷,這顯然是一種不合理的壟斷。
不同的人對于古籍“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原文加注標點的結果總是大同小異的,也就是說,對古籍“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加注標點這種表達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古籍“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本身是已經進入公共領域的作品,古籍本身和加注過標點的文字,不形成獨立的表達,它是依附于古籍本身而存在的,如果對加注了標點這種“標點”給予著作權保護,勢必會形成一種不合理的壟斷。
(四)中華書局對古籍“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分段、加注標點和字句修正”的工作不具有法律意義上的獨創性,不應受著作權法保護。
1、從立法本意上看,對古籍“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進行“分段、加注標點和字句修正”所形成的中華書局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不應受著作權法保護。
1991年《著作權法實施條例》對“整理”的解釋“第五條第(十二)整理,指對內容零散、層次不清的已有文字作品或者材料進行條理化、系統化的加工,如古籍的校點、補遺等。”但要注意的是,在2001年重新頒布的《著作權法實施條例》中該條被完整地刪除,現在再主張古籍斷句屬于“整理”、能夠產生新作品顯然是不正確的。
演繹作品是指通過改編、翻譯、注釋、整理已有作品而產生的新作品。著作權中的所謂“整理”的真實含義是指因選擇或者編排已有作品并體現出獨創性。只有整理行為構成再創作時,才產生演繹作品。
雖然中華書局公司花費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當然這也是在特定歷史環境下,真正的投入主體是國家,而非現在的中華書局公司),產生了中華書局版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但這種勞動成果并不具有一定程度的“智力創造性”,不能體現作者獨特的智力判斷和選擇,也不能展示作者的個性并達到一定的創作高度要求。這種勞動只是一種“額頭流汗”,如果對這種“額頭流汗”予以著作權保護,會不可避免地阻礙他人利用前人的勞動成果進行創作,這是與著作權法鼓勵后人“站在前人肩膀上”創作新作品的基本宗旨相違背的。而且,《伯爾尼公約》也是將作者的智力活動創作成果作為受保護的作品,而非僅僅是“額頭流汗”的勞動成果。
2、中華書局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只是發現和揭示事實,不是對自己思想內容的表達,沒有獨創性。
古人寫書的時候也有語氣的停頓,只不過根據當時的習慣,不把標點標出來而已,現在的研究者通過自己的研究發現了古人要停頓的地方,很準確地找到古人原本要停頓的地方,并且把正確的標點標出來,也就是說,斷句是在遵循古籍原意的前提下,為了方便現代人閱讀,在古籍中本應停頓的地方用現代漢語的標點加以標識。這種工作只是在在發現和揭示事實,把古人本來就要斷句的東西真實的還原出來而已,并未改變原作品的表達,也未產生新的表達含義。這個行為不叫創作,不可能形成新的作品,這不是版權保護的對象,因此,中華書局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不能產生以獨創性為前提的“作品”。
(四)應嚴格區分正文和校勘記兩部分內容來確定著作權問題
中華書局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正文部分,因為不具有獨創性,不享有著作權。但是,客觀地說,古籍整理中出現的校勘記、注釋、出版說明和校后說明,這些文字是經過獨立創作反映作者思想的內容,只有這部分才稱得上是演繹作品,才享有著作權。也就是說,中華書局對中華書局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雖然擁有著作權,但其對于其中的古籍“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正文部分,作為原有作品本身,是不享有著作權的,也不能限制他人使用。
二、一審判決中,對于“國學時代本“二十五史”與中華書局本“二十五史”構成實質性近似”的認定是錯誤的。
(一)一審法院采用普通的比對判斷近似性是錯誤的。
由于該案客體的特殊性,對于認定是否實質性近似時,不應簡單采取通常意義上的比對方法和比對標準。
對古籍“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工作,具有極大的特殊性、復雜性和專業性。點校工作包含對古文進行斷句、加標點、修正錯誤等內容,對文章的主體內容不能私自增改,稍有改變必須說明原因和注明出處;而加標點和斷句又必須遵循一般語言表達的規律,所以點校的結果總體應基本一致,只在細微處存在區別,否則會產生理解歧義。
對于一般意義上的文字作品而言,只要權利人作品與被控侵權作品所表達的內容基本一致或者達到一定比例,尤其在含有明顯的你錯我也錯的抄襲點的情況下,就可以認定侵權成立。然而,古文點校工作所具有的特殊性、復雜性和專業性特點,在對各個點校本版本進行比對時,不能簡單照搬通常意義上的比對方法和比對標準。一審法院對于作品的比對采用的是一般意義上的文字作品的對比方法,但對于古文點校作品,這種比對方法顯然是不妥的。
(二)即便兩者的勞動成果具有相似性,也不能就此認定上訴人是對被上訴人作品的復制。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著作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5條:“由不同作者就同一題材創作的作品,作品的表達系獨立完成并且有創作性的,應當認定作者各自享有獨立的著作權”。也就是說,著作權法意義上的“獨創”并非是指“首創”或獨一無二,“獨創性”中的“獨”是指勞動成果源自于勞動者本人,由勞動者獨立完成,而非抄襲的結果。只要是獨立完成的結果,勞動成果即使碰巧與他人的勞動成果一模一樣,也仍然符合“獨創性”。
上訴人擁有對古籍進行自動比對、自動標點和自動排版的三大核心技術,其對古籍“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進行的點校而產生的成果,是通過自己擁有的技術力量,在節約大量人力和物力成本下獨立完成的,而對古籍點校的結果又具有極大的趨同性,法院不能認為上訴人是對被上訴人作品的復制,更不能認定上訴人侵權。
三、一審判決中“國學時代公司主張涉案的國學時代本二十五史為其自行校勘完成的主張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該認定是錯誤的。
上訴人國學時代公司,一個以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為基本任務的公司,其創辦的“國學網”是一個關于國學的大型學術型公益網站。
上訴人擁有三大核心技術:自動比對、自動標點和自動排版。
1.自動比對系統能夠自動進行多種版本古籍的逐字比對,完成后即可在古籍中標示出文字和符號的任何差異。這套系統借助古籍智能輔助標點系統及古籍智能版本比對系統,使專家學者免除了許多繁瑣的重復勞動,提高了研究效率,無異于延長了學者的學術生命。
2.自動標點系統是自動為古籍加注標點的軟件系統。基于對大規模帶標點文本的分析統計,以句型為基礎,通過查找比對,對無標點的古籍文獻自動加上合適的標點符號,可用于大規模古籍整理等領域。該系統理想狀態下自動標點準確率在90%以上,在機器無法完全識別的情形下還會自動提示專家進行人工干預。
3.自動排版系統可以實現版式設計任意可選,多種格式自動排版,疑難僻字一次補齊,目錄索引自動生成。該系統較好地解決了古籍生僻字造字,簡繁體轉換、橫豎版式等多項技術難點,已申報國家專利。
利用這項智能排印技術,上訴人完成了《十三經》、《隨園食單》、四大奇書等書籍的排印,為文學院排印了一套1.5億字,共計150冊《中國古代文學史資料全編》的叢書,特別是參與了《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該技術把信息科學技術融入古籍文獻的整理、保存、傳播、研究與應用之中,使古籍整理與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將對古籍整理與編輯產生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上訴人國學時代文化傳播股份有限公司擁有以上三項核心技術的權利證書。
擁有這三項技術,上訴人可以在極少的時間和人員投入上是完全可以完成“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工作的。
四、本案認定事實部分中,與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認定的事實不符。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九條下列事實當事人無需舉證證明(一)眾所周知的事實;(二)自然規律及定理;(三)根據法律規定或者已知事實和日常生活經驗法則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實;(四)已為人民法院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確認的事實;(五)已為仲裁機構的生效裁決所確認的事實;(六)已為有效公證文書所證明的事實。”
在此案之前,與此案有關聯的一個案件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簡稱中華書局)訴漢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漢王公司)侵犯著作權糾紛一案,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曾對此案進行二審審理和判決,判決書為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1)一中民終字第6393號,該判決書中認定的事實為“本院經審理,對于各方當事人對原審法院經審理查明的事實無異議的部分,確認如下:……漢王公司提交了國學公司在點校過程中形成的五大紙箱稿件,稿件的用紙黃舊,隨意抽取可以看到多人多處修改評點筆跡。漢王公司表示,帶來的內容并非全部,國學公司處尚有四十箱,可隨時查閱,可以證實國學公司進行點校時所做的大量工作,并非抄襲中華本。”
在“本院認為”部分,對法理闡述明確如下:“本案中,中華本和國學本在內容上都屬于對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進行點校的版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均屬古籍,其所涉內容跨越中國整個封建文明史,各版本形成時間甚為久遠。上述特點決定了古文點校工作具有極大的特殊性、復雜性和專業性。點校工作包含對古文進行斷句、加標點、修正錯誤等內容,對文章的主體內容不能私自增改,稍有改變必須說明原因和注明出處;而加標點和斷句又必須遵循一般語言表達的規律,所以點校的結果總體應基本一致,只在細微處存在區別,否則會產生理解歧義。對于一般意義上的文字作品而言,只要權利人作品與被控侵權作品所表達的內容基本一致或者達到一定比例,尤其在含有明顯的你錯我也錯的抄襲點的情況下,就可以認定侵權成立。然而,古文點校工作所具有的特殊性、復雜性和專業性特點,使得法院在對各個點校本版本進行侵權比對時,不能簡單照搬通常意義上的比對方法和比對標準。中華書局采用的三種方法基本源于對一般意義上的文字作品的對比,但對于古文點校作品,漢王公司根據行業特點提出的多項反駁意見合乎情理。此外,古文點校本等對古籍進行整理的成果,是后人必須參照學習的對象,這是文化傳承與發展的必然趨勢。這種情況與一般意義上的文字作品可能被參照學習的情形甚為不同。因此,對于各版本的古文點校本彼此之間是否構成抄襲、剽竊乃至實質性近似,其判斷標準不能簡單照搬用于一般意義上的文字作品的比對方法和比對標準。在某一點校版本并非照搬照抄另一形成時間在前的點校版本的情況下,需要慎重把握侵權行為的認定標準,結合案情進行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這段文字至少認定了以下幾點:
1、點校的結果總體應基本一致,只在細微處存在區別,否則會產生理解歧義。
2、古文點校工作所具有的特殊性、復雜性和專業性特點,使得法院在對各個點校本版本進行侵權比對時,不能簡單照搬通常意義上的比對方法和比對標準。
3、古文點校的學習參考與一般意義上的文字作品被參照學習的情形甚為不同,對于各版本的古文點校本彼此之間是否構成抄襲、剽竊乃至實質性近似,其判斷標準不能簡單照搬用于一般意義上的文字作品的比對方法和比對標準。
而此次判決中,與以上三點事實和法理的認定是矛盾的,這種做法不符合法律規定。
五、此案對訴訟標的著作權的判定,應站在促進技術發展、弘揚民族文化的高度。
(一)對古籍“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點校工作,是國家行為,代表國家意志,勞動成果不應由某一家公司壟斷,而應造福于整個中華民族。
對古籍“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點校工作,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工程浩大的工作,前后歷時20個春秋。在這個過程中,始終體現了國家力量的投入,其表現為:一是國家領導人直接指示和關懷。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在《歸功毛主席,歸功周總理》一文中說:“解放后,我們黨十分重視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毛主席親自批示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周總理作了許多重要指示。1974年4月初周總理指示點校二十四史工作由我總其成。我聽到這指示,興奮、感激和慚愧的心情交織在一起。” (瞿林東主編:《20世紀二十四史研究綜論》,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頁)。二是國家成立專門小組確保出版機構的落實。1958年,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立,指定中華書局為該小組的辦事機構,承擔國家級古籍整理工作。三是國家調集史學精英確保專業人員的參加。當時,“以中華書局為依托,中國科學院的一些研究所和許多高等學校的學者們共同參與對二十四史的點校工作。”(瞿林東主編:《20世紀二十四史研究綜論·總序》)。如1963年,點校工作遇到困難,國家正式發文,從全國各地高等學校抽調人員參加史籍整理。即使在文革期間,周恩來總理排除阻力,調集斷代史研究的第一流專家,繼續開展史籍校點工作。標點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整理出版是史學界的大事,也是現代中國人的幸事,沒有老一代國家領導人的支持,沒有全國史學精英的奮勉,僅僅依靠一個法人單位的力量是根本完成不了這一偉大事業的。
正因為對古籍“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點校工作,是國家行為,代表國家意志,作品應造福于整個中華民族,而不應由某個單位,特別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進行了改制后的單位來大搞文化壟斷,坐享其成,坐收漁利。
(二)本案的判決,應本著促進技術發展的角度做出正確的判斷
古籍數字化,使數量龐大的古籍以新的載體形式出現,極大地提高了信息本身的價值,對古籍信息的儲存、分類、過濾、獲取和傳播起到重要作用,也為學術研究開辟了一條新途徑。
同時,古籍整理的數字化技術決不是簡單的文字復制,專業人員需要對文本進行數字結構標準化處理,這樣才能保證各種檢索系統隨著指令運轉。所以,對于那些嚴肅而富有專業精神、熱情而富有進取的數字化古籍整理的開拓者,應該給予應有的尊重和鼓勵。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 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中規定,要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其中有兩項工作要做:一個是加強文化典籍整理和出版工作;一個是推進文化典籍資源數字化工作。古籍數字化也是國家鼓勵和發展的方向,對于本案的判決應充分考慮到《決定》的精神。
(三)本案的判決,應本著著作權法的立法本意和站在弘揚民族文化的高度做出正確的判斷。
著作權從權利產生的歷史和對權利的觀念上看,都不是一種所謂的“自然法上的權利”,而是一種純粹的“法定權利”。著作權是近代法律強制規定的產物。著作權法的終極目標不是鼓勵一個人的勞動,而是促進文化創作傳播的發展。如果過分保護作者對作品形成了一種絕對性質的壟斷,作品就不可能成為他人進行新創作的材料來源,這將嚴重阻礙思想和信息的傳播以及文化的發展。
我們期盼,二審法院對于本案能夠重新審視和判斷,充分考慮到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特殊性,充分尊重市場經濟下,實現權利分配的合理性。我們也堅信,二審法院會站在促進新技術發展、弘揚民族文化、振興民族精神的高度,做出正確地判決,實現真正的公平和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