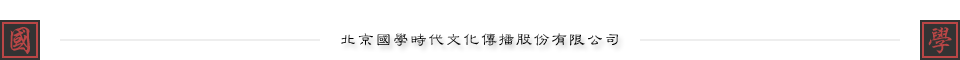令人失望的“選、注”——評(píng)《二十世紀(jì)詩(shī)詞注評(píng)》
《二十世紀(jì)詩(shī)詞注評(píng)》(錢(qián)理群、袁本良注評(píng);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6月,以下簡(jiǎn)稱(chēng)“注評(píng)”),我于去年才購(gòu)得,前不久,方展讀,稍加翻檢,覺(jué)得實(shí)在是令人失望。
編選者自稱(chēng)是“為時(shí)代、為大眾、為詩(shī)人、為詩(shī)”而選詩(shī)(見(jiàn)書(shū)末跋),這樣的標(biāo)準(zhǔn),實(shí)在是高,用于編選舊體詩(shī),可能更是困難重重,這就決定了編選者不僅要有才識(shí),而且要化深功夫。
然而,我的觀(guān)感卻是編選者作“學(xué)問(wèn)”作得實(shí)在是太“輕巧”。我對(duì)現(xiàn)當(dāng)代詩(shī)詞,本就不甚注意,所以也不知道目前存世的有多少種選本,我只發(fā)現(xiàn),“注評(píng)”的前半本書(shū),基本上就是在這本尚屬于“草創(chuàng)階段”的選本《二十世紀(jì)名家詩(shī)詞鈔》(毛谷風(fēng)編著;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93,以下簡(jiǎn)稱(chēng)“毛本”)中,再進(jìn)行擇選,除一些政治家、社會(huì)名流,如廖仲愷、徐特立、黃炎培、汪精衛(wèi)等,是“毛本”所未入選的;也只是零星幾位,其詩(shī)詞比較習(xí)見(jiàn)的大詩(shī)家,如梁?jiǎn)⒊Ⅳ斞浮⑻K曼殊等,被選詩(shī)作才是出乎“毛本”的,其余真可以說(shuō)是都已“牢籠”于此了。由此,“注評(píng)”不僅視界受到“毛本”的局限,還沿襲了不少“毛本”的失誤,如將秋瑾的生年誤作“1877-1907”(應(yīng)是“1875-1907”)、章士釗的生年誤作“1882-1977”(應(yīng)是“1882-1977”)……最妙的是,在第42頁(yè)保留著的一個(gè)“沿襲”的“殘痕”,即在黃賓虹的《題畫(huà)》中選了一首,卻在注釋中說(shuō)“原題十五首,錄二”,“錄二”的是“毛本”(見(jiàn)其第73頁(yè))。
“注評(píng)”的后半本,是否也“沿襲”了可作“捷徑”的其它選本,這是見(jiàn)識(shí)孤陋的我,不能辨析的。但我僅從所選的劉柏麗一首《漁家傲》,與其個(gè)人專(zhuān)集《柏麗詩(shī)詞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對(duì)觀(guān),就覺(jué)得頗有問(wèn)題,首先是題目,“注評(píng)”作“歡呼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衛(wèi)星上天”,專(zhuān)集無(wú)“歡呼”兩字;其次是下闋首句,“注評(píng)”作“昂宿驚疑呼獵戶(hù)”,“驚”字,專(zhuān)集作“猜”。
至于“注評(píng)”的注釋?zhuān)抑浑S意考察了零星幾家,即我手頭正好有他們的個(gè)人詩(shī)集的,黃節(jié)、丁寧,發(fā)現(xiàn)均是問(wèn)題不少。黃節(jié)的《十月十一日夜月中有懷曼殊》,因?yàn)閷?duì)黃節(jié)與蘇曼殊的經(jīng)歷,沒(méi)有詳實(shí)的認(rèn)識(shí),以致注得不到位,就不去說(shuō)了,《十二月望后雨中過(guò)羅崗洞探梅有寄》,就“硬傷”坦現(xiàn)了,“十二月望后”的“十二月”是農(nóng)歷,農(nóng)歷12月15日,是公歷的1913年1月21日,所以注釋說(shuō)“此詩(shī)作于1912年冬”是錯(cuò)的,《黃節(jié)詩(shī)選》(劉斯奮選注;廣東人民出版社1984)也是犯了同樣的錯(cuò)誤,只有《黃節(jié)詩(shī)集》(馬以君編;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1989)將其編為1913年才是正確的。再則,注“羅崗洞”在“廣州北郊”也是錯(cuò)的,應(yīng)是在東郊增城縣。
注丁寧詞《江城子》“熟梅天氣晚風(fēng)柔”一首,說(shuō)“此詞約作于1934年至1938年”,這是將此詞原收入的《丁寧集》的寫(xiě)作起訖年歲,完全不假思索地寫(xiě)上了。如此,遇到下面這首《鷓鴣天·歸揚(yáng)州故里作》,因?yàn)槭鞘杖搿稇褩骷返模摷瘜?xiě)作起訖年歲長(zhǎng)了,是1939年至1952年,所以就“不好意思”了,只好不加注釋。事實(shí)上,稍細(xì)讀丁寧詞集《還軒詞》(安徽文藝出版社1985),就會(huì)發(fā)現(xiàn)她的詞作排列都是編年的,即按時(shí)間順序,所以前詞是1934年,后詞因后面跟有《鵲踏枝·庚辰暮春》,“庚辰”是“1940”年,所以它也就立即可以“編年”為“1939年秋”了。而且這首詞的末句“秋來(lái)盡有閑庭院,不種黃葵仰面花”,對(duì)其不加注釋?zhuān)彩钦f(shuō)不過(guò)去的,所謂“不作向日葵”,正好是表達(dá)對(duì)投靠日寇者的鄙夷。因此,“注評(píng)”的“點(diǎn)評(píng)”說(shuō)是“寂寞而不凄苦,頗見(jiàn)閑適之趣”,就是瞎說(shuō)了。“注評(píng)”之所以會(huì)有這些失誤,我個(gè)人揣測(cè),應(yīng)該就是未讀《還軒詞》之故,“不種黃葵仰面花”,詞集本身就已經(jīng)注明了。
此外,我想說(shuō)的,是我的一個(gè)大困惑,“注評(píng)”本著“四為”標(biāo)準(zhǔn),而“落選”這些位,如王闿運(yùn)、黃遵憲、沈曾植、夏曾佑、陳獨(dú)秀、呂碧城、陳寅恪、吳芳吉、錢(qián)鐘書(shū)……我總覺(jué)得是莫名其妙的;再則,一本厚390頁(yè)(指實(shí)際選注部分)的書(shū),到第347頁(yè),都是1920年以前出生的,我想“為時(shí)代”而選,僅從篇幅上說(shuō),無(wú)論如何也是比例失調(diào)了。哎,怎么說(shuō)呢,事實(shí)上,選注新時(shí)代的舊體詩(shī),實(shí)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所以想“輕巧”地完成,是無(wú)論如何也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