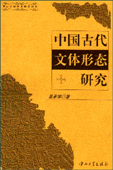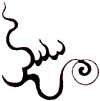|
盟誓之文,是中國古代一種文體,雖然人們對此比較陌生,但實際上它是先秦時代最為常見的應(yīng)用文體之一,在后代也有一定影響。《文心雕龍》中有"祝盟"一篇,并把盟誓列為"有韻之文",頗為重視。本文以先秦的盟誓之文為主要對象,研究其文體體制及文化意義。
一
盟誓制度從萌芽到形成,應(yīng)該經(jīng)過了一個相當(dāng)長的歷程。盟誓是從原始的詛誓咒語分化出來而獨立的。最早應(yīng)用于日常生活的個體與個體之間,以后才逐漸應(yīng)用于氏族與氏族、部落與部落之間,他們出于某些目的而締結(jié)各種協(xié)議,為了互相取信,唯一可行的方式是對神靈作出遵守諾言的保證。盟誓的出現(xiàn),是基于人們對于神祇的共同敬畏。只有這樣,神祇才可能成為各方所承認的見證人和監(jiān)督者。盟誓的核心內(nèi)容就是對不守信者,將由神祇加以懲罰,降下災(zāi)難。盟誓的威懾力,正是基于當(dāng)時人們對于神靈共同的崇拜與敬畏觀念,盟誓給參盟者造成一種巨大的約束力與心理壓力。在未有文字以前,最早的盟誓自然只能是口頭形式,文字產(chǎn)生以后盟誓才逐漸有文字為據(jù)。盟誓文體形態(tài)也是由最早的口頭上的簡單誓辭,逐漸發(fā)展到比較完整的文本,并形成正式的盟誓制度。
在春秋時期,戰(zhàn)與盟是諸侯之間經(jīng)常使用和交替使用的兩種手段。諸侯與諸侯、大夫與大夫、個人與個人之間契約的執(zhí)行,主要是靠盟誓來制約的。在此背景下盟誓也就成為諸侯之間一種非常重要和常用的活動,打開《春秋》三傳,觸目皆是諸侯之間的會盟與背盟的行為。
"盟"字在《左傳》出現(xiàn)640次;在《公羊傳》中出現(xiàn)162次;在《榖梁傳》中出現(xiàn)172次。 "誓"字在《左傳》出現(xiàn)22次;在《榖梁傳》中出現(xiàn)1次,在《公羊傳》中沒有出現(xiàn)。
可見"盟"字的使用比"誓"字頻繁得多,因為"盟"實際上往往就包含了"誓"的內(nèi)容。
諸侯之間的盟誓,正是社會發(fā)展到某種特殊階段的產(chǎn)物。《春秋》隱公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wèi)侯盟于瓦屋。"《榖梁傳》釋:"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于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zhì)子不及二伯。"五帝指傳說中的黃帝、顓頊、帝嚳、堯、舜。范寧說:"五帝之世,道化淳備,不須誥誓而信自著。"
三王謂夏、商、周三代。范寧說:"夏后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會,眾所歸信,不盟詛也。""二伯"指齊桓公、晉文公。《榖梁傳》認為,此處特別記載盟的日期,是含有微言大義的"春秋筆法"。諸侯之間的盟,正是彼此之間互不信任的產(chǎn)物。故范寧解釋說:"世道交喪,盟詛茲彰,非可以經(jīng)世軌訓(xùn),故存日以記惡。蓋春秋之始也。"所謂"世道交喪",是由于分裂與戰(zhàn)爭的出現(xiàn),人際關(guān)系產(chǎn)生欺詐與彼此之間的不信任。正是因為"世道交喪",才產(chǎn)生盟誓文體。因此,范寧在解釋《榖梁傳》時把盟詛的出現(xiàn)作為春秋時代開始的標(biāo)志,《榖梁傳》對于《春秋》筆法的闡釋不一定完全準(zhǔn)確,但對于誥誓、盟詛等文體產(chǎn)生以及交質(zhì)子等行為的時代性分析,卻是有道理的。除了《榖梁傳》隱公八年的記載之外,《公羊傳》桓公三年也稱:"古者不盟,結(jié)言而退。"也就是說古人不用歃血盟誓,但他們信守諾言,協(xié)定講定就告退。他們都認為在春秋以前,王與諸侯之間,有約定的誓言,但無詛盟。可見這種看法是古人的共識。
古代文體學(xué)家也普遍接受這種歷史觀念,他們認為在夏、商、周即三王時代,人們之間互相信任,彼此遵守諾言。所以人與人之間,集團與集團之間的協(xié)議經(jīng)過商定,一經(jīng)達成共識就執(zhí)行,不需用詛咒加以約束。劉勰《文心雕龍·祝盟》說:"在昔三王,詛盟不及,時有要誓,結(jié)言而退。"明代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盟》與劉勰所言相同,他進一步認為在三王時代人們之間也有誓言,但僅僅如此,并不涉及以鬼神來懲罰的詛咒。詛盟的出現(xiàn)與興盛是因為人們之間缺乏忠信,才需要借助于鬼神。"三代盛時,初無詛盟,雖有要誓,結(jié)言而退而已。周衰,人鮮忠信,于是刑牲歃血,要質(zhì)鬼神,而盟繁興,然俄而渝敗者多矣。"
這些文體學(xué)家也都注意到盟誓產(chǎn)生的特殊時代性問題。
關(guān)于"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之說,應(yīng)該加以具體分析。古人之所以提出這種歷史觀念,主要是為了強調(diào)誥誓盟詛文體的時代性。他們所指的誥誓盟詛,又是特指形態(tài)成熟有規(guī)范的官方文體。因為口頭的盟誓形態(tài)在春秋時代之前應(yīng)該已經(jīng)出現(xiàn),但是盟誓系統(tǒng)制度的形成以及在國與國之間的大規(guī)模的應(yīng)用,則是在春秋以后。也就是說,在春秋時期特定的政治、歷史環(huán)境下,盟誓之風(fēng)盛行。
據(jù)《周禮·秋官》記載,當(dāng)時專門有"司盟"之職,主管盟書及其禮儀:"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其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眾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為司盟共酒脯。"司盟所管范圍甚廣,邦國之盟是其大者,此外百姓犯法違約,使其盟詛,誓不再犯;保存百姓之間買賣、借貸的券契副本,以備出現(xiàn)爭議時驗證;獄訟當(dāng)事人先必盟詛,保證所供為事實,如有虛假將受罰。可見先秦盟誓使用范圍是相當(dāng)廣的,本文主要研究其邦國之盟。
從現(xiàn)存文獻看來,三代也有用于誓師的誓文。正如《周禮·士師》說:"誓,用于軍旅。"是出征時告誡將士之辭。通常為了師出有名,首先要聲討討伐對象的罪行,再表示齊心協(xié)力參加戰(zhàn)斗的決心。《尚書》中的誓體也較多,有《甘誓》、《湯誓》、《牧誓》、《費誓》、《秦誓》。這些誓與后來的盟誓本質(zhì)是不同的,它雖然也以神祇上帝作為眾人實施行動的監(jiān)察,但其所誓是同一集團或同盟為了統(tǒng)一完成某一目的所作的,是為了壯大聲威而不是因為彼此之間互不信任。春秋時期的盟誓制度產(chǎn)生的背景是王室衰微,諸侯蜂起。諸侯之間,諸侯與王室之間,為了各自的長遠利益或暫時利益而進行盟誓,但彼此之間又缺乏真正的誠信,只能以神譴和詛盟加以約束和威脅。春秋的盟誓與先前的盟誓最大的不同,是采用了詛盟,而且形成一整套完整的禮儀形式。而先前的盟誓正如范寧說的"眾所歸信,不盟詛也"。
所以,從單純的諾言到盟誓制度,標(biāo)志著人類之間的信任已經(jīng)出現(xiàn)某種程度的危機,只好借助于外在的力量即鬼神崇拜的介入來消除這種危機。"盟"的形式也有一個發(fā)展過程,最初可能源于部落之間以盟的儀式聯(lián)合起來,處理部落之間的大事。春秋初期,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通過盟的形式聯(lián)合起來對付第三國或另外的軍事集團,同盟國內(nèi)部的關(guān)系還是比較平等的,春秋中期以后,出現(xiàn)由盟主來主盟的局面。
盟誓與古代巫術(shù)之詛咒有密切關(guān)系。《尚書·無逸》:"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是說如果統(tǒng)治者變亂先王正法,百姓內(nèi)心怨恨他們,在口頭詛咒他們。孔穎達疏云:"詛祝謂告神,明令加殃咎也。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襄十七年《左傳》曰:'宋國區(qū)區(qū),而有詛有祝。'《詩》曰:'侯詛侯祝。'是詛祝意小異耳。"
盟往往包括了詛的內(nèi)容,但盟與詛又不同。《詩經(jīng)·小雅·何人斯》:"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傳》曰:"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孔穎達疏曰:"盟大而詛小,盟詛雖大小為異,皆殺牲歃血告誓明神,后若背違,令神加其禍,使民畏而不敢犯也。"
所謂"三物"也就是豕、犬、雞,以三牲來求神降禍于對方,這就是詛。 《左傳》隱公十一年記鄭伯讓每百人拿出一頭豬,每二十五人拿出一條狗或一只雞,用來詛咒射殺潁考叔的人。當(dāng)詛用于正規(guī)場合以求神對不守諾者降禍時,實際上也就是盟了。所以,盟與詛往往是合二為一的行為。如《左傳》襄公十一年春記季武子將作三軍,"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又《左傳》定公六年"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盟誓的本質(zhì)是用外在的、強制的、帶有威脅性的形式來維持彼此的誠信,其產(chǎn)生的前提恰是彼此缺乏誠信。然而真正誠信是不須詛盟的,正如劉勰在《文心雕龍·祝盟》篇所說:"信不由衷,盟無益也。""忠信可矣,無恃神焉。"如果缺乏誠信,詛盟作用也不大。《榖梁傳》僖公五年曰:"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是說諸侯尊敬周王世子,不敢與周王世子會盟,因為凡是結(jié)盟,都是由于彼此之間不相信任,只好通過結(jié)盟的方式,約束雙方的誠信。各諸侯國當(dāng)然不敢對尊敬的周王世子表示不誠信之意了。"盟者,不相信也。"此句深刻地揭示了盟誓的社會心理基礎(chǔ),非常值得注意。諸侯的會盟活動,正是為了消除各方彼此之間的不信任。《左傳》昭公三年謂"有事而會,不協(xié)而盟。"也就是說,有事才會見,不和睦才盟誓。《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說"不協(xié)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也就是說,因為不和協(xié)的緣故,因而乞求在尊神面前明白宣誓,以求天意保佑。既然盟誓是一種在彼此之間不信任的基礎(chǔ)上強行取信的文體,這種文體的內(nèi)部就必然存在著難以調(diào)和的矛盾和不可克服的先天缺陷,而盟誓所體現(xiàn)出來的復(fù)雜的文化意蘊也正是根于此。
從理論來說,當(dāng)時人們之所以盟誓,正是認為盟誓是非常鄭重之事,是有約束力的,應(yīng)該遵從,這也是人們使用盟誓的初衷。《左傳》成公十一年"齊盟,所以質(zhì)信也。"《左傳》襄公九年:"盟誓之言,豈敢背之。"《左傳》昭公十六年:"世有盟誓,以相信也。"《左傳》哀公十二年,子貢說:"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jié)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茍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可以說,盟誓正是在當(dāng)時具體歷史條件下人們消除彼此之間信任危機所能采用的最理想的方式--盡管其缺陷是顯而易見的。
二
正因為如此,盟誓的外在形式便顯得重要起來。我們看到先秦時代諸侯之間的盟誓,是一種非常莊重神圣的儀式,是當(dāng)時重要的禮制之一。盟與誓形式上有所差異,盟用牲而誓不用牲,只是約言而已,所以盟比起誓要更為鄭重正規(guī)些。《禮記·曲禮下》云:"諸侯使大夫問于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鄭玄注:"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聘禮今存,遇會誓禮盟亡。誓之辭,《尚書》見有六篇。"孔穎達疏曰:"約信曰誓者,亦諸侯事也。約信以其不能自和好,故用言辭共相約束,以為信也。若用言相約束以相見,則用誓禮。故曰誓也。""涖牲曰盟者,亦諸侯事也。涖,臨也。臨牲者,盟所用也。盟者,殺牲歃血,誓于神也。若約束而臨牲則用盟禮。"
盟誓是重要的禮制,故有些負責(zé)此類禮儀的人員。《周禮·春宗伯·詛祝》謂當(dāng)時有"詛祝"者:"詛祝掌盟、詛……,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zhì)邦國之劑信。"賈公彥疏曰:"作盟詛之載辭者,為要誓之辭,載之于策,人多無信,故為辭對神,要之使用信,故云以敘國之信用。"
《周禮·秋官·司盟》謂當(dāng)時有司盟之官:"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所謂"載書"也就是指盟辭。鄭玄注:"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于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于上,而埋之謂之載書。"
孔穎達在《禮記·曲禮下》疏時所說更為具體:"盟之為法,先鑿地為方坎,殺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
從上述諸說法看來,盟禮最主要的儀式是殺牲歃血而在神靈面前發(fā)誓,以神靈為盟誓之證。這些神靈大致可分為上帝諸神和其他自然神如日月山川之類。盟禮的過程大致是先掘地為方坎,在坎上殺牲,殺牲時先割牲耳,盛于珠盤,取牲血,盛于玉敦。由司盟蘸血寫盟書,并宣讀盟書。主盟者先微吸牲血(或以血涂口旁),然后由參盟者依次為之,這叫歃血。以歃血形式來取信,正是原始社會人們對于血的宗教觀念的殘余。在盟誓的禮儀中歃血的次序是以尊卑為序的,《左傳》哀公十三年記載"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于周室,我為長。晉人曰:于姬姓,我為伯。"吳國與晉國爭著要先歃血其實也就是爭當(dāng)盟主地位。又《國語》晉語八"宋之盟,楚人固請先歃。"也是意在爭盟主地位。為什么要殺牲,除了歃血之外,還另有含義。依孔穎達說:"殺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
諸侯之間的盟約,要有復(fù)本,除了埋于坎之外,還分別藏于司盟之府等地方,以備檢勘。《周禮·秋官·大司寇》:"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nèi)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孫詒讓在《周禮正義》卷六九中說:"蓋凡盟書,皆為數(shù)本,一本埋于坎,盟者各以一本歸,而盟官復(fù)書其辭而藏之。其正本藏天府及司盟之府,副本又別授六官,以防遺失,備檢勘,慎重之至也。"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展喜對齊侯說:"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這段話正可證《周禮·秋官·大司寇》所言不虛。據(jù)曾憲通先生考據(jù),盟誓之辭書于策,有數(shù)本之多,且有正本副本之別,當(dāng)由司盟之官職掌"誓盟之璽"以鑒別之。他認為《古璽匯編》中有七方古璽齊璽皆與誓盟有關(guān)。盟誓用璽,史書失載,這些古璽可補史籍之闕,彌足珍貴。
陳夢家在《東周盟誓與出土載書》一文中,根據(jù)《左傳》并參考《周禮》以及漢、晉、唐注家所述,對東周盟誓制度作了全面的考察,總結(jié)出春秋時盟誓的禮儀及程序。它們分別是:"為載書"、鑿地為"坎"、"用牲"、盟主"執(zhí)牛耳",取其血、"歃"血、"昭大神",祝號、"讀書"、"加書"、"坎用牲埋書"、載書之副"藏于盟府"十項。他還認為戰(zhàn)國的盟誓制度與春秋相仿。
我以為這里對于先秦盟誓制度的總結(jié)是比較全面準(zhǔn)確的。
但是除了"盟在盟府"正規(guī)誓禮之外,還可以有其他形式的誓禮,孔穎達《毛詩正義·何人斯》疏曰:"若臨時假用其禮者,不必有牲,故《左傳》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入楚師,登子反之床,子反懼,而與之盟。皆無牲也。"
個體之間取信之誓的形式也可能不同。如《左傳》定公十年:"荀躒言于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杜預(yù)解釋說:"為盟書沉之河。"《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晉公子重耳為了表白不辜負子犯,誓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并且"投其璧于河"。這種誓禮比較簡單,是以自然神為見證,或以盟書或以玉璧投之河。以上是文獻中關(guān)于先秦時代盟誓的一些記載,這可能是當(dāng)時的慣例,但盟誓的儀式也是因地而異、因人而異的。劉安《淮南子·齊俗》談到各地人們?nèi)⌒欧绞讲煌?故胡人彈骨,越人契臂,中國歃血也。所由各異,其于信一也。"高誘注云:"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骨中,飲以相詛;刻臂出血,殺牲歃血,相以為信。"他認為胡人、越人與中國的盟誓目的都是為了取信,但是具體的方式不同,胡人將酒置于人頭骨中,飲酒為誓,越地人在手臂上契刻出血,而"中國"(即與"四夷"
相對而言的華夏)則是歃血為盟。
1965年至1966年,山西考古工作者發(fā)掘了侯馬市東的盟誓遺址,發(fā)掘了三百多個坑,出盟書的坑共四十三個,這批盟書共有五千余。侯馬出土的盟書,是我國東周時期晉國的官方文獻,盟書是用朱色或墨色寫在石片或玉片上的盟辭誓言,當(dāng)時稱為"載書"。侯馬盟書的發(fā)現(xiàn),有重大的史學(xué)意義。從文體學(xué)史研究來看,對于我們了解古代盟書提供了非常寶貴的實物依據(jù)。據(jù)文獻記載,盟誓的禮儀程序是先鑿地為坎,再殺牲,然后將盟書與牲埋在坎中。侯馬盟書出土情況大體相同,可證實原先的記載是比較可信的,但是侯馬盟書的禮儀有些特殊情況,一是在鑿地為坎后,先在壁龕中存放璧或璋一類玉幣,而后埋盟書與牲;二是文獻記錄盟誓所用之牲為牛、豕或牛、豕、犬、雞,但是侯馬盟誓遺址所用牲卻是以羊為主,兼用牛、馬,并無用豕。張頷等人整理的《侯馬盟書》將這些盟書分為宗盟、委質(zhì)、納室、詛咒、卜筮五類。
鄭玄說古人"用血為盟書",而侯馬盟書用毛筆書寫,字跡一般為朱紅色,少數(shù)黑墨色,與記載不同。郭沫若認為,"以血書盟誓,這樣做的缺點是不甚顯著。看來,在戰(zhàn)國時代或更早,血書便改用朱書代替了。古人有'丹書',蓋凡盟誓書以丹,后人猶沿用'書丹'這個詞匯。"關(guān)于盟誓的文體,郭沫若認為,"古時涖盟,除總序外,人各具一盟書,盟文相同,而人名各異,不是把所有涖盟者之名字寫在一通盟文之上。"
盟誓就是對自然神(如日月山川之類)或祖先神作出信守諾言的保證,并表示如果不遵守諾言,國家、氏族乃至后代都將降臨種種災(zāi)難,無疑這些災(zāi)難都是最為嚴(yán)重和可怕的,因此也最有威懾力。盟誓對于盟誓者之所以有約束,首先是建立在當(dāng)時人們對于神祇的普遍敬畏和極端迷信。當(dāng)時的獄訟也采用盟詛之法,《周禮·秋官司寇·司盟》說:"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訴訟者如果不提供實情,盟詛將使其受到神的嚴(yán)懲。《墨子·明鬼》記載一個非常復(fù)雜的官司,"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斷案者只好讓兩位當(dāng)事人盟誓,其中一人其辭尚無讀完,"羊起而觸之,折其腳,祧神而槁之,殪之盟所。"《墨子》所錄,雖是民間故事,卻應(yīng)該真實地反映出當(dāng)時人們普遍的社會心理,即鬼神會嚴(yán)懲不遵盟誓者。
但除此之外,我們不能忽視中國古代社會普遍認同的誠信道德規(guī)范也對盟誓產(chǎn)生很大的作用。前者對于盟誓者產(chǎn)生巨大的心理壓力,后者對盟誓者產(chǎn)生社會輿論監(jiān)督。《左傳》成公元年:"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背盟者必敗,因為不祥、不義而神人不助。可見"祥"與"義"即迷信觀念與道德觀念兩者是盟誓的支柱,也是彼此遵盟的共同心理基礎(chǔ)。
春秋時簡單的誓辭格式大致是"所不……者,有如……",《左傳》定公六年孟孫曰"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孔疏:"諸言'有如'皆是誓辭。"此言甚是,如下數(shù)例: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左傳》文公十三年)
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左傳》宣公十七年) (殖綽)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左傳》襄公十八年)
(樂懷子)乃復(fù)撫之曰:"主茍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左傳》襄公十九年) 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于君焚丹書者,有如日。"(《左傳》襄公二十三年)
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子行抽劍曰:"……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左傳》哀公十四年) 這些"有如"格式的誓言是什么意思呢?《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杜注:"言與舅氏同心之心如此白水,猶《詩》言'謂予不信,有如皎日。
'"正義:"諸言'有如'皆是誓辭,有如日,有如河,有如皎日,有如白水,皆取明白之義。言心之明白,如日如水也。有如上帝,有如先君,言上帝先君明見其心,意亦同也。"認為此誓取"明白"之意。但也有另外的理解,《國語·晉語》"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沈璧以質(zhì)。"韋昭注:"如,往也。質(zhì),信也。言若不與舅氏同心,不濟此河,往而死也。因沈璧以自誓為信。"韋昭釋"如"為"往",在此例子中可通,但以其他相通句式的例子衡之,則不可通。也有學(xué)者認為"如日"、"如河"、"如白水"、"如上帝"、"如先君"是發(fā)誓時以各種神靈為證。如楊伯峻注《左傳》僖公廿四年"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意謂河神鑒之。"
沈玉成譯為"有河神為證。" 的確,這種注解是有道理的,古人是指天地神靈為證發(fā)誓的,如《國語·越語下》記越王勾踐對范蠡發(fā)誓說:"后世子孫有侵蠡之地者,使無終于越國,皇天后土四鄉(xiāng)地主正之。"這就是以神為正之例。不過,從"所不……,有如……"這個句式來看,似乎是"如果不……,就將會……"的詛誓之辭。所以錢宗武《誓辭"有如"注解質(zhì)疑》一文認為,《左傳》中的"有如"誓辭凡十例,皆為表示假設(shè)關(guān)系的復(fù)句,
常用句型為"所不……者,有如……"的格式。"所"即"若"。"有"為語氣副詞,訓(xùn)"如"為"順從、聽從","有如白水"、"有如河"即"聽從河神的懲罰","有如此盟"即"聽從這次盟約的懲罰","有如日"即"聽從天神的懲罰","有如先君"即"聽從先君的懲罰","有如陳宗"即"聽從陳氏歷代祖宗的懲罰"。從語法上看,這種解釋比較好理解,而且其含義比較符合一般盟誓"有渝此盟,明神殛之"通例的內(nèi)在邏輯。
以上數(shù)例,都是一般的誓言,比較簡單,而盟誓的正規(guī)形式應(yīng)該復(fù)雜得多,內(nèi)容也應(yīng)該更為豐富。由于文獻記載之不同,先秦時期的盟誓,或詳或略。其中以《左傳》所載為詳,下舉數(shù)例:
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六月,晉人復(fù)衛(wèi)侯。寧武子與衛(wèi)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wèi)國,君臣不協(xié),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捍牧圉?不協(xié)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后,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后不貳。(《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兇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xié),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左傳》成公十二年)
秋,七月,同盟于亳。……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奸,毋留慝,救災(zāi)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左傳》襄公十一年)
從以上所載的盟誓,大致可以看出當(dāng)時盟誓已經(jīng)形成一定的樣式體制。綜合《左傳》記載與侯馬盟書等實例,不難看出先秦盟誓大致是由三部分組成的:(一)盟誓緣起,即敘述各方之所以盟誓的原因;(二)遵誓要求。即列出盟誓各方所應(yīng)遵守的具體條款;(三)違盟惡果,即參盟各方共同約定,如果盟誓者有不遵盟的,他們本人及家人,甚至其國家即將受到鬼神的嚴(yán)懲。
后代的盟誓文的體制大致沿襲先秦盟誓。劉勰在《文心雕龍·祝盟》中說:"夫盟之大體,必序危機,獎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靈以取鑒,指九天以為正,感激以立誠,切至以敷辭,此其所同也。"劉勰認為盟誓的大致規(guī)格,必定要敘述危機,獎勵忠孝之心,約定生死與共,同心協(xié)力,請神靈鑒察,指上天為證,以真誠之心和懇切之辭來寫盟誓。這可以說是對盟誓體制比較全面中肯的總結(jié),如劉勰所盛贊的臧洪與劉琨的兩篇盟誓,就是如此。《后漢書·臧洪傳》說臧洪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shè)壇盟誓。臧洪先登壇,歃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tǒng)。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伷,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并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jié)。隕首喪元,必?zé)o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又如劉琨《與段匹磾盟文》:
天不靜晉,難集上邦,四方豪杰,是焉煽動,乃憑陵于諸夏,俾天子播越震蕩,罔有攸底。二虜交侵,區(qū)夏將泯,神人乏主,蒼生無歸,百罹備臻,死喪相枕。肌膚潤于鋒鏑,骸骨曝于草莽,千里無煙火之廬,列城有丘曠之邑,茲所以痛心疾首,仰訴皇穹者也。臣琨蒙國寵靈,叨切臺岳;臣磾世效忠節(jié),忝荷公輔。大懼醜類猾夏,王旅隕首喪元,盡其臣禮。古先哲王,貽厥后訓(xùn)。所以翼戴天子,敦序同好者,莫不臨之以神明,結(jié)之盟誓。故齊桓會于邵陵,而群后加恭;晉文盟于踐土,而諸侯茲順。加臣等,介在遐鄙,而與主相去迥遼,是以敢干先典,刑牲歃血。自今日既盟之后,皆盡忠竭節(jié),以翦夷二寇。有加難于琨,磾必救;加難于磾,琨亦如之。繾綣齊契,披布胸懷,書功金石,藏于王府。有渝此盟,亡其宗族,俾墜軍旅,無其遺育。
《文心雕龍·祝盟》盛贊"臧洪歃辭,氣截云蜺;劉琨鐵誓,精貫霏霜",可見這是先秦以后有代表性的盟誓作品。由于先秦時代的盟誓規(guī)范和完整的文本甚少,所以臧洪與劉琨兩篇盟文,為我們了解古代盟誓文體提供了寶貴的文本。
先秦文獻對于盟誓的記載往往只記其事,所載盟誓之文往往甚略,有的甚至闕然不載。《左傳》桓公元年與鄭伯盟于越,"盟曰:渝盟無享國!"這肯定是對于原本盟文的省略。而同一盟誓,在不同文獻記載中,詳略也不一。《左傳》僖公九年:"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既盟之后,言歸于好。'"非常簡略,然而在《榖梁傳》則記載:"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但是在《孟子·告子下》篇中記載: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歸于好。"
《孟子》所記錄之盟,共有五則盟約。所以可以推斷,史傳中所載的盟誓之文,大體都只是截裁其中部分,并不是全文刊載。葵丘之會桓公與諸侯的盟誓,有些奇怪,倒像是道德方面的契約,這也許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諸侯盟誓的一種方式吧。而在僖公三年《公羊傳》記載諸侯的盟會,桓公在大會上提出各國共同遵守的盟約是:"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就是說不要阻斷川谷,不要囤積糧食,不要變換當(dāng)立的太子,不要以妾為妻,這些也都是道德方面的規(guī)范。相近的盟誓如《說苑·反質(zhì)》所記載:
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奸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奸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政,無以奸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于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
所盟誓的內(nèi)容與葵丘之會的盟誓相近,可見有些盟誓的內(nèi)容可以超出戰(zhàn)爭的范圍,是由主盟者對諸侯國禮義上的要求,但其目的也是為了提高主盟者的地位和號召力,增強其凝聚力。
三
諸侯盟誓之后,又常有"尋盟"之舉,"尋盟"的本義是重申前盟或舊約,之所以要尋盟,正反映出盟誓之后,參盟者沒有完全執(zhí)行盟誓。《左傳》哀公十二年:
吳子使大宰噽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jié)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茍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吳王讓太宰噽來尋盟,而子貢說,如果有盟約,就不能改變了。如果盟約可以重溫,也就可以冷落。《左傳》昭公十三年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同意說:"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也就是說,諸侯討伐有二心的國家,才有重溫舊盟的必要。如果都聽從命令,還重溫什么舊盟?但是在春秋時代,尋盟幾乎與盟誓一樣,都是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
有尋盟,也就有背盟。盟的目的是求其互相信任,而其前提恰是互相不信任,所以既盟之后經(jīng)常出現(xiàn)不遵盟的情況。《左傳》桓公十二年君子曰:"茍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盟誓越頻繁,越反映出盟誓的不受尊重,故《詩》中把屢盟看成添亂。春秋時期,經(jīng)常出現(xiàn)背盟的情況,尤其是小國,更是根據(jù)實際的利害關(guān)系隨時調(diào)整與大國的盟約。《左傳》襄公九年記載,鄭國剛與晉國盟誓,載書說:"自今日既盟之后,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但不久,楚共王討伐鄭國,鄭國馬上背盟。鄭國背盟的理由是,我們原先的盟約就說"唯強是從",只要是強大的國家我們就服從,現(xiàn)在楚師強大,我們當(dāng)然要服從,實際上我們并無背盟。晉國是憑借武力要挾訂盟的,這種盟約本來說沒有誠信可言,神靈不會理睬在要挾情況下訂立的盟約,只有真誠的盟誓神靈才會親臨,所以背叛與晉國訂的盟約是完全正當(dāng)?shù)摹_@種既立盟又不一定遵盟的情況反映了當(dāng)時人們對神、對現(xiàn)實、對信用等宗教與道德矛盾的態(tài)度,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春秋以至戰(zhàn)國時代的誓盟,在許多情況下,其實是以強凌弱的結(jié)果,是弱者在強者軍事的壓迫之下,不得已而盟的,故出現(xiàn)所謂城下之盟,這實際上是不平等的條約。如鄭國與晉國盟誓:"自今日既盟之后,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左傳》襄公九年)這種盟誓僅僅體現(xiàn)強勢國家單方面的意志,要求弱國對強國惟命是從,這是何等的不合理。但另一方面弱國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也會采用暴力劫持等非正常手段以強求對方訂盟,這就是劫盟。《文心雕龍·祝盟》:"周衰屢盟,弊及要劫,始之以曹沫,終之以毛遂。"如《史記·刺客列傳》記齊桓公與魯莊公會盟,曹沫以匕首劫持齊桓公,要他退還侵占的魯?shù)亍!妒酚洝て皆袀鳌氛f秦圍趙國邯鄲,平原君去楚國求救欲結(jié)盟,長談未果,門客毛遂按劍上前,陳述利害,終于迫使楚王訂盟。據(jù)《史記》記載,此后"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還是遵守了盟約。可見人們寧愿冒險地采用非正常的手段來獲得盟約,這種"要盟"、"劫盟"之所以出現(xiàn),正說明事后盟誓仍有較強的制約性。"背盟"與"劫盟"正是從不同角度反映出當(dāng)時人們對于盟誓普遍存在的相當(dāng)矛盾復(fù)雜的心態(tài)。
我以為,古代文體也折射著人類文化與心理的發(fā)展和進化。盟誓之文含蘊著豐富的文化意義,忠信與禮義是人類走向階級社會之后所急需具備的。正如《禮記·儒行》所說:"忠信以為甲胄,禮義以為干櫓。"忠信與仁義,是當(dāng)時人們維持社會秩序與自我保護的武器。盟誓文體的出現(xiàn),正反映了人類對于彼此之間信用的需要和強調(diào),而這種對信用的需要和強調(diào)的前提是不守信用的出現(xiàn)。正是社會出現(xiàn)爾詐我虞的現(xiàn)象,才需要作出所謂"我無爾詐,爾無我虞"的許諾。在渾渾沌沌的原始社會里,人們之間的信用不需要強調(diào),它以天然的狀態(tài)存在著。當(dāng)人們感到需要強調(diào)信用之時,正是信任開始出現(xiàn)危機之日。《禮記·檀弓下》說:"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此語耐人尋味。《老子》三十八章則對人類社會發(fā)展作出這樣的總結(jié):"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這是以道家的觀念來考察仁義道德在人類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的內(nèi)在矛盾性。從某種角度來看,盟誓制度的出現(xiàn),也正是反映出禮制是"忠信之薄而亂之首"的現(xiàn)象。
人們對于遵守信用的監(jiān)察,此責(zé)職最先是由神秘的神靈和社會公理、輿論來擔(dān)任的,最初人們對于鬼神的監(jiān)督作用是深信不疑的,但現(xiàn)實教訓(xùn)了人們,守信者未必就受到神的保佑而失信者也未必就受到懲罰,同時強權(quán)的力量又遠非公理與道德所能制約的。于是盟誓的作用自然也就趨于弱化,人們在盟誓的同時也要求以其他形式來輔佐盟誓的執(zhí)行。故《左傳》成公十三年說:"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在盟誓之外,增加婚姻聯(lián)系,以血肉之軀來擔(dān)保,要比神靈的監(jiān)察和道德的約束更為實際。婚姻既是感情的聯(lián)盟,某種程度上也具有人質(zhì)的性質(zhì)。由于盟誓約束力實際上不大,于是又出現(xiàn)人質(zhì)之法,在盟會之外,以國君之子或有血緣關(guān)系的親屬為人質(zhì),以之作為實施盟約或其他許諾的保障。在極重親情的古代中國,人質(zhì)的作用是可想而知的。春秋時期以人質(zhì)來取信也是非常早就出現(xiàn)的。如《左傳》隱公三年,記載周平王與鄭國互相以人作抵押。周平王的兒子狐到鄭國作人質(zhì),鄭莊公的太子忽到周朝作人質(zhì)。于是《左傳》的"君子曰"發(fā)了一番議論:"信不由中,質(zhì)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zhì),誰能間之?……行之以禮,又焉用質(zhì)?"《左傳》宣公十二年,記楚國攻破鄭國,鄭襄公肉袒牽羊向楚莊公求和,楚莊公最后同意了,于是"潘尪入盟,子良出質(zhì)。"楚國的潘尪入城結(jié)盟,鄭國的子良到楚國做人質(zhì)。這是以人質(zhì)的方式來補充盟誓。以婚姻和人質(zhì)作為盟誓的附加物以保障信用,可見鬼神對于人的威脅或者說人對于鬼神的敬畏在逐漸減弱,人們對于社會公理與道德約束能力也逐漸失去信心,這意味著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危機逐漸增大。人質(zhì)之出現(xiàn),其實反映出人們對于盟誓可靠性的懷疑,而從更本質(zhì)的意義來看,是復(fù)雜殘酷的現(xiàn)實,使人們對于以取信于鬼神的形式產(chǎn)生不信任感,這也許是人們認識能力的一種進步,同時,也意味著人類正逐漸從樸素、單純而蒙昧走向現(xiàn)實和狡獪,神靈的作用已經(jīng)讓位給強權(quán)與暴力。但是既然還需要盟誓,也就意味著神靈的權(quán)威還沒有完全退位,還有相當(dāng)?shù)牧α俊?/p>
隨著社會的發(fā)展,社會契約和法律的作用越來越大,人與人之間,族與族之間,國與國之間的關(guān)系,逐漸由法律與契約來協(xié)調(diào)和制約。當(dāng)然,實際上就是強權(quán)與實力起著主導(dǎo)地位,強權(quán)取代了神權(quán)。秦漢以后,官方的盟誓大致流為形式,而不具備巨大的威懾力,盟誓在政治與外交中的作用明顯弱化了。而在民間社會,盟誓傳統(tǒng)從未斷絕,它仍然保持著特有的威嚴(yán)與魅力,比如民間的結(jié)義拜盟與一些秘密社團都非常重視盟誓,
盟誓一直起著難以代替的重要作用,甚至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之中也殘存一些古老盟誓的遺跡。
以上是我們對于先秦盟誓文體及其文化本質(zhì)所作的初步探討,在盟誓這種文體上,交織著在當(dāng)時那種特殊時代的社會生活之中,神權(quán)與強權(quán)、蒙昧與理智、誠信與猜疑的色彩。可以說,盟誓是中國古代歷史最為悠久,文化內(nèi)涵最為豐富的文體之一。在我們看來,盟誓制度的出現(xiàn)與衰落,盟誓傳統(tǒng)的綿延不絕,是和人類文明與人性發(fā)展有密切關(guān)系的。
(原載《文學(xué)評論》2001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