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201520152105.com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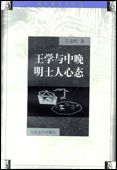
左東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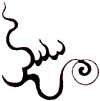
|
新書介紹——《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 |
|
|
第一章:明前期的歷史境遇與士人人格心態的流變 第二節、理學、八股與明代前期士風 三、理學流行中的士人人格與心態 當理學的宗旨與科舉入仕的動機逐漸相背離時,并非所有士人均屈從于 勢而同流合污。他們堅持自我的人生理想,以弘揚圣學為己任,視科舉為俗 學,決不肯為利祿而有損其節操。薛瑄是較早對科舉發難的明儒,他非常直 率地說:“道之不明,科舉之學害之也。”(《讀書錄》卷八)這是因為, 許多士子將經書與科舉視為二物,不能有切于自我心性之修煉,所謂“習舉 業者,讀諸般經書,只好安排作時文材料用,于己全無干涉。故其一時所資 以進身者,皆古人之糟粕;終生所得行事者,皆生來之習氣。誠所謂書自書, 我自我,與不學者何以異。”(同上卷一)而其要害則在于“借經書以徼利 達。”而著名學者吳與弼讀朱子《伊洛淵源錄》后,便立志學為圣人,“而 盡焚當時舉子文字,誓必至乎圣賢而后已。”(《康齋文集》卷十二,《跋 伊洛淵源錄》)他果然不再參加科考,以躬耕講學而終其一生。此二位均為 明前期的大儒,故可作為持守程朱理學的士人代表。剖析此二人,便可透視 此類士人的人格與心態。 薛瑄(1389—1464),字德溫,號敬軒,河津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宣 德中授御史,景帝時任大理寺丞,英宗復辟后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后 致仕卒于家。吳與弼(1391—1469),字子傅,號康齋,撫州崇仁人。平生 講學不仕,天順初被朝廷征召授諭德,旋辭歸,卒于家。此二人從品格上講 均為重節操的高潔儒者,他們淡泊名利,守道直行,誠可作為士人的楷模。 薛氏的耿直倔強曾被多種明史著作及野史筆記所記載稱頌,宣德間為御史時, 臺閣重臣三楊欲識其面,他卻認為自己司糾彈之職而不應私見公卿大臣,從 而拒絕相見。尤其在正統年間,宦官王振因同鄉關系使召其為大理寺少卿, 三楊勸其前往王振處一見,薛拒絕不行;三楊無奈托李賢勸之,薛義正詞嚴 地說;“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后來“公卿見振多趨拜,瑄獨 屹立。振趨揖之,瑄亦無加禮。”為此他得罪了權傾朝野的王振,終于被誣 蔑下獄,差點丟掉了性命。景泰間又因平反冤獄而與大臣王文發生沖突,亦 無絲毫畏避意,以致王文惱怒地說:“此老倔強猶昔。”(上所述均見《明 史》卷二八二《儒林一》)至于吳與弼則更因其甘居草野并多次拒絕征聘, 而被明人譽為難以企及的高人,連輕易不肯許可人的大怪杰李贄亦贊其曰: “公風格高邁,議論英偉,胸次灑落,師道尊嚴。善感悟啟發人,其學術質 任自然,務涵養性情,有孔門陋巷風雩之意。”(《續藏書》卷二一,《聘 君吳公》)薛、吳二人作為獨善其身的典型,顯示了程朱理學的確對士人自 我節操的培育具有很大的作用,使明前期不少士人具備了儒家理想的倫理主 義人格特征。 但是過于嚴峻狹隘與理想化的程朱理學對士人人格的塑造并不全都具有 正面的意義,起碼它在下述三個方面對于士人人格產生過負面效應。首先是 過分執著于倫理理想會使士人在現實的政治中缺乏應有的適應能力。前人在 研究以薛氏為代表的關學時,多強調其追求實用的實踐品格,這大凡是指下 述二個方面:一是在理論上缺乏自我創造性,基本恪守宋儒原有理論而踐履 之,即其本人所言:“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 (《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上》)二是在行動上強調與理論的一致性,他 說;“見得理明,須一一踐履過,則事與理相安,而皆有著落處,若見理雖 明,而不一一踐履過,則理與事不相資,終無可依據之地。”(《續讀書錄) 卷二)這些主張都不能算錯,特別是第二點,頗有與后來陽明所言知行合一 相近之處。但任何理論進入現實領域時都不可能絲毫不走樣,這在先儒那里 稱之為通權達便,尤其象程朱理學那樣高遠的理想化倫理原則,在復雜多變 的現實政治領域必然會遭遇到許多麻煩。薛夫子的決不拜官公朝而謝恩私室 當然顯示了他做人的光明磊落,但他之不能如三楊那般從容地應付于官場也 是顯而易見的。且不說他的多次下獄遭貶的麻煩,即使其本人亦曾屢次辭官, 說明了他也自我感覺到對官場的不適應。他在天順年間致仕時,臨行前對岳 正囑咐道:“英氣太露,最害事。”(《明儒學案》卷七,《河東學案上》) 這或許是針對岳正耿直的個性而進行的勸告,但又何償不是他一生的人生經 驗的總結呢?吳與弼的遭遇則更能說明問題。當他在天順初被征召至朝中時, 沒多久便堅決辭朝歸鄉了。關于他辭官的原因,前人曾有過種種的推測,《 明史》本傳言因大臣尹直與其有隙,遂毀謗之,故而還鄉;有人認為是他本 欲做尹、傅之類的帝王之師宰,朝廷卻未能滿足其要求而辭職;黃宗羲則力 辯其謬,認為是他預先知道“石亨必敗,故潔然高蹈。”其根據是吳與弼回 鄉后曾對人解釋何以辭歸曰:“欲保性命而已。”(《明儒學案》卷一,《 崇仁學案一》)這些推論除第二點缺乏有力證據外,其他兩點則都有一定道 理,但我以為最根本的原因還是他沒有應付官場的任何能力。在其未入朝前, 便已有了“迂”的名聲,盡管英宗說:“人言此老迂,不迂也。”卻并未改 變周圍人的看法,那些宦官們見其“操古禮屹屹,則群聚而笑之。”儼然將 其視為一件古色古香的出土文物。若僅僅是宦官的看法倒也罷了,可是連極 力推薦他的李賢也如此說:“凡為此者,所以勵風俗,使奔競干求乞哀之徒, 觀之而有愧也。”(同上)話雖講得很婉轉,意思卻并無大的變化,依然是 中看不中用的擺設而已。在此種環境中,作為持守圣學理念甚堅的儒者吳與 弼,顯然已經沒有留在朝中的任何必要,于是便只有退隱之一途可供選擇了。 在其退隱行為中,石亨、曹吉祥諸權臣所造成的險惡政治環境固然是重要原 因之一,同時也有其理想與現實之間存在巨大的差距而產生的失望情緒在起 作用,但他之缺乏現實適應能力應是最為重要的原因。因為作為一位以天下 為己任的儒者,決不應輕易放棄對現實的關注,除非到了于時事無任何補益 的程度。此種缺乏實際操作能力的情形決非只限于薛、吳二人,而是體現于 許多士人身上,成化年間憲宗失德,此時內閣大臣劉吉、萬安等三人及眾大 臣對朝政無所規正,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諺語,以譏其無能 也。(見《明史》卷一六八,《劉吉傳》)憲宗久不接見大臣,而萬安見帝 時無他語,只知頓首口呼“萬歲”而已,“一時傳笑,謂之‘萬歲閣老’。 帝自是不復召見大臣矣。”(同上《萬安傳》)此類士人在品格上自然不能 與薛、吳二人相比,但由于科舉八股的摧折與程朱理學的限制,使其人品與 能力均失之,遂造成明中期人才的荒蕪。 其次是對程朱理學的過于執著往往使許多士人流于固執與偏激。堅守程 朱理學者一般都自律甚嚴,具有高潔的人格與凜然的正氣,這些都是他們超 越常人之處。但他們對于其他人也常常要求甚嚴,有時甚至近乎苛刻。仍以 薛瑄為例,他死后被謚“文清”,說明了后人對其高潔人品的認肯,但同時 也留下了他不能善解人意甚至有些吹毛求疵的史實,黃宗羲曾在《明儒學案》 中記錄了正統四年南安知府林竿的一段話:“比者,提學薛瑄以生員有疾罷 斥者,追所給廩米。臣以為不幸有疾,罷之可也。至于廩給,糜費于累歲, 而追索于一朝,固已難矣。父兄不能保子弟之無疾,今懲償納之苦,孰肯令 其就學。”(卷七《河東學案上》)生員得病已屬不幸,停發其廩米已是不 忍,而薛老夫子竟然還要追回已往所發廩米,其行為不能不說近于刻薄。但 此類小事上的刻薄至多說明薛夫子性情有些偏執,尚不至于影響其純儒的品 格。而后來至大學士邱濬,其偏執便流于忮險了。邱濬(1420—1495)字仲 深,瓊山人,景泰五年進士,后官至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他雖未能被 列入《明史·儒林傳》與《明儒學案》,但他曾作過《大學衍義補》及《續 通鑒綱目》,還編寫過教忠教孝的南戲劇本《五倫全備記》,理應被列入理 學家之行列中。就其個人品質講,他廉潔耿介,自甘清苦,一生嗜學,至老 不衰。加之為官直言敢諫,勇于任事。應該說并沒有大的污點。但在各種史 書中已記載了他不少并不美妙的遺聞瑣事。《明史》本傳記其“性偏隘,嘗 與劉健議事不合,至投冠于地。言官建白不當意,輒面折之。與王恕不相得, 至不交一言。”此種恩怨分明的舉措尚無大過,至多算是缺乏容人之量,所 以后來李贄譏諷其為“真不脫海蠻氣習。”(《續藏書》卷十一,《太傅邱 文莊公》)而焦竑在《玉堂叢語》中,已言其“學博貌古,然心術不可知。” 并引述了劉健送他的一副對子,叫做;“貌如盧杞心尤險,情比荊公性更偏。” (卷八《刺毀》)這便牽涉到了人格品行的大問題。同時還由人品推及到為 官施政的才能上,文征明雖承認他“博學自信,以天下為己任”的長處,卻 隨之又指出其“任偏矯正”的性格缺陷,于是他贊同毛珵對邱氏的評論: “天下事非紙上陳言可舉,而古今異宜,遠近異勢,亦非一己之見可盡。如 濬之才,置之翰林則有余,不可在論思之地。”(《文征明集》卷二六,《 明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公行狀》)不過,人們盡管已經在懷疑邱 學士的“心術”是否純正,但總體上仍沒有將其歸入小人的行列。再向前發 展,偏執與追逐名利的私心相結合,更使得士人的人格問題趨于嚴重。黃綰 在其《明道篇》中曾集中論述了好名尚氣節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他認為自明 代立朝以來,逐漸養成一種尚氣節的士習,其風聲流傳,遂不可止,并由此 造成了很壞的影響,他說:“蓋立名、尚氣節者,但知名節為大,而不知圣 人之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親戚、故舊、上下交際,處處皆有 其道。后世不知有道,惟欲立己之名,成己之節,一切反之而不恤,忍心殘 薄,乃自以為賢,為得計,其弊遂至不可救。故古人以名節為道德之薄,為 學者之戒。論人者,乃以為圣賢事業在此,或取之為理學名臣,不知其流越 趨越下。故今之仕者,爭以殊詭標名,惟恐其不異;刻虐稱才,惟恐其不極; 顛倒亂真,惟恐其不奇;堅忍毀成,惟恐其不特;要其心皆陰懷巨利,陽示 不欲;內存刻薄,外施仁義。論世者尤以天下事非此才力不能為,非此風聲 不能振,豈不為世道之害,國家生民之禍載! ”真誠的偏執已經不能被視為 君子之氣象,更何況為謀一己之私而走向氣節的極端,那顯然要被歸入小人 之行列了。此種士風的要害在于其人性之偽,亦即表里不一,言行脫節。依 黃綰的見解,此種士風敗陋的原因乃在于學術之不純,故曰:“今日海內虛 耗,大小俱弊,實由學術不明,心術不正,故士風日壞,巧宦日眾,吏弊日 多,貪殘日甚。……此皆吾黨之所當知,必思有以救之可也。救之如何?明 學術而已。”(卷二)黃綰的論辯當然不是無隙可擊,誠如上節所言,在明 代這個以私有制為基本性質的封建帝國中,士人入仕的真正目的乃在于個人 利益的獲得,其他方面諸如科舉的成功、名節的崇尚、學術的討論等等都極 易流于獲利的手段。由此觀之,為名尚氣節而走向世道之害,也脫離不了追 求名利這一根本的性質,蓋因其有名節可稱,則有利于仕祿之顯達也。明代 士人顯然無法改變制度,因而從本質上講也就無法改變士風。但這并不意味 著可以將黃綰所提出的“明學術”的主張視為無足輕重,對于明代學術史而 言,認識到學術不明為士風不正的原因之一,便須辨明學術,而辨明學術的 具體內容,便是由朱學走向心學。學術固然不是轉變士風的唯一因素,但卻 是體現士風的重要標志。其實,對此問題的認識并不始于黃綰,在此引述他 的話乃在于他論述的較為具體詳細而已。早在其師王陽明那里,便已認識到 此種陰陽不一的人性之偽,故曰:“逮其后世,功利之說日浸以盛,不復知 有名德親民之實。士皆巧文博詞以飾詐,相規以偽,相軋以利,外冠裳而內 禽獸,而猶或自以為從事于圣賢之學。如是而欲挽而復之三代,嗚呼其難哉!” (《王陽明全集》卷八,《書林司訓卷》)程朱理學由熔鑄士人的儒家倫理 人格的理想學說淪落到士人獵取名利的招牌,這當然是明初極力推行程朱理 學的君臣們所始料未及的,然而的確又是不得不然的歷史發展趨勢。盡管此 種趨勢不是直線型的,其發展階段也并非如此處所描繪的那般涇渭分明,其 中有曲折、有回流、有夾雜,但就總體上講,卻是清晰可辨且不可逆轉的。 同時這也是心學產生的契機。 其三,士人對程朱理學的固守使其思想空間過于狹窄,從而形成其封閉 內向與緊張自責的心態。第一節所概括的士人清慎的心態,一方面固然是明 前期外部政治環境的產物,但同時也與士人人格的內部構成有密切的關聯, 尤其是與其程朱理學的學養有關。比如宋儒朱熹論學主敬,便對明前期士人 有深刻影響。朱子之治學名言便是“涵養需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那么“ 敬”有何內涵呢?朱子曾解釋說:“敬非是塊然兀坐,耳無所聞,目無所見, 心無所畏,而后謂之敬。只是有所畏謹,不敢放縱。如此則身心收斂,如有 所畏。常常如此,氣象自別。存得此心,乃可以為學。”(《朱子語類》卷 十二)可知敬有二大特征:一是畏謹,故又曰:“敬,只是一個‘畏’字。” (同上)二是收斂不放縱,故又反復強調:“學者須常收斂,不可恁地放蕩;” “人常須收斂個身心,使精神常在這里。”(同上)當然,敬還可以具體落 實到言行上:“坐如尸,立如齋,頭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 止,氣容肅,皆敬之目也。”(同上)總而言之,敬是對人的身心言行的一 種限制,此乃從消極意義講;同時亦為精神專一之謂,此乃從積極意義講。 限制身心之其他方面而使之專一于圣學,則是二者的統一。對此朱子亦言之 甚明:“敬,莫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自家精神,專一在此。今看來諸所 以不進,緣是但知說道格物,卻于自家根骨上煞欠缺,精神意思都恁地不專 一,所以工夫都恁地不精銳。未說道有甚底事分自家志慮,只是觀山玩水, 也煞引出了心,那得似教他常在里面好! 如世上一等閑物事,一切都絕意, 雖似不盡人情,要之,如此方好。”(同上)朱子把敬作為進學的態度與手 段,強調畏與收,顯然將士人的生存空間與精神空間大大壓縮了,非但不可 觀山玩水,還要“世上一等閑物事,一切都絕意,”盡管也察覺到頗有些“ 不盡人情”,還是稱“如此方好”。他描畫出的儼然是一副形若槁木、情趣 皆無的道學家圖像。明前期士人為學大都尊崇朱子,在人生態度上采取嚴格 的倫理主義立場,從而自我的思想空間也被壓縮到極為狹小的范圍。如明儒 胡居仁論學即強調敬與誠二字,他在主持白鹿洞書院時所續修之學規,便特 意列入“主誠敬以存其心”一條,作為朱子《白鹿洞學規》的補充,由此可 見二者之間的繼承關系。(見《胡敬齋集》卷二,《續白鹿洞學規》)胡居 仁有時甚至比宋儒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如周敦頤、程顥尚倡言尋求孔顏樂處, 講一些人生受用,而胡居仁連此一點也反對,論及“求樂”便皺眉頭,故而 反復辯難曰:“上蔡記明道語,言‘既得后,須放開。’朱子疑之,以為 ‘既得后,心胸自然開泰,若有意放開,反成病痛。’愚以為,得后放開, 雖似涉安排,然病痛尚小。今人未得前,先放開,故流于莊、佛。又有未能 克己求仁,先要求顏子之樂,所以率至狂妄。殊不知周子令二程尋孔顏之樂 處,是要見得孔顏因甚有此樂,所樂何事?便要做顏子工夫,求至乎其地。 豈有便來自己身上尋樂乎?故放開太早,求樂太早,皆流于異端。”(《明 儒學案》卷二)依胡氏之見,士人決不應輕言求樂,而須終生在“所樂何事” 上痛下工夫,否則即為儒家之異端。因而他甚至對黃庭堅贊許周敦頤的那段 名言亦表示不滿曰:“‘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雖曰形容有道氣象,終 帶了些清高意思。”(《居業錄》卷一)士人既不可求樂,連清高亦須避免, 這就把“清慎”心態中的“清”之一項也抽而去之,所留下的惟“慎”而已。 所謂“慎”,亦即時刻保持自我警覺,進行自我檢束,從而使自我始終保持 一種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狀態,其實也就是朱子所言的“敬”的狀態。要 保持此種狀態是相當艱難的,它不僅須犧牲掉自我的人生享樂,極力抑制自 我的人生欲望,收斂自我的個性,更要不斷地進行心靈的自我拷問,剔除一 切可能影響道德純潔的因素。現擇取幾位明代前期儒者,看他們內心深處的 天理與人欲之間是如何進行艱苦搏殺的。曹鼐,這位中了宣德八年狀元的士 人,無疑飽讀過儒家詩書并深諳程朱之義理,但他在做泰和典史時,“因捕 盜,獲一女子,甚美,目之心動。輒以片紙書‘曹鼐不可’四字火之,已復 書,火之。如是者數十次,終夕竟不及亂。”(《玉堂叢語》卷一,《行誼》) “不及亂”說明了他意志的堅定,并最終入閣為大學士;而數十次書寫“曹 鼐不可”,則說明了克制自我情欲的艱難。楊鼎,這位中了正統四年榜眼的 官員,在任戶部右侍郎時,曾“書‘十思’于座隅以自省,曰量思寬,犯思 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后,名思晦,位思卑,守思終,退思早。” (同上)此“十思”充分體現了克制情欲、檢束自我的“敬”與“慎”的原 則,可謂全面而具體。楊鼎是否真正做到了“十思”的要求,因無充足的材 料而難以斷定,但是要整日生活在這“十思”之中,想必需要付出極大努力 并時刻處于警覺的狀態。查一查楊鼎的生平,不免令人頗為失望。他如此地 檢束自我,卻依然在天順三年“以陪祀陵寢不謹下獄。”最終被彈劾而辭官 歸鄉。如果說曹、楊二人非純粹理學家而缺乏足夠代表性的話,也許再拿薛 瑄為例更為合適。他在明前期可謂是堅守朱子學之大師,象朱子本人一樣, 他立定志愿痛下克去己私而還復天理的工夫,以便最終達到圣人的境界。但 在這天理人欲的交戰中,他卻時時感受到變化氣質的艱難,他曾一再說:“ 嘗念顏子三月不違仁,諸子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吾自體驗此心,一日 之間,不知幾出幾入也。以是知圣賢之學極難,而亦不可不勉。”(《薛文 清公讀書錄》卷六)“氣質極難變,十分用力,猶有變不能盡者,然亦不可 以為難變而遂懈于用力也。”(同上)在此,由氣質之性而變為純乎天理可 以視為一個逐漸趨于理想境界卻又永遠無法實現的過程,并且在此過程中充 滿了“幾出幾入”的反復糾纏,則其內心充滿緊張也就不言而喻了。 程朱理學與科舉制度都是關系到明代思想學術的重大舉措,尤其對士人 人格心態具有重大的影響。它們在明前期盡管對政治的穩定、文化的建設以 及文官制度的建立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但同時也帶來了如上所述的種種負 面影響。從士人這個角度講,他們在領受了許多的挫折與煩惱之后,勢必會 自覺不自覺地提出自己的質疑并試圖突破對自我的困擾,下面要論述的陳獻 章便是在思想界異軍突起的第一人。 |
|
人民文學出版社
版權所有 北京國學時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Copyright©2000
國學網站,版權專有;引用轉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
國學網站,版權專有;引用轉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