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詩經》
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又稱為《詩》、《詩三百》、《三百篇》。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之一,始稱為《詩經》。此書共收詩三百一十一篇,其中除去有題目而無文詞的六篇(即有樂曲無歌詞的“笙詩”),還余三百零五篇。
書中作品寫作年代大約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即公元前十一世紀到前六世紀。詩作者除個別者外絕大多數不可知,其產生的地域包括今天的甘肅、陜西、山西、河南、山東、湖北等省的一些地區。
《詩經》按照樂曲的不同,分“風”、“雅”、“頌”三類。“風”分十五國風,除了周南、召南以外,還有邶、睟、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共一百六十篇。“雅”分《大雅》、《小雅》,共一百零五篇。“頌”分《周頌》、《魯頌》、《商頌》,共四十篇。
《詩經》編纂成書大約在公元前六世紀中葉,春秋時代的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曾以此書作為課本教授學生。漢代儒生深信孔子刪訂此書,言孔子曾從古代詩三千多篇中“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史記·孔子世家》)。這種說法傳播很廣,但不可信。《詩經》所反映的社會生活極為廣闊。國風大多是廣大勞動人民的民歌,表現了他們的喜怒哀樂和對社會的認識。但是這部分一被采入官府,用作貴族子弟學習教材后,其社會作用就產生了根本的變化。大小雅則多為當時士人或下級官吏的作品,其中優秀部分記錄了周民族發展歷史,表現了西周末年和東周初年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尖銳。頌多為祭祀而寫,其中少數篇章是描寫商、周民族史的,漢代詩有專學,傳詩者有齊、魯、韓(今文)、毛(古文)四家,毛詩晚出獨存,因此,后代亦稱《詩經》為“毛詩”。因《詩經》詞義深奧,歷來很少有白文本流傳,其稱為《詩經》的全集注本較著名的有:《詩經廣詁》(清徐)、《詩經通論》(清姚際恒)、《詩經原始》(清方玉潤)、《詩經直解》(今人陳子展)等。
2 《毛詩傳箋》
《詩經》注本,三十卷,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箋。亨為漢初魯國(山東省曲阜一帶)人。曾為詩作訓故傳》,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世稱大毛公。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山東省高密縣)人,少曾為鄉吏,后入太學學習,通今古文經學,并師事馬融,鮂讀儒家經典,成為經學史上著名的經學大師。
毛氏對詩篇大義和文字名物作了簡略的訓釋,釋意在前,稱之為“序”,注解文字在每句之后,稱之為“傳”。毛氏所傳之詩用戰國時篆文書寫,因而稱之為“古文經”。毛傳與齊、魯、韓三家今文“詩經(今文,指用漢代流行的隸書書寫)學”不同,很少有虛妄迷信的內容,摒棄了漢代盛行的讖緯神學,堅守孔子“不語怪力亂神”的著述原則和“溫柔敦厚”的詩教,注重詩的教化作用。
毛傳在探討詩經的藝術表現時“獨標興體”指出書中用“興”的表現手法有一百一十六處。鄭玄對毛傳中闕疑、不明和錯誤之處作了補充和訂正。他說:“注《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則下己意,使可識別也。”(見《毛詩正義》“鄭氏箋”下引語)鄭氏吸取了齊、魯、韓三家的一些意見,做到了今古文經學的融會貫通。并能按照他對詩意的理解將詩三百零五篇依年次加以排列,以史證詩。當時經書尚沒有通用的傳本,師生之間口耳相傳,因而特別注重“家法”(指嚴守師說)。毛傳鄭箋保存了漢代乃至先秦時代人們對《詩經》的理解和解釋,但他們也從經學角度對《詩經》作了許多歪曲。
此書為封建時代士人必讀書,刻本甚多。較好的有清嘉慶枕經樓刻本。此本以惠棟校本為底本,并參校諸本,芟除蕪雜,正其舛謬,并附有《詩譜表》。
3 《詩譜》
二卷,東漢鄭玄撰,玄有《毛詩傳箋》已著錄。此書亦名《詩譜·序》,鄭氏依據《春秋》次第和《史記》年表,列舉各詩先后世次,闡述各詩之世代及做詩之緣由,借以說明《詩經》與歷史時代和社會風土之關系,雖然也有可取之處,終以穿鑿附會為多。
作者認為“此(指詩譜)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于力則鮮,于思則寡”(見《詩譜·序》)。其目的是為學者提供方便,通過文字講解和列表說明,舉一反三,便于對《詩經》總體和各篇主旨的把握。但鄭氏完全繼承了《詩序》的“風雅正變”和“美刺”說,并作了進一步的發揮。他提出:上起陶唐,及至文武成周之世,都是太平盛世,制禮作樂、頌聲興起。這時期的作品都是正“風”正“雅”,能起“美教化”的作用,是詩之正“經”;周朝懿王、厲王之后,王室衰微,政教崩壞,所以怨刺載道,這以后的詩都是變“風”、變“雅”,只能以其怨刺作為鑒戒。對《詩經》世次的排列是鄭氏解詩的依據,并把各詩的解釋納入,這種意見的宗旨是把對《詩經》的闡釋納入為政治服務的軌道。
唐初孔穎達等人奉詔作《毛詩正義》,割裂《詩譜》分置于“風”“雅”“頌”之前,原書遂至北宋而軼。清丁晏重加補綴,著《詩譜考證》,胡元儀別總譜,稱《毛詩譜》。
有清光緒間南菁書院刊刻《皇清經解續編》本。
4 《毛詩正義》
《詩經》注本,四十卷,唐孔穎達撰。穎達(574~648)字沖遠,一作仲達,冀州衡水人,隋末舉明經,入唐累官國子司業,遷祭酒。嘗受唐太宗命撰《五經正義》,卒謚“憲”。
此書是奉旨修訂的官書,是孔氏組織當時經學家王德韶、齊威、趙乾葉、賈普曜共同完成的。它的文字用當時學者顏師古考訂的正本,把《詩經》文字完全固定下來。在注釋方面用毛傳鄭箋,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加以疏解,對漢魏到唐初四個世紀的詩經學研究成果盡量加以吸收總結,述義翔實,疏解亦明,代表了當時詩學最高水平。其文字的音切義訓則采取陸元朗(德明)《經典釋文》中《毛詩釋文》,簡明準確,至今仍為我們采用。此書是從經學角度解詩,忽略了詩經的文學特點。書中疏文堅守“疏不破注”的原則,曲徇注文,不免有生硬、穿鑿附會之處。
此書實際是以隋代著名經學家劉焯、劉炫《詩經》注疏為基礎加以整理增刪而成的。后被收入《五經正義》《十三經注疏》,長期作為官方尊奉的定本而成為封建社會士人必讀書,影響很大。
有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本行世。
5 《毛詩本義》
《詩經》注本,十六卷,北宋歐陽修撰。修(1007~1072)字永叔,號醉翁、六一居士,吉水(江西省吉水縣)人。北宋時著名文學家,天圣間進士,曾任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謚文忠。
此書凡為說一百十四篇,統解十篇,《明世》《本末》二論。《幽》《魯》《序》三問。全書不錄詩,每說分“論曰”、“本文”兩部分。書中對漢代《詩經》學的基礎———《詩序》《毛傳》《鄭箋》都有所指摘,這些貫穿于諸說之中。其中的“論曰”偏重揭示序、傳、箋的矛盾和舛謬,并提出自己的意見和看法;“本義”則偏重于闡釋詩義,往往拋開《詩序》說詩,從整體上動搖了漢唐以來大小毛氏、鄭玄等人《詩經》學的權威地位。歐陽修是詩人,他往往能依詩立意,做出符合原詩本義的解釋。如解釋《衛風·氓》,認為此詩為“女子色衰而為其男子所棄,因而自悔之辭”,“一篇始終是女子責男之語”,并說“不知鄭氏何從知為賢者之辭,蓋臆說也”。這就比鄭玄和《詩序》所說《氓》之旨在于諷刺衛國風氣淫靡和贊美棄婦能返于正道更符合原詩實際一些。
此書對后世多有啟迪。其后蘇轍著《詩集傳》言《詩序》不可盡信,鄭樵《詩辯妄》專攻詩序和《毛傳》《鄭箋》,朱熹撰《詩集傳》脫離漢學,皆由此書開其端,并形成了宋代《詩經》學。
有清康熙時刊《通志堂經解》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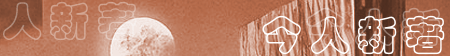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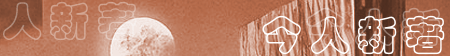
![]() web@guoxue.com
web@guoxue.com ![]() 010-68900123
010-6890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