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石倉歷代詩選》(石倉十二代詩選)
上古至明詩選本,五百零六卷,明曹學?編選。?福建閩侯人。萬歷進士,任四川右參政、按察使,后因著《野史紀略》觸怒權宦,被劾,削職為民,家居二十余年。清人入關,學?參加抗清斗爭,殉節而死。
此書為明代詩選中最宏偉之作,上自上古,下至明代嘉靖、隆慶,包括古詩十三卷,唐詩一百卷,拾遺十卷,宋詩一百零七卷,全元詩五十卷,明初集八十六卷,次集一百四十卷,詳于當代而略于古代。
此書意在存明人詩,故明以前詩擇之不精,考訂不確,錯誤很多,即以選詩來說,既濫且缺,許多名篇未能入選(如李商隱《無題》和詠史佳作入選很少),一些劣品卻充斥書中(唐胡曾《詠史》詩竟選了四五十首),有些著名的組詩竟被拆散(杜甫《前出塞》九首只選七首,刪去了“挽弓當挽強”和最末一首)使其失去了完整性。一些思想性較強的篇章也被遺漏,如杜甫的《石壕吏》《新安吏》《無家別》,白居易的《秦中吟》《新樂府》都未入選。另外如一詩分屬兩人,作品歸屬錯誤則不可勝數。《四庫全書》所收明詩僅至“次集”而止,實際上,明次集之后還有三集百卷,四集百三十二卷,五集五十二卷,六集百卷,共三百八十四卷。另外還有明續集五十一卷,再續集三十四卷,《閨秀集》一卷,《南直集》三十五卷,《浙江集》五十卷,《福建集》九十六卷,《社集》二十八卷,《楚集》十九卷,《四川集》五卷,《江右集》五卷,《江西集》五卷,《陜西集》三卷,《河南集》一卷。又有三續集十三卷,四續集九卷,續五集四卷,五續集六卷,六續集二卷。共三百六十七卷,由此可見曹氏欲藉此以存明朝一代文獻。
① 六義指風、雅、頌、賦、比、興。這里朱氏強調了它們的音樂意義。因為風、雅、頌之分是由于音樂不同。
據今人鄭振鐸《劫中讀書記》言,三集及以后諸集非如《嘯亭雜錄》所說,均為抄本,實際都有崇禎間刻本,清陶蘭泉有足本,后陶氏書售予日本東方文化研究學院。鄭氏所藏為殘本,共六百六十卷。常見者為五百零六卷本,另有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本。
52 《樂府廣序》
漢魏樂府古詩選集,三十卷,明末朱嘉徵編纂。嘉徵字岷左,別號止?圃人。海寧(浙江海寧縣)人,崇禎壬午(1642)舉人,至清曾為徽州府推官。
朱氏論詩強調詩與音樂是一個整體,認為孔子刪詩的目的在于“定六詩之序而樂以正”。并認為“六義①存而詩存,六義亡而詩亡”。因此編者在此書中將漢魏樂府古詩按照“風雅頌”次序排列,以“相和曲辭”中的“相和曲”(八首)“吟嘆曲”(一首)“平調曲”(四道)“清調曲”(四首)“瑟調曲”(十五首)“夢調曲”(四首)“大曲”(一首)“雜曲”(三十一首)為漢風,以“相和歌辭”中的“平調曲”“清調曲”“瑟調曲”“楚調曲”“雜曲”為魏風,以“鼓吹曲辭”“橫吹曲辭”“雜舞歌辭”為漢魏之雅與變雅。以“郊廟歌辭”為漢魏之頌。二十五卷至三十卷為歌詩與琴曲,并在每詩或每組詩后撰一“序”點明詩之主題,標明美刺,目的在于“本原于忠臣孝子之心,發明于保定扶危之旨”。雖然編者分類及其“序”多牽強附會、迂腐冬烘之處,但在明末清初民族矛盾十分尖銳的時刻朱氏編纂此書是有寄托的,所以黃宗羲為之作序。書中廣泛搜羅歷代學者對所錄詩的解釋,批評的文字,可資參考。編者對一些詩篇的思想與藝術的分析也有可取之處。
朱氏另有《漢魏詩集廣序》,其分類與《樂府廣序》同,二書均有清遠堂刊本。
53 《采菽堂古詩選》
古詩選本,三十八卷,補遺四卷,清陳祚明編選。祚明字允倩,號稽留山人,錢塘(浙江省杭州市)人。生活于明末清初,明侍御史元倩之弟。元倩殉明朝之難后,他隱居不仕,后因貧傭書京師,病死于京師客邸,著有《稽留山人集》。
這本古詩選“選無專旨,有美必錄”,無派別門戶之見,這在明末清初很少有。陳氏論詩注重“情”、“辭”,他說“體格不同而同于情”,“辭不同而同于雅”,凡情深而辭雅正者皆能入選。因之選錄面很寬,自《卿云》以下至隋代選詩達數千首。他特別重視詩的感染性,他說:“吾言吾之悲,使聞者愀乎其亦悲;吾言吾之喜,使聞者鬯乎如將同吾之喜。”在注釋、分析入選詩篇時注意提示詩人情感的底蘊。對于情旨深隱的詩章,編者必“索之希微”,深入挖掘它的含義。在注釋、分析作品時多取材眾說,加以折衷。不逞私臆,不眩博矜奇,也不務為穿鑿,故作高論。這是一部比較平實可讀的選本。
此書分代編排,每代之前都是首列樂府,然后按世次編排諸家作品。對于異文殊文則擇善而從,兩者均善則并存。入選作者時代及其爵里依馮惟訥之《古詩紀》。
此書最早刊本為康熙丙戌(1706)年刊本,常見者有乾隆傳萬堂刊本。
54 《古詩評選》
古詩選評本,六卷,清王夫之選評。夫之有《楚辭通釋》已著錄。
王氏雖也用此書授徒,書中介紹了古詩中的名篇佳作,但主要還是藉此宣揚他的詩學觀點。選者因推崇古詩,遂愛及齊梁,對于入選的作品贊揚較多。如評《白頭吟》說“亦雅亦宕,樂府絕唱”,評《悲歌》說“突兀壯而無霸氣”。評《戰城南》說“所詠雖悲壯而聲情繚 繞,自不如吳均一派裝長髯大面腔也”。關于《古詩十九首》他說:“《十九首》情該一切,群怨俱宜,詩教良然,不以言著。”并贊美說《十九首》“驚心動魄”“深練華贍”“好色不淫,怨悱不傷”。對于六朝王氏說“安得起六代入于地人一拯唐人之衰也”。由此可見編選者把漢魏六朝看成詩歌創作的高峰,到唐代則已是詩歌創作之衰世。他偏愛婉約含蓄,辭氣嫻雅,優游不迫,無劍拔弩張之氣的作品。在評庾信詩時,對杜甫盛贊的庾信“凌云健筆”則大加撻伐:“健筆者,酷吏以之成爰書而殺人,藝苑有健訟之言,不足為人心憂乎?”他還注重詩歌的神韻風采,反對鋪述刻畫,強調“詩”與“史”的區別。他諷刺“詩史”說“以詩史譽杜”乃是“見駝則恨馬背之不腫也”。他認為詩之敘事較史尤難,“史才固以隱括生色,而從實著筆自易”,詩則“即事生情,即語繪狀,一用史法,則相感不在永言和聲之中,詩道廢矣。此《上山采蘼蕪》一詩所以妙奪天工也。杜子美放(仿)之作《石壕吏》,亦將酷肖,而每于刻畫處猶以逼寫見真,終覺于史有余,于詩不足”。他對杜甫的批評未必正確,但對詩與史敘事方法區別的探討是有益的。基于這些看法,古詩名篇《孔雀東南飛》都未入選,原因就是“潦倒拖沓”“自是古人里巷所唱盲詞白話”。對于古詩領域中一些有定論的問題和有定論的詩人,王氏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如說“建安風骨”“如鱔蛇穿堤,堰傾水長流,不涸不止而已”。對于曹植則極盡攻擊之能事,認為他的詩是“以腐重之筆,寫鄙穢之情,風雅至此掃地盡矣”。對庾信也是貶多于褒。這些都有失公允。
全書共選詩八百余首。卷一為樂府歌行,卷二為四言詩,卷三為小詩,多為五言絕句,卷四、卷五為五言古詩,卷六為新體詩。
有民國初湖南長沙劉人熙刻本,收入太平洋書局民國間排印《船山叢書》。
55 《古詩選箋》(古詩箋)
五言、七言古詩流派選本,三十二卷,清王士?選,聞人絯注。士?見《十種唐詩選》。人絯,字訥甫,松江(上海市松江縣)人。生活于乾隆(1736~1795)時代,是位不得志、困伏鄉里的文人。
王氏論詩標榜神韻,以沖和淡遠的意境為詩的最高境界,這個詩歌選本不僅貫徹了編選者的論詩主張,也想通過此書向讀者展現五言、七言詩的發展演變階段。對于五言詩,編者認為《古詩十九首》已發展到頂點,因而漢五言詩幾乎全部入選,魏晉以下則從嚴,唐代只取陳子昂、張九齡詩作,以體現五言詩“升降之變”,由此可見為選者所重視的還是興寄深遠、意境恬淡的詩篇。至于極古之變、內容豐富、風格多樣、善于鋪敘的杜甫,卻一首未選,不能不說這正反映了“神韻”說的局限。七言則以杜甫為正宗,“七言大篇,尤為前所未有,后所莫及,蓋天地元氣之奧,至杜而始發之”。并將杜詩立為“千古標準”,凡學杜者取之,但所取杜詩亦多為描寫生活瑣事的作品。七言部分選錄宋、元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晁沖之、晁補之、陸游、元好問、虞集、吳萊等人的作品,聞箋偏重介紹詩本事、用典,對于難懂的句子也作了必要的疏解,簡明平實,便于初學。
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排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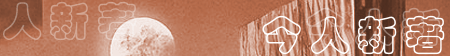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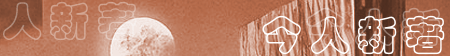
![]() web@guoxue.com
web@guoxue.com ![]() 010-68900123
010-6890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