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敦煌藏經(jīng)洞出土文書(shū)為主要研究對(duì)象的“敦煌學(xué)”,是二十世
紀(jì)世界學(xué)林中的一門顯學(xué)。雖然在其發(fā)展過(guò)程中受到材料分散、內(nèi)容
龐雜、語(yǔ)言多異等種種困難的影響,但敦煌學(xué)的研究仍成果輝煌。同
時(shí),它還為宗教、文學(xué)、語(yǔ)言、藝術(shù)、考古、科技等其它學(xué)科做出了
重要貢獻(xiàn)。
雖然敦煌文獻(xiàn)早在1900年就被發(fā)現(xiàn),但其真正為學(xué)界所知,是從
1909年伯希和將其得敦煌四部古籍精品帶到北京并展示給中國(guó)學(xué)者之
時(shí)開(kāi)始的。以后,由于羅振玉、蔣斧、王仁俊、劉師培、伯希和、內(nèi)
藤虎次郎等人的宣說(shuō)和研究成果的刊布,敦煌文獻(xiàn)的價(jià)值大顯于世,
而京師大學(xué)堂的碩學(xué)鴻儒們從伯希和處抄錄的敦煌文獻(xiàn)及所做的跋語(yǔ)、
札記,則構(gòu)成了中國(guó)敦煌學(xué)的初期篇章。如果說(shuō)京師大學(xué)堂的學(xué)者們
開(kāi)創(chuàng)了中國(guó)的敦煌學(xué),當(dāng)不為過(guò)。而其中貢獻(xiàn)最大的人,當(dāng)數(shù)羅振玉。
1910年秋,經(jīng)羅振玉等人的多方努力,藏經(jīng)洞劫后剩余的近萬(wàn)號(hào)寫(xiě)本
調(diào)運(yùn)到北京,歸京師圖書(shū)館收藏,此即現(xiàn)存國(guó)家圖書(shū)館的敦煌經(jīng)卷的
來(lái)歷。這批寫(xiě)本后被學(xué)部官僚李盛鐸、劉廷琛等人盜取,精華進(jìn)一步
被掠,但國(guó)家圖書(shū)館仍不失為世界上敦煌文獻(xiàn)四大收藏地之一。
中國(guó)早期的敦煌學(xué)研究,由于資料主要得自伯希和的照片,重點(diǎn)
在于傳統(tǒng)的四部古籍的研究,其中既有清儒所未見(jiàn)的六朝唐人經(jīng)籍寫(xiě)
本,也有一些后世已佚的經(jīng)疏、史籍、佛典、道書(shū)等等,為二十世紀(jì)
的學(xué)術(shù)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二、三十年代,中國(guó)學(xué)者前后相繼,或遠(yuǎn)渡重洋調(diào)查抄錄敦煌文
獻(xiàn);或萬(wàn)里西征考察敦煌石窟。這是二十世紀(jì)中國(guó)學(xué)術(shù)發(fā)展中一個(gè)輝
煌燦爛的時(shí)代。各種新思潮、新學(xué)問(wèn)、新方法都充分展現(xiàn)出來(lái)。在此
期間,北大的劉半農(nóng)、蔡元培、董康、胡適等學(xué)者都為敦煌研究做出
了貢獻(xiàn)。其中,劉半農(nóng)在巴黎國(guó)立圖書(shū)館抄出了104種敦煌文獻(xiàn),歸國(guó)
后輯印為《敦煌掇瑣》三冊(cè)。這一抄本在很長(zhǎng)時(shí)間里成為中國(guó)敦煌研
究的史源,并在某種程度上左右了中國(guó)敦煌學(xué)的研究選題。此外,胡
適在英法查閱敦煌寫(xiě)卷后編成的《荷澤大師神會(huì)遺集》,也成為中國(guó)
禪宗史研究的劃時(shí)代著作。
除北大學(xué)者外,清華的王國(guó)維和陳寅恪也是二、三十年代敦煌學(xué)
研究的重要人物。特別是王國(guó)維提出的“二重證據(jù)法”,成為了后人
研究歷史,特別是研究出土文獻(xiàn)的重要法寶。王國(guó)維的研究涉獵廣泛,
方法新鮮,超越了清朝學(xué)者的研究高度,不僅被國(guó)人奉為經(jīng)典,同時(shí)
也受到伯希和等海外中亞學(xué)者的重視。
在二、三十年代的敦煌研究中,分別成立于1921年底和1922年初
的敦煌經(jīng)籍輯存會(huì)和北大研究所國(guó)學(xué)門,最值得關(guān)注,他們?yōu)槎鼗脱?BR>究做出了卓著的貢獻(xiàn)。王國(guó)維《韋莊的秦婦吟》、陳垣《摩尼教入中
國(guó)考》、王維誠(chéng)《老子化胡說(shuō)考證》、向達(dá)《唐代俗講考》等,都是
此階段成果的重要標(biāo)志。而陳垣編《敦煌劫余錄》(1931),著錄京
師圖書(shū)館所藏敦煌寫(xiě)本8679件,分類編排,體制極佳,成為第一部大
型的敦煌寫(xiě)本分類目錄。
1925年,美國(guó)哈佛大學(xué)教授華爾納率隊(duì)到敦煌考察,中國(guó)學(xué)者陳
萬(wàn)里隨行。他成為中國(guó)第一位科學(xué)考察敦煌千佛洞的學(xué)者。撰寫(xiě)了
《西行日記》、《敦煌千佛洞三日間所得之印象》、《萬(wàn)里校碑錄》
等,對(duì)敦煌莫高窟題記和碑銘作了研究。1927年4月,中國(guó)和瑞典聯(lián)合
組成“西北科學(xué)考查團(tuán)”。中方學(xué)者袁復(fù)禮、黃文弼、丁道衡等參加
了該考察團(tuán)。黃氏《高昌磚集》、《吐魯番考古記》等,均為敦煌學(xué)
必備的參考書(shū)。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圖書(shū)館(現(xiàn)國(guó)家圖書(shū)館),這不僅是敦煌寫(xiě)本
的收藏單位,同時(shí)也是重要的研究機(jī)構(gòu)。1934年,北平圖書(shū)館派向達(dá)、
王重民兩位學(xué)者前往英法調(diào)查研究敦煌文獻(xiàn)。他們不僅分別編著了
《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jīng)眼目錄》、《敦煌寫(xiě)本書(shū)目》和《巴黎敦煌殘
卷敘錄》等書(shū),同時(shí)還拍攝了數(shù)萬(wàn)張寫(xiě)本照片,成為此后中國(guó)學(xué)者研
究敦煌文獻(xiàn)的主要依據(jù)。向、王兩先生的英法之行,一方面為中國(guó)的
敦煌學(xué)準(zhǔn)備了素材,另一方面,向、王兩位先生也由此成為中國(guó)敦煌
學(xué)研究的領(lǐng)軍人物。合中外學(xué)人綜合來(lái)看,王重民先生無(wú)疑成就最大。
他編纂或參與編纂的《敦煌遺書(shū)總目索引》、《敦煌古籍?dāng)洝罚?BR>到今天仍為學(xué)界所利用。
四十年代,中國(guó)敦煌研究也有長(zhǎng)足發(fā)展。1942年春,重慶中央研
究院組織“西北史地考察團(tuán)”;1944年,中央研究院與北大合組“西
北科學(xué)考察團(tuán)”,均收獲頗豐。向達(dá)兩次代表北大出行,其規(guī)模和成
果遠(yuǎn)遠(yuǎn)超過(guò)1925年陳萬(wàn)里的西行。他不僅為北大文科研究開(kāi)出了新路,
而且使中國(guó)的敦煌學(xué)研究走上了真正的歷史文獻(xiàn)和考古資料相結(jié)合的
正路。1944年2月,“敦煌藝術(shù)研究所”正式成立,敦煌千佛洞收歸國(guó)
有,常書(shū)鴻任所長(zhǎng),開(kāi)始臨摹壁畫(huà),調(diào)查洞窟。史巖受研究所之托,
調(diào)查抄錄供養(yǎng)人題記,編成《敦煌石室畫(huà)像題識(shí)》。
1948年12月,北大五十周年校慶之際,舉辦敦煌考古工作展覽,
同時(shí)印行《展覽概要》,由向達(dá)、王重民編寫(xiě)。該書(shū)對(duì)海內(nèi)外敦煌學(xué)
學(xué)術(shù)史做了完整全面的回顧,實(shí)為此前敦煌學(xué)研究的一份極佳總結(jié)。
從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國(guó)的敦煌研究,從單純的依據(jù)書(shū)本研
究,發(fā)展到實(shí)地考查;從依賴于海外郵寄的照片,到親身前往英法等
國(guó)抄錄攝影研究;從注意中國(guó)傳統(tǒng)的四部古籍,到關(guān)心民間文學(xué)、社
會(huì)情勢(shì)等諸多方面,這是中國(guó)敦煌學(xué)研究的第一高漲時(shí)期。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敦煌文獻(xiàn)研究同樣取得了重大進(jìn)步。國(guó)
內(nèi)出版了王重民《敦煌曲子詞集》、《敦煌古籍?dāng)洝罚味薄抖?BR>煌曲初探》、《敦煌曲校錄》,周紹良《敦煌變文匯錄》,姜亮夫
《瀛涯敦煌韻輯》,王重民、向達(dá)等《敦煌變文集》,蔣禮鴻《敦煌
變文字義通釋》等一系列整理研究敦煌文獻(xiàn)的重要成果。
五十年代末,斯坦因所獲敦煌寫(xiě)本S.1-6981號(hào)縮微膠卷的公布,
預(yù)示了對(duì)包括歷史資料在內(nèi)的敦煌文獻(xiàn)進(jìn)行綜合研究的美好前景。
1961年中華書(shū)局出版的《敦煌資料》第一輯和1962年商務(wù)印書(shū)館出版
的《敦煌遺書(shū)總目索引》所收劉銘恕編《斯坦因劫經(jīng)錄》,就是倫敦
藏卷公布后的整理結(jié)果。遺憾的是,此后不久的“文化大革命”使中
國(guó)的敦煌研究全面停止。而日本、歐洲和港臺(tái)地區(qū)卻在這十多年中取
得了相當(dāng)大的進(jìn)步。
七十年代末,“文革”結(jié)束,敦煌研究重獲新生。與此同時(shí),包
含世俗文獻(xiàn)最為豐富的巴黎國(guó)立圖書(shū)館藏卷全部公開(kāi)。在全國(guó)主要學(xué)
術(shù)研究中心,人們可以看到英圖、法圖、北圖三大敦煌寫(xiě)本收集品的
縮微膠卷。1981年后陸續(xù)出版的《敦煌寶藏》140冊(cè),將膠卷變成書(shū)本,
更加方便了研究者。資料的大量公布,是促使這十余年來(lái)敦煌研究進(jìn)
步的直接原因。
由于大量原始文獻(xiàn)的公布,進(jìn)行敦煌文獻(xiàn)的分類整理成為可能。
于是,一批分類輯校敦煌文獻(xiàn)的專集紛紛出現(xiàn)。其中唐耕耦等編《敦
煌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文獻(xiàn)真跡釋錄》1-5輯是迄今敦煌研究中收錄歷史資料最
全的一部錄文集。此外,在研究方面,幾乎每個(gè)課題都有學(xué)者在從事
研究。這些研究大都散見(jiàn)于國(guó)內(nèi)各種專業(yè)刊物和論文集、紀(jì)念文集中。
而從八十年代以來(lái)多次舉辦的國(guó)際性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也為敦煌研究的發(fā)展
起到了推進(jìn)的作用。
可喜的是,近年來(lái)出版界對(duì)敦煌文獻(xiàn)的出版傾注了極大熱情。一
系列大型圖錄先后出版,此舉極大地改變了過(guò)去閱讀資料的局限。特
別是九十年代以來(lái),敦煌文獻(xiàn)四大藏家的最后一家──俄藏敦煌文獻(xiàn)
開(kāi)始全面公布,這些首次刊布的新材料必將推動(dòng)敦煌學(xué)許多領(lǐng)域的具
體研究,并為21世紀(jì)敦煌學(xué)研究提供更為廣闊的天地。
然而,從整個(gè)學(xué)術(shù)史的發(fā)展來(lái)看,在中國(guó)敦煌學(xué)的熱鬧背后,也
存在著不少問(wèn)題。比如目前在深入研究具體問(wèn)題的同時(shí),忽視了基本
工具書(shū)的編纂,也缺乏超出個(gè)案研究的宏篇巨制。此外,目前的研究
中有一種就敦煌而說(shuō)敦煌的傾向,這很容易令敦煌學(xué)的路子越走越窄。
在我看來(lái),我們切不可孤立敦煌學(xué),而應(yīng)利用各個(gè)不同學(xué)科的方法來(lái)
研究敦煌吐魯番材料,用開(kāi)放的眼光來(lái)看待敦煌的問(wèn)題,這樣才能在
自己所研治的對(duì)象之外獲得更多知識(shí)。
在新時(shí)代里,敦煌學(xué)還能否成為世界學(xué)術(shù)的新潮流,這是一個(gè)值
得深思的問(wèn)題。毋庸置疑,敦煌寫(xiě)本的編目、整理、校錄、考釋和敦
煌學(xué)的個(gè)案研究,仍將在21世紀(jì)持續(xù)下去,而且會(huì)做得越來(lái)越精細(xì)。
但從敦煌學(xué)的資料來(lái)看,還有不少可貴之處沒(méi)有得到充分發(fā)掘,從大
文化的角度來(lái)審視,還有不少課題可以開(kāi)拓。首先,中古時(shí)代的宗教
史,包括佛教、道教以及從西亞、中亞傳入的祆教、摩尼教等等,需
要更全面地深入研究。第二,敦煌莫高窟為我們提供了最集中最豐富
的唐朝社會(huì)和文化的全貌。如此豐富多彩的立體畫(huà)面,在敦煌之外很
難集中找到。我們應(yīng)充分利用這一資源,全面研究唐代各階層的社會(huì)
和文化。第三,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歷史變遷,十分有利于我們對(duì)
吐蕃王朝和漢藏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隨著古藏文文書(shū)翻譯發(fā)表,這方
面的歷史研究也將得到推動(dòng)。第四,敦煌及周邊地區(qū)出土的大量各民
族語(yǔ)言的材料,包含有大批文書(shū)檔案,真實(shí)地記錄了這些民族的歷史。
這有助于我們利用其本民族的史料研究其本民族史。但由于這些文書(shū)
解讀上的困難,真正的歷史研究恐怕要等到21世紀(jì)才能充分開(kāi)展起來(lái)。
在敦煌文獻(xiàn)方面,我們一方面應(yīng)著手進(jìn)行對(duì)敦煌文獻(xiàn)的總體研究,
用中古佛寺文獻(xiàn)構(gòu)成的方式來(lái)復(fù)原敦煌文獻(xiàn)的原貌。其次,在敦煌文
獻(xiàn)全面公布的以后,我們應(yīng)在過(guò)去分類整理敦煌文獻(xiàn)的工作基礎(chǔ)上,
再提高一個(gè)層次。把敦煌文獻(xiàn),特別是其中的四部書(shū)寫(xiě)本,按比較合
理的分類體系來(lái)編排,校錄出“定本”,并使之電子化,把敦煌文獻(xiàn)
的研究成果貢獻(xiàn)給各個(gè)學(xué)科的研究者。再次,我們應(yīng)注重將同時(shí)代的
出土文獻(xiàn)與敦煌文獻(xiàn)左右互補(bǔ),為敦煌文獻(xiàn)研究不斷注入新的活力。
最后,要有系統(tǒng)地吸取外國(guó)學(xué)者的高水平研究成果,熔鑄到新的整理
和研究中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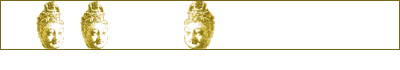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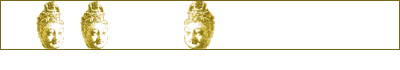
![]()
![]() web@guoxue.com
web@guo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