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清在《傳統:由“知識資源”到“學術資源”》(《中國社會
科學》2000年第4期)一文中說,構成傳統最重要的是它所擁有的一些
經典,并具體反映在讀書人的知識來源上。基于此,或許可以換一個
角度思考20世紀中國傳統的失落,以及失落的究竟是什么?透過《新
青年》文本可知,五四一代關于傳統的立場,主要體現在不把傳統作
為政治制度合法性的知識資源,傳統也因此呈現由“知識資源”向
“學術資源”的過渡。自五四迄于今,文化傳統由各種“經典”向抽
象化的象征符號過渡意味著對傳統文化的認知受到知識分子文化素養
以及歷史境況的影響,從中可見中國知識分子無論是批判傳統還是弘
揚傳統,都不斷在重新界定傳統,并用新的象征符號表達。同時,
“經典”的“學術資源”化也表明,傳統作為“知識資源”的失落構
成20世紀中國文化命運的實質寫照。
盛邦和在《傅斯年:批評主義史料學派的文化建設論》(《河北
學刊》2000年第3期)一文中說,評論中國現代文化建設史諸學派,傳
統的觀點是兩大學派:文化激進主義學派與文化保守主義學派。這樣
劃分欠科學,劃分為文化守護學派、文化批評(破壞)學派及文化建
設學派較為適宜。胡適群類是中國文化批評學派最有力與最有影響的
積聚。他們從“破壞”入手,以期中國文化的徹底重構。他們的實證
疑古的方法論即為此目的服務,并將此種方法運用于史學。傅斯年屬
胡適文學“猛將”之一,他主張中國文化“脫棄舊型入于新軌”,于
“破壞”前提下重作新制;他對中國“性”、“命”說作全新詮釋,
倡言“史學便是史料學”,認真實踐,做出成績,在中國文化建設史
上留下鮮明印記。
張錫坤、徐正考在《氣韻源于“氣運”》(《吉林大學學報》
2000年第3期)一文中說,把氣韻等同于“傳神”的詮釋,存在著三大
誤區:以“風韻”解氣韻之“韻”;以“文氣”解氣韻之“氣”;以
為氣韻的哲學基礎在于玄,無視“無”與“氣”的完全不調和。氣韻
源于“氣運”,二者的通假既有音韻學的依據,又有文獻可證。氣韻
即氣運,乃氣運從哲學到文藝審美中的延伸,是《易傳》所崇尚的生
命運動的美學精神的抽取縮和。劉勰的“自然之道”,鐘嶸的“氣之
動物”,與氣韻有著共同的旨趣,是分別從文學、詩歌和繪畫領域對
文藝本體論的表達。
張作耀在《曹操集權而未篡漢自立辨析》(《東岳論叢》2000年
第3期)一文中說,東漢末年,身逢亂世的曹操以其杰出的政治軍事才
能,逐步鏟除群雄,控制東漢王朝;進而廢三公,恢復丞相制度,把
持朝政。曹操集權而不篡的原因是:他認為輕易廢立,為天下大不祥
之事;世受漢恩,使他不敢輕言廢立;他以扶漢而不篡漢倡言天下,
自食其言,多有不便;控制漢室,可以“挾天子以令諸候”,使自己
凌駕于劉備、孫權之上而無降低自己地位之虞,同時也否定了劉備、
孫權割據政權的合法性。當然,如果條件成熟,曹操還是會篡漢自立
的,只不過天不假年而已。
杜勤在《論鼎三足的喻象意義》(《華東師大學報》2000年第3期)
一文中說,殷代開始鼎以銅制取代陶制,由日常炊具變為禮器。從此,
鼎之為器,含物象之法,其用途較之發明當初發生了質的變化。與鑄
于鼎面的動物圖案的神秘巫術意義同樣,鼎三足也被賦予了重要的喻
象意義。進入西周后神運萬物的原始宗教趨于理性化、世俗化,陰陽
學說從自然的客觀變化中考察大地萬物之運行規律,建立起一套類通
天地的人間秩序,滋生出天地人三位一體的宇宙思想,從而為鼎三足
為“三公”的喻象意義提供了重要的基礎。
程美寶在《陳寅恪與牛津大學》(《歷史研究》2000年第3期)一
文中說,陳寅恪曾被牛津大學聘為漢學教授,卻終未到任。中國中英
文化協會和英國利用庚子賠款建立的大學中國委員會在聘任過程中扮
演了重要的角色。陳寅恪赴英受阻是由于戰爭令交通中斷的說法并不
準確;令陳滯留香港的很可能是當時一些中國外交官摻雜了政治和外
交因素的做法。英國漢學家修中誠與陳寅恪商定在牛津大學開展中國
歷史研究的計劃和有關信件,展示了陳寅恪的學術抱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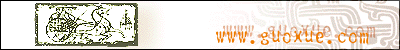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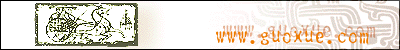
![]()
![]() web@guoxue.com
web@guo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