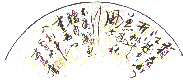一
我們時(shí)常會(huì)在學(xué)術(shù)史的敘述中論定某位學(xué)者、某部著作、某種思潮是“但開(kāi)風(fēng)氣不為師”的。當(dāng)我讀罷由錢理群、袁本良兩位先生編撰的《二十世紀(jì)詩(shī)詞注評(píng)》(以下簡(jiǎn)稱《注評(píng)》)時(shí),由衷地感到,其實(shí)“但開(kāi)風(fēng)氣即足矣”。
建構(gòu)新的學(xué)科,開(kāi)拓新的研究領(lǐng)域,往往是由自發(fā)到自覺(jué)的生成過(guò)程。在此過(guò)程中,“師”的刺激,固然能夠起到某種程度的催化作用(譬如,王國(guó)維之于中國(guó)新史學(xué),趙元任之于中國(guó)現(xiàn)代語(yǔ)言學(xué),等等),但終究無(wú)法取代學(xué)科或者研究領(lǐng)域自身的演進(jìn)與成熟(譬如,在學(xué)科建構(gòu)的進(jìn)程中熔鑄學(xué)風(fēng)的培養(yǎng)、學(xué)術(shù)本位的確立和學(xué)術(shù)梯隊(duì)的布局,在研究領(lǐng)域開(kāi)拓的進(jìn)程中孕育學(xué)術(shù)意識(shí)的鍛煉、學(xué)術(shù)視野的獨(dú)辟蹊徑或者獨(dú)上高樓和學(xué)術(shù)方法的推陳出新或者辭舊迎新,等等)。學(xué)術(shù)史已經(jīng)為我們的觀點(diǎn)提供了有力的佐證。(當(dāng)然,這里的“學(xué)術(shù)史”是“注重進(jìn)程,消解大家”的“學(xué)術(shù)史”,而不是“文苑傳”、“詩(shī)文評(píng)”或者“學(xué)案”,等等。)
無(wú)論是否“為師”,“開(kāi)風(fēng)氣”的學(xué)術(shù)舉動(dòng)都是應(yīng)當(dāng)受到我們的歡迎、得到我們的喝彩和贏得我們的期待。在當(dāng)前的學(xué)術(shù)生態(tài)中,“但開(kāi)風(fēng)氣即足矣”本身就是一種務(wù)實(shí)的風(fēng)氣。“務(wù)實(shí)”不是“爬行現(xiàn)實(shí)主義”。在《注評(píng)》中,我們透過(guò)字里行間可以讀到一具“務(wù)實(shí)”的靈魂,這既是文學(xué)史家的靈魂,也是知識(shí)分子的靈魂。
我們無(wú)意高估《注評(píng)》在20世紀(jì)中國(guó)文學(xué)學(xué)科史中的地位,僅就其在“文學(xué)現(xiàn)代性”中所發(fā)揮的作用進(jìn)行評(píng)價(jià)。錢、袁兩位先生除了將這部輯錄了二十世紀(jì)舊體詩(shī)詞精華的著作作為他們的“友誼的紀(jì)念”,更旨在以此對(duì)“舊詩(shī)詞創(chuàng)作與文學(xué)史敘述的關(guān)系”這一問(wèn)題的討論和研究提供可資借鑒的參考。
二
在《注評(píng)》的首尾,錢理群先生的序《一個(gè)有待開(kāi)拓的研究領(lǐng)域》和袁本良先生的跋《老樹(shù)春深更著花》以一貫之,揭示了“二十世紀(jì)舊體詩(shī)詞”在他們的思考中所占據(jù)的位置。簡(jiǎn)而言之,這兩篇文章的標(biāo)題形象地展現(xiàn)出了他們“合作的結(jié)晶”中那道最深邃,同時(shí)也是最耀眼的光澤。更為難能可貴的是,這部著作不僅為我們提供了“一個(gè)有待開(kāi)拓的‘老樹(shù)春深更著花'的研究領(lǐng)域”,也記錄了新時(shí)期以來(lái)文學(xué)史研究工作中對(duì)“文學(xué)現(xiàn)代性”進(jìn)行梳理的大膽嘗試和勇敢推進(jìn),這是《注評(píng)》最具“開(kāi)風(fēng)氣”意義之所在。
顯然,“二十世紀(jì)舊體詩(shī)詞”應(yīng)當(dāng)隸屬于“二十世紀(jì)中國(guó)文學(xué)”的范疇。1985年起,錢理群、黃子平、陳平原三位先生合作陸續(xù)推出了《論“二十世紀(jì)中國(guó)文學(xué)”》和《二十世紀(jì)中國(guó)文學(xué)三人談》,正式提出了“二十世紀(jì)中國(guó)文學(xué)”的概念。作為這一文化事件的親歷者,錢理群先生無(wú)疑是認(rèn)同他們所歸納出的“二十世紀(jì)中國(guó)文學(xué)”的四大特征的,即“走向‘世界文學(xué)'的中國(guó)文學(xué)”、“以‘改造民族的靈魂'為總主題的文學(xué)”、“以‘悲涼'為基本核心的現(xiàn)代美感特征”、“有文學(xué)語(yǔ)言結(jié)構(gòu)表現(xiàn)出來(lái)的藝術(shù)思維的現(xiàn)代化進(jìn)程”。細(xì)考四大特征,“二十世紀(jì)舊體詩(shī)詞”并沒(méi)有獲得相應(yīng)的生存空間,更不用說(shuō)客觀的文學(xué)史坐標(biāo)了。
“舊體詩(shī)詞”不入“新文學(xué)史”不但是建國(guó)以來(lái)文學(xué)史家在研究工作中約定俗成的“潛規(guī)則”(譬如王瑤先生的《論現(xiàn)代文學(xué)與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的關(guān)系》),而且是部分文學(xué)史家竭力維護(hù)的“清規(guī)戒律”(譬如唐弢先生的《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史的編寫問(wèn)題》)。上世紀(jì)80年代,啟蒙者們?cè)谑澜缥膶W(xué)的影響下對(duì)建國(guó)以來(lái)被政治認(rèn)定扭曲了的現(xiàn)代化進(jìn)程做著正本清源的工作,尋找著屬于東方的“文學(xué)現(xiàn)代性”。當(dāng)“旁采泰西”的渴望超越“上法三代”的追求時(shí),“二十世紀(jì)中國(guó)文學(xué)”的外延局限性也便在情理之中了。將中國(guó)文學(xué)現(xiàn)代性的進(jìn)程定位于“亞洲的覺(jué)醒”的格局之中,這種國(guó)際視野值得推崇,但對(duì)傳統(tǒng)中國(guó)以及現(xiàn)代中國(guó)的理解與尊重?zé)o疑應(yīng)當(dāng)與之并重。承認(rèn)“二十世紀(jì)舊體詩(shī)詞”的創(chuàng)作是一種具有獨(dú)立價(jià)值的文學(xué)實(shí)踐,并將其納入“二十世紀(jì)中國(guó)文學(xué)”的大家庭中,這是建立在“現(xiàn)在文學(xué)”這一概念與生俱來(lái)的排斥性之外的、沖破了現(xiàn)代/傳統(tǒng)、新/舊的二元對(duì)立思維模式的開(kāi)拓。《注評(píng)》所呈現(xiàn)給我們的正是這樣一種“二十世紀(jì)中國(guó)文學(xué)”自身的涅磐。伴隨新世紀(jì)的曙光,錢、袁兩位先生的工作已從別有幽懷升華為別有用心,他們正在著力為“重建現(xiàn)代文學(xué)”的補(bǔ)天工程煉石。
三
被錢理群先生稱為“研究新詩(shī)人與舊體詩(shī)詞關(guān)系的最好的文章”的劉吶的《舊形式的誘惑》可謂促成《注評(píng)》的重要起因。此文在序中被再三征引,錢先生發(fā)凡劉氏的觀點(diǎn),提出了“新詩(shī)與舊詩(shī)是只能互補(bǔ),而不能相互替代的”。在新文學(xué)史上,魯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老舍、郁達(dá)夫、田漢、朱自清、王統(tǒng)照、聶紺弩等人皈依舊體詩(shī)詞的“忤逆”之舉說(shuō)明了“舊詩(shī)在表達(dá)現(xiàn)代人(現(xiàn)代文人)的思維、情感……方面,并非無(wú)能為力,甚至在某些方面,還占有一定的優(yōu)勢(shì),這就決定了舊詩(shī)詞在現(xiàn)代社會(huì)不會(huì)消亡,仍然保有相當(dāng)?shù)陌l(fā)展天地”;在二十世紀(jì)舊體詩(shī)詞的發(fā)展史上,辛亥革命前后、40年代抗戰(zhàn)時(shí)期和接近世紀(jì)末的“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后的消化時(shí)期成為并峙的三個(gè)創(chuàng)作高峰,啟示了我們:“特定歷史情境下對(duì)傳統(tǒng)文化的認(rèn)同,與舊詩(shī)詞形式的采用之間所存在的內(nèi)在聯(lián)系,應(yīng)該是我們考察、研究傳統(tǒng)詩(shī)詞的現(xiàn)代命運(yùn)的一個(gè)較好的視角。”肯定舊體詩(shī)詞作為一種文學(xué)形態(tài)的“優(yōu)勢(shì)”并考察、研究其“現(xiàn)代命運(yùn)”,這是《注評(píng)》點(diǎn)燃的一把星星之火。
在史料中求史識(shí),是《注評(píng)》作為一部文選與一部行走在“二十世紀(jì)中國(guó)文學(xué)”邊緣上的文本的內(nèi)在張力。第一,錢理群先生在序中說(shuō)“通過(guò)對(duì)現(xiàn)代舊詩(shī)詞的寫作實(shí)踐(作品)的具體分析,找出‘現(xiàn)代社會(huì)的特定情境'、‘作為現(xiàn)代人的詩(shī)(詞)人的特定情感、思維'與‘舊詩(shī)詞的特定形式'這三者之間的具體關(guān)系,并在大量的細(xì)讀分析的基礎(chǔ)上,對(duì)舊體詩(shī)詞在現(xiàn)代社會(huì)發(fā)展的余地(意義、價(jià)值)、限度、困惑與前景作出科學(xué)的總結(jié)。”建立在《注評(píng)》基礎(chǔ)上的“科學(xué)的總結(jié)”顯示了錢、袁兩位先生的學(xué)術(shù)雄心,但從中不難讀出更多的是他們“有待于少年之努力也”,對(duì)后學(xué)在此領(lǐng)域深入研究的諄諄教誨與殷殷期待。他們不僅“俯首甘為孺子牛”,為來(lái)者編撰了這部工具書式的大觀;而且“示來(lái)者以軌跡”,將研究的肯綮無(wú)償?shù)鼐璜I(xiàn)給了有志青年。“開(kāi)風(fēng)氣”得益于看得遠(yuǎn),看得遠(yuǎn)來(lái)源于站得高,站得高是惟有學(xué)術(shù)責(zé)任心和使命感的學(xué)者才能做到的。第二,在“二十世紀(jì)中國(guó)文學(xué)”的譜系中觀察“二十世紀(jì)舊體詩(shī)詞”,在“二十世紀(jì)舊體詩(shī)詞”的蘊(yùn)藉中研究“二十世紀(jì)中國(guó)文學(xué)”,兩者相得益彰。如果說(shuō)上世紀(jì)70年代末以降是一個(gè)將中國(guó)文學(xué)這個(gè)棄兒送回世界文學(xué)的襁褓中去(繼續(xù)五四未完成的“現(xiàn)代”)的時(shí)代,那么80年代末以來(lái)便是一段健兒憑借自己的雙手,揮灑自己的汗水,“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niǎo)飛”的歲月。兩者共同構(gòu)成了中國(guó)文學(xué)現(xiàn)代化的起步階段,孕育著中國(guó)文學(xué)的健康發(fā)展。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先鋒派開(kāi)啟了新的篇章;在文學(xué)研究中,“二十世紀(jì)中國(guó)文學(xué)”這一概念的成長(zhǎng),即在世界文學(xué)的語(yǔ)境中擺脫獨(dú)語(yǔ)、告別失語(yǔ)、走向?qū)υ挶闶亲钣辛Φ淖C明。《注評(píng)》正是這方面的“預(yù)流”之作。第三,《注評(píng)》的切入點(diǎn)——“二十世紀(jì)舊體詩(shī)詞”——恰是中國(guó)文學(xué)現(xiàn)代化的“阿喀琉斯之踵”,這也決定了此書的“權(quán)力”。新詩(shī)因其先鋒性而成為中國(guó)文學(xué)現(xiàn)代化的尖兵,在相當(dāng)長(zhǎng)的時(shí)期內(nèi)與政治認(rèn)定把持的主流閱讀全緊緊地幫定在了一起。建國(guó)以后,統(tǒng)治者對(duì)舊詩(shī)“束縛思想,又不易學(xué)”的判詞與舉國(guó)唱誦毛主席詩(shī)詞的壯舉既捆住了舊詩(shī)的手腳,又留下了讓其呼吸的空隙。憋悶但不至于窒息、生存但不能夠自由的舊詩(shī)在新時(shí)期“眾聲喧嘩”,達(dá)到了二十世紀(jì)舊詩(shī)史上的最高峰,這一“怪現(xiàn)狀”的確值得我們深思。《注評(píng)》的意義在于為深思得我們提供了一條清澈的小溪,“緣溪行,忘路之遠(yuǎn)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shù)百步,中無(wú)雜樹(sh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直達(dá)至境。這條小溪流淌的泉水便是回歸讀者的主流閱讀權(quán),便是在一定程度上的非政治認(rèn)定的歷史化與經(jīng)典化的進(jìn)程。上述三點(diǎn)凝結(jié)在一起,錢、袁兩位先生那力透紙背的苦心與藍(lán)圖便躍然眼前了。
《注評(píng)》選得精當(dāng),注得準(zhǔn)確,評(píng)得貼切,不失為一部以史家眼光搜集、整理和勘別史料的典范。盡管較之此前劉吶、汪暉、吳曉東、王富仁等人在“舊體詩(shī)創(chuàng)作與文學(xué)史敘述的關(guān)系”這一研究領(lǐng)域的成果并無(wú)重要理論創(chuàng)獲,但其系統(tǒng)化的建樹(shù)還是告訴我們:但開(kāi)風(fēng)氣即足矣!如果說(shuō)此前的著作是鼓風(fēng)氣之作的話,那么繼這部開(kāi)風(fēng)氣的《注評(píng)》而來(lái)的,就應(yīng)當(dāng)是我們的得風(fēng)氣之作了!
(《二十世紀(jì)詩(shī)詞注評(píng)》,錢理群、袁本良編撰,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