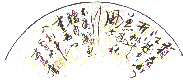內容提要:本文主要分為四個部分進行論述,第一部分主要以甲午戰爭中的黃海海戰為切入口,通過這一戰中中日海軍力量的對比引出對于19世紀后半期中日海軍力量消長著這一問題。第二部分中著重介紹這一消長過程,而第三部分作為全文的重點從體制、經費、重視程度、戰略理念、教育、發展環境等方面進行多角度、多層次的分析。最后一部分得出結論:甲午戰爭中中國海軍的失敗實是19世紀后半期的數十年間中日分殊的必然結果,不是一二人之力所能夠左右得了的。
關鍵詞:軍備競賽;消長;體制;經費;教育制度
一、夢斷甲午年
國殤
操吳戈兮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敵若云,矢交墜兮士爭先。
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
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
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
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
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1)
113年前,在黃海大東溝海面上,兩只艦隊遭遇了,于是“車錯轂兮短兵接”,雙方爆發了激烈的戰斗——這就是中日戰爭史上著名的黃海海戰。交戰的雙方分別是清政府的北洋艦隊和日本聯合艦隊,在萬頃波濤之中,兩軍搏殺了近五個小時,北洋海軍英勇奮戰、視死如歸,譜寫了甲午戰爭史上慷慨悲壯的歷史悲歌。
黃海海戰是中日雙方海軍的主力決戰,其規模之巨大,戰斗之激烈,時間之持久,在世界近代海戰史上是罕見的。就雙方的兵力損失情況而論,中方損失無疑是大于日方的,“九月,丁汝昌率北洋兵艦與日本戰于大東溝,失致遠、經遠、超勇、揚威四艦。”(2)而日軍只有五艦受創,無一艦沉沒。相較之下,雖然北洋海軍最后迫使日軍撤離戰場,粉碎了日軍的企圖,但是從戰場的損失情況和實際效果來看,此役北洋海軍在戰術層面上確是失敗了。
如果說在1894年九月間發生的這場激戰中北洋海軍尚有搏殺的勇氣的話,那么,北洋海軍于1895年2月17日的最后覆滅就不能不說是一首挽歌了。“2月17日上午8時30分,日本聯合艦隊以松島艦為首艦,本隊千代田、橋立、嚴島、第一游擊隊吉野、秋津洲等艦緊隨其后,第三、第四游擊隊殿后,從百尺崖起航,成單縱陣形,各高懸軍旗,魚貫自北口進,徐徐入威海衛港。”“鎮遠、濟遠、平遠、廣丙、鎮東、鎮西、鎮南、鎮北、鎮中、鎮邊十艦,皆降下中國旗,而易以日本旗。唯一的例外是康濟艦,其艦尾仍懸黃龍旗。因為這是留下來載送丁汝昌靈柩的。……4時,康濟艦載著丁汝昌、劉步蟾、楊用霖、戴宗騫、沈壽昌、黃祖蓮等靈柩6具,以及陸海將弁和洋員,在汽笛的哀鳴聲中,迎著瀟瀟冷雨,凄然離開威海衛港,向煙臺港駛去。”(3)北洋海軍就這樣覆滅了,中國的海軍夢也在甲午戰爭的隆隆炮聲中化作云煙。究其原因,應該說是諸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然而實力的差距已然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李鴻章說過:海戰唯恃船跑,“稍有優絀,則利鈍懸殊”。(4)從整個甲午戰爭間北洋海軍與日本海軍的對比來看,可以說是正是略遜一籌,故而姑且不論其他因素的影響,但從武備一方面看,北洋海軍就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下面我們試以黃海海戰為例來說明這種實力上的差距。
表一:黃海海戰的北洋海軍和日本聯合艦隊實力對照表(5)
| 類別 |
北洋艦隊 |
日本聯合艦隊 |
比較 |
| 軍艦總數 |
10 |
12 |
-2 |
| 艦種 |
鐵甲艦 |
4 |
1 |
+3 |
| 半鐵甲艦 |
1 |
3 |
-2 |
| 非鐵甲艦 |
5 |
8 |
-3 |
| 火炮 |
火炮總數 |
173 |
268 |
-95 |
| 30公分以上口徑重炮 |
8 |
3 |
+5 |
| 20公分以上口徑大炮 |
16 |
8 |
+8 |
| 15公分以下口徑炮及雜炮 |
149 |
160 |
-11 |
| 15公分(6吋)口徑速射炮 |
|
30 |
-30 |
| 12公分(4.7吋)口徑速射炮 |
|
67 |
-67 |
| 總噸數(噸) |
31366 |
40849 |
-9483 |
| 總馬力(匹) |
46200 |
73300 |
-27100 |
| 平均馬力(匹) |
4620 |
6108 |
-1488 |
| 平均航速(節) |
15.5 |
(本隊)15.5
(一游)19.4 |
-0.1
-3.9 |
| 總兵力(官兵人數) |
2054 |
3630 |
-1576 |
綜觀上表,可以看出,日本聯合艦隊在很多方面與北洋海軍相比具有明顯的優勢。具體分列如下:
1)參戰艦只數量:日軍是北洋海軍的1.2倍
2)火跑總數:日軍是北洋海軍的1.549倍
3)總噸位:日軍是北洋海軍的1.302倍
4)總馬力和平均馬力:日軍分別是北洋海軍的1.587倍和1.322倍
5)平均航速:日軍的本隊和第一游擊隊分別是北洋海軍的1.006倍和1.252倍
6)總兵力:日軍是北洋海軍的1.767倍
7)速射炮:日軍有97門,而北洋海軍無一門速射炮
當然,北洋海軍在個別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優勢,例如在鐵甲艦數量方面,北洋海軍就占據著4比1的絕對優勢,而在30公分以上口徑重炮和20公分以上口徑大炮這兩個方面也分別具有8比3和2比1的優勢。不過從總體上來看,北洋海軍處于明顯的劣勢。對此,英國斐利曼特海軍中將曾評論說:“為比較兩軍實力計,但以參與黃海戰斗之軍艦而事對照,已可得起正確結論矣。是役也,無論噸位、員兵、航速、或速射炮、新式艦,實以日本艦隊為優。該國軍艦除赤誠外,性能約略一致,艦體大小由二千二百噸至四千二百噸,俱為甫竣工之新銳艦。中國方面,雖有定遠、鎮遠兩二等戰艦,噸位各七千四百噸;其次經遠、來遠兩艦,噸位亦各二千九百噸,但不過虛具裝甲巡洋艦之名而已。其余各艦,或噸位小,實力弱,或艦型不稱,裝備不當。”(6)
雖然,黃海海戰交戰雙方艦只并未涵蓋兩軍所有艦只,但是基本上包括了中日海軍的主力,因此,我們從黃海海戰中中日兩軍實力的差距中就可以基本上明了1894年前后中日海軍這種實力上的懸殊。然而,是否中日海軍力量的對比從一開始就是這樣的格局呢?
二、軍備競賽
要明曉這一點,我們就必須追根溯源,從中日兩國海軍的發展歷史說起。
中國自古就有水師,唐宋以后,中國的造船技術有了很大的發展,可以說一度具有領先世界的水平。尤其是1405-1433年間的鄭和七下西洋,堪稱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未有之壯舉。真可謂“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7)然而有清一代,西方各國的航海造船技術有了突飛猛進的進展,海軍相關體制和戰略思想也逐漸近代化。在一二百年的時間內完成了由傳統的海軍向近代海軍的轉化過程。而此時的中國水師仍然沿襲了歷代的固有體制,沒有什么突破性的進展。所謂“水師有內河、外海之分。初,沿海各省水師,僅為防守海口、緝捕海盜之用,轄境雖在海疆,官制同于內地。至光緒間,南北洋鐵艦制成,始別設專官以統率之。”(8)由此可見遲至光緒年間,中國仍然尚未完成由古代水師向近代海軍的轉型。
關于中國近代海軍的初創,《清史稿》中是這樣記載的:“中國初無海軍,自道光年籌海防,始有購艦外洋以輔水軍之議。同治初,曾國籓、左宗棠諸臣建議設船廠、鐵廠。沈葆楨興船政于閩海,李鴻章筑船塢于旅順,練北洋海軍,是為有海軍之始。”(9)可見,中國海軍的創建,當在咸同之際,而真正完成,恐已到了光緒初年。下面我們用一些重要的時間點粗略勾勒以下自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起至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中國海軍的發展脈絡: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文豐疏言購呂宋國船一艘,駕駛靈便,足以御敵。旋諭隸水師旗營操演,并諭紳商多方購置。是為海軍購艦之始。
·咸豐六年(1856年),怡良疏言,允英國司稅李泰國之請,置買火輪船,以剿粵匪。旋隸向榮調遣。
·同治元年(1862年),曾國籓于安慶設局,自造小輪船一艘。(自造輪船之始)
·六年(1867年),李鴻章遷虹口制造局于高昌廟,建船塢,名曰江南制造局。……是年,瑞麟向英國訂購六兵船。(江南制造局之始創)
·光緒元年(1875年),制造局制馭遠兵船成。船政制元凱兵船成。以揚武練船令學生游歷南洋各處,至日本而還。尋諭南北洋大臣籌辦海防。令總稅務司赫德赴天津,與李鴻章商訂購英國二十六頓半、三十八頓半之砲船各二艘,專備海防之用。是年,沈葆楨購法國威遠兵船。(至日本宣揚武力)
·二年(1876年),沈葆楨會同李鴻章奏派學生,分赴英、法各國,入大學堂、制造局練習。此為第一屆出洋學生。是年,船政制登瀛洲、蓺新兩兵船成。制造局制金甌小鐵甲船成。(自造小鐵甲船之始)
·三年、四年(1877-1878年),泰安、威遠、超武兵船亦成。沈葆楨疏請各省協款,每年解南北洋各二百萬,專儲為籌辦海軍之用,期十年成南洋、北洋、粵洋海軍三大枝,猶恐緩不濟急,請以四百萬先解北洋,俟成軍后,再解南洋。(籌辦三大海軍力量)
·六年(1880年)……李鴻章設水師學堂于天津。旋以在德國船廠定購之定遠、鎮遠二鐵艦。(訂購兩艘二等戰艦,即定遠、鎮遠二姊妹艦)
·十四年(1888年),海軍衙門奏定官制,設提督、總兵、副將、參將、游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經制外委等官。是年,在英、德廠所造致遠、靖遠、經遠、來遠四快船來華。英百濟公司所造出海魚雷快艇亦告成。六月,臺灣番民叛,命致遠、靖遠二艦往剿平之。(海軍衙門設立,同時自英、德購進四艘鐵甲或半鐵甲之巡洋艦)
·二十年(1894年),船政制通濟練船成。訂購英國砲艦一艘,命名福安。二月,鎮遠、定遠二艦置新式克鹿卜快砲十二尊。四月,朝鮮內亂,北洋遣兵艦往剿。五月,與日本兵船戰于牙山口外,濟遠船傷,廣乙船沈,操江船失,載兵之高升商船亦沈。九月,丁汝昌率北洋兵艦與日本戰于大東溝,失致遠、經遠、超勇、揚威四艦。(黃海海戰)
·二十一年(1895年),日本以師船攻威海,定遠、鎮遠各艦亦失,丁汝昌敗死。(北洋海軍覆沒)(10)
我們再來看日本方面:
“日本古無海軍,安政二年六月,和蘭人始獻蒸汽船,德川將軍家定遣矢田崛景、藏勝麟太郎等于長崎就和蘭人學操汽船術,復遣榎本釜次郎、赤松太三郎等往和蘭國習海軍法,又購觀光艦于和蘭。……慶應丁卯,德川氏還政,設三職隸八課,始有海陸軍務之名,而未設專官。……八月,于兵部省中分陸軍、海軍二部,各設分局,逮五年二月,始廢兵部省,與陸軍分,專設海軍省。六年六月重定官制,沿為今制。”(11)
·1872年(同治十一年、明治五年)11月28日,根據“全國皆兵主義”,頒布《征兵告諭》,實行國民義務兵役制。用普遍義務兵役制,來取代武士職業兵役制。告諭中規定:“全國四民男子年達二十歲者,悉宜編入兵籍,以備緩急”。同時,設海陸軍。兵役制的改革是明治政府加強軍事力量,準備對外擴張的重要措施之一。表明日本向軍國主義道路的邁進。從征兵告諭發布時起,日本先后設立了海軍學校一所,海軍兵團三處,用以培養和補充海軍軍官。但當時日本海軍力量仍很薄弱,總共大小艦船不過十七艘。(12)
·1874年(同治十三年,明治七年),日本侵略臺灣的失敗,使明治政府“痛感艦船之不足,向英國定購了扶桑、金剛、比睿三艦”(13)“這是海軍省設立后向外國購置新艦的開始”(14)
·日本自1868年明治維新之后,經過十五年的大力擴充和苦心經營,到了1882年(光緒八年、明治十五年),日本已擁有“艦船十二艘,兵員八千九百九十五人”(15)的一支海軍力量。
·日本政府制定了從1883年(光緒九年、明冶十六年)開始的八年造艦計劃。
·明治政府決定從1886年(光緒十二年,明治十九年)發行海軍公債
·1888年(光緒十四年、明冶二十一年),西鄉從道又提出《第二期軍備擴張案》,這是一個龐大的造船計劃。其中包括建造海防艦以下四十六艘的五年計劃。
·至1890年(光緒十六年、明治二十三年),日本海軍擁有完成和正在建造的艦只計二十五艘。合計五萬余噸(16)
·1892年(光緒十八年、明治二十五年)。向英國購買了當時世界上最快的巡洋艦“吉野”。
·1893年(光緒十九年,明治二十六年)2月,天皇睦仁再次下諭節省內廷經費。六年間,每年撥給造艦經費三十萬元。又命令全體文武官員,除特殊情況外,在此期間,一律繳納十分之一的薪俸作為造艦費。并決定擴大原計劃之軍艦制造費。計劃在七年中,以一千八百萬元的巨款,建造鐵甲戰斗艦二艘、巡洋艦一艘、通報艦一艘。
·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前,日本政府以軍港為中心,將全國海岸劃成五個海軍區。每一海軍區設一海軍鎮守府。計:第一海軍區:橫須賀;第二海軍區:吳第三海軍區:佐世保;第四海軍區:舞鶴;第五海軍區:室蘭(未定)(17)
·甲午中日戰爭前,日本海軍艦船的編制是,以松島為旗艦,合高千穗、千代田、高雄、大和、筑紫、赤城、武藏,編為常備艦隊。其他艦艇則分屬于各鎮守府。
綜合中日兩國海軍發展的歷史,我們選取1888年這個時間點作為參照,不難看出,此時中國海軍較之于日本海軍仍然具有很大的優勢。具體如下:
表二:1888 年北洋海軍與日本海軍實力對照表(18)
| 戰艦種類 |
中國
(僅計北洋海軍) |
日本 |
| 二等戰艦 |
2 |
1 |
| 包括二等戰艦在內的鐵甲艦 |
4 |
2
(包括1865年法國產的撞船“東艦”) |
| 快船(巡洋艦) |
7 |
5 |
| 艦船總數 |
24
(不含運輸船) |
22(不含運輸船) |
| 官兵 |
4千余人 |
近萬人(參照黃遵憲《日本國志》的記錄似少于此數) |
由此可見,至1887年時,中國僅一支北洋海軍就足以與整個日本海軍相抗。而且在二等戰艦、鐵甲艦、快船等主要指標上還領先于日本海軍,如果再加上南洋海軍的實力(福建海軍已于之前的馬尾海戰中全軍覆沒),自然遠出于在日本之上。關于這一點,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光緒元年(1875年),制造局制馭遠兵船成。船政制元凱兵船成。以揚武練船令學生游歷南洋各處,至日本而還。”(19)當時,“以英人郎威理司海軍訓練”。(20)在這個時候,中國尚可耀兵與日本,所謂“至日本而還”,可見當時的日本海軍勢力可謂甚不足觀,其時,郎威理曾建議借此時機一舉殲滅日本海軍主力,后來這一建議雖然被否決,但由此大抵可以看出中日海軍力量這時尚存在巨大差距。這一事件大大刺激了日本當局,也加快了其擴軍備戰的步伐。但即便如此,至1888年,從中日海軍實力對比來看,優勢仍然在中國一方。
然而僅僅六年之后的1894年,中國的北洋海軍卻大敗于日本海軍之手。從第一部分列舉的黃海海戰中中日海軍力量的對比中,我們驚奇的發現,短短六年之后,日本海軍在諸多方面的實力已經遠遠高于北洋海軍之上,尤其是在速射炮、艦船航速和新銳艦的數量上,中日兩國可謂已經不可同日而語。由此,甲午戰爭中中國海軍的慘敗也就似乎不可避免了。那么產生這種激變的原因何在呢?
三、中日海軍力量消長的原因
要推究這種激變的內在原因,就必須結合多方面的因素進行一綜合的分析。總結概括起來,就是因為中日之間的巨大分殊。正是這種分殊導致了中日海軍力量在19世紀后半期的消長變化,具體來說有以下六個方面:體制之殊、經費之殊、重視程度之殊、戰略理念之殊、教育制度之殊、發展環境之殊。
體制之殊
若論中日海軍體制之殊,首先需明確中日海軍的體制是什么。
就中國來看,海軍最開始并沒有獨立的機構,而是水師的輔助。整個體制也仍然沿襲了水師軍制而無所變化。在海軍的管理上,最早是由中央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進行管理,在李——阿艦隊被遣散以后,遂改由地方督撫和北洋通商大臣等辦理,但始終未成立一專門機構。1885年(光緒十一年)10月13日,清政府發布設立海軍衙門的決定。派醇親王奕譞為總理海軍大臣,“所有沿海水師,悉歸節制調遣”。派慶親王奕劻、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為會辦大臣。正紅旗漢軍都統善慶、兵部右侍郎曾紀澤任幫辦。并責成李鴻章“專司其事”。海軍衙門的設立,標志清政府籌建海軍的活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21)
而日本方面海軍管理體制的近代化就早了許多了。“慶應丁卯,德川氏還政,設三職隸八課,始有海陸軍務之名,而未設專官。明治元年戊辰二月,改為軍防事務局,閏四月復改為軍務官,二年七月,又改為兵部省,皆以海軍隸其中,而別設海軍大將、中將、少將等官。四年四月,復置大、中、少佐,大、中、少尉等官。八月,于兵部省中分陸軍、海軍二部,各設分局,逮五年二月,始廢兵部省,與陸軍分,專設海軍省。六年六月重定官制,沿為今制。”(22)
由此,我們便不難看出,日本早在明治四年(1871年)就已經將陸海軍分置二省,相當于部級單位。而中國遲至1885年才建立海軍衙門這一專門機構,時間較日本晚了14年,從級別上來說,仍然是隸屬于兵部之下的一個機構。由此,我們便不難看出中日海軍在管理制度上存在著很大不同,日本有專門的海軍省管轄,而中國只有一個海軍衙門,而這一海軍衙門又無多少實權,海軍管理權實際上掌握在北洋大臣、南洋大臣及各地方督撫手中,權力分散而且較為混亂、不利于集中管理和指揮,從而影響了海軍的戰斗力的發揮和相互間的配合。這一體制上的重大缺陷在中國海軍發展的早期,問題尚未充分暴露,但到了19世紀末葉,其弊病就暴露無遺了。而日本海軍制度上的優越性在19世紀后期卻逐漸發揮出來,為日軍海軍的發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平臺。
經費之殊
從中日海軍軍費的投入來看,也可以窺見19世紀后半期中日海軍力量消長的原因。下面以僅有的材料就中日雙方海軍軍費的投入作一對比
表三:北洋海軍與日本海軍軍費對照表(23)
| 年份 |
中國(北洋海軍) |
日本(按照 1895年中日貨幣匯率折算) |
| 1868-1875(6月) |
情況十分復雜,這里不能十分明確,理論上南北洋海軍年撥款 200萬兩,但是實際上并未達到此數目。據姜鳴的研究成果,認為在光緒元年(1875年)—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北洋共的款項2300萬兩,其中后八年(1887-1894)共收1053萬兩(平均每年115萬兩,后八年年均131.625萬兩) |
約 567.5萬元(358萬兩白銀)平均每年近45萬兩 |
| 1875/6-1876/6 |
270萬元(約170萬兩) |
| 1876/6-1877/6 |
354萬元(約223萬年) |
| 1877/6-1878/6 |
321.75萬元(約203萬兩) |
| 1878/6-1879/6 |
264.16萬元(約166.7萬兩) |
| 1879/6-1880/6 |
263.63萬元(約166萬兩) |
1880/6-1881/6
(1881.6-1882年資料缺) |
365萬元(約230萬兩) |
| 1883-1890 |
年均 330萬元(約208.2萬兩) |
| 1891-1895 |
5855萬元(還不包括天皇內廷經費等項),年均1171萬元(約738.8萬兩) |
由此可見,自 1875年以后,日本對于海軍的投入就已經超過了北洋海軍,并且在1876-1890年間始終維持在200萬兩以上,1891年后,每年的平均投入更是達到738萬兩白銀,遠遠高于清朝對于北洋海軍的投入。總的來看,1875-1894年中,清政府對于北洋海軍的理論投入應為4000萬兩(按南北分解計算,每年北洋海軍可得銀200萬兩),據姜鳴的研究成果認為實際到位的只有2300萬兩,而日本方面則高達6516萬兩以上(1881年6月至1882年資料缺)。通過上面的分析,不難發現中日經費投入的巨大懸殊,沒有投入,何嘗會有收獲,故而中日海軍力量為何會在19世紀后半期發生激變也就不難解釋了。
重視程度之殊
若論中日雙方對于發展海軍的重視程度,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從日本方面來看,日本上至于天皇,下達于百姓,都對海軍的發展和海防十分重視。1890年(光緒十六年、明治二十三年),天皇睦仁下諭撥出內帑三十萬元作為造船費。同時,再向民間征集二百余萬元的建艦經費。(24)1893年(光緒十九年,明治二十六年)2月,天皇睦仁再次下諭節省內廷經費。六年間,每年撥給造艦經費三十萬元。又命令全體文武官員,除特殊情況外,在此期間,一律繳納十分之一的薪俸作為造艦費。(25)為了籌措海軍軍費,日本天皇可謂親力親為,以身作則,甚至下諭節省內廷經費以敷海軍之用,其重視程度不可謂不高。而反觀之中國的最高統治者,無論是慈禧還是光緒皇帝,對于海防的重視程度都是很不夠的。集中表現在兩點:
其一是18世紀70年代的海防塞防之爭。其時,中國面臨著嚴重的邊疆危機,阿古柏政權已經控制了新疆的大片地區,其后中國南疆(越南)也出現了邊疆危機,法國的侵略勢力已經滲入越南北圻,逼近廣西、云南。以左宗棠為代表的一些清廷要員主張應以塞防為主,而李鴻章等人仍然認為中國最大的威脅來自于海上,尤其是日本。李鴻章的海防戰略應該說是具有遠見卓識的,但從當時的形勢來看,如果不重塞防,中國將會有再次大片喪失領土之虞。而中國人對于領土向來是十分看重的,所謂“寸土不讓”,而對于一望無際的海疆及制海權的重要意義在當時尚認識不足,故而認為塞防乃當務之急。因此,也就難怪堅持重塞防的一方為何占據主導地位并最終使清廷將大量軍費用于新疆等地區的戰事和加強邊疆防務了。
如果說這一爭論尚屬意見之殊的話,那么北洋海軍軍費的挪用就不能不說是清政府對于海軍建設不甚重視的鐵證了。過去常認為這些款項主要用于營建頤和園,其實不盡然。總署和戶部確定年撥海防經費四百萬兩后,此款便成為眾目睽睽的一大財源。每當清政府財政拮據,便從其中大量騰挪。(26)查北洋海防報銷折,僅光緒元年至六年,就從中挪用“滇案恤款”20.3萬余兩,“借撥河南買米銀”4萬兩,“山西河南兩省賑款”20萬兩,“京師平糶不敷價銀”7.4萬余兩,“河間等處井工”4萬兩,“惠陵工程”4萬兩等等。(27)光緒十二年,海署又借口經費不足,責請將南北洋經費、東三省餉項,自光緒十三年正月起統按二兩平(即京平)核發,(28)每百兩可扣除六兩平余,用來劃抵名義上由海軍衙門專款撥發的“定遠”等八艦薪糧公費。據光緒十三年至二十年“定遠”等艦經費報銷折片統計,八年中平余劃抵薪糧的共二十余萬兩。以上所有各項,雖然在北洋海防報銷折內是列入“登除”欄目,但畢竟都是從海防協餉中騰挪抽分的,且總數達170余萬兩,超過北洋海防經費總收入的7%,所以不能忽視。(29)至于西太后為修建頤和園而挪用海軍款項一事,甚為復雜,可謂眾說紛紜,尤其是其挪用的數目,由數百萬兩至幾千萬兩諸說各異,但是無論如何,修建頤和園對于海軍建設產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尤其是帶來了一定程度上的經費緊張這一點應該是毋庸置疑的。
從以上數例,中日雙方最高領導層對于海軍的重視便可窺見一斑了。我們這里再舉一例:日本政府在制造艦船,擴張海軍的活動中,始終以中國海軍作為對手和假想敵。特別對中國北洋艦隊的定遠、鎮遠二鐵甲艦,感到莫大威脅,耿耿于懷,必欲除之而后快。以致那時不僅在日本海軍軍人中盛傳著“一定要打勝定遠”這樣一句流行的話。甚至在小學校兒童作游戲時,也把兒童們分成甲乙兩組,一組裝作中國艦隊,另一組扮成日本艦隊,進行以捕捉“定遠”、“鎮遠”而決定勝負的戰斗游戲。目的是對兒童進行以戰勝定遠、鎮遠“二巨艦作為日本的戰略目標的教育”。(30)在日本海軍建設可謂婦孺皆知,深入人心。而相較之下,中國之領導高層尚對于海防和海軍建設認識不足,就更不必說中下層民眾了。
戰略理念之殊
中日雙方海軍力量的分殊還在于其戰略理念的不同。
就日本方面而言,日本土地面積狹小而人口稠密,自然資源稀缺,國內市場有限,又屬后起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足夠的殖民地提供巨大的海外市場。因此,日本要擴張勢力,謀求發展,在當時的條件下就必然需要擴展生存空間,而東亞不是美洲,沒有處女地可供拓殖,要想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就必然損害其他國家利益,因此,日本的發展戰略從一開始就具有很強的侵略性和進攻性。“在完成自身的現代化之后,日本開始了向亞洲大陸擴張的生涯。只要看看日本的好戰傳統,看看它的軍事領導人從最古時代就享有的巨大威望,這一點也就毫不奇怪了。講求實際的日本領導人得出了這一明確結論:每個民族必須為自己去掠奪,軟弱和膽小者將一無所獲。”(31)正是基于這一點,日本的戰略從一開始就具有一種進攻性和侵略性。而日本是一個島國,如果想要入侵其他國家就必須穿過茫茫大海,而擁有一支強大的海軍力量對于保障日軍的海上交通線及其在相關海域的制海權是十分重要的,正因為如此日本政府和軍方才把建設近代化海軍提到了如此重要的戰略高度。可以這樣說,基于以上原因,日本的海軍戰略是一種以動制靜,以攻代守的進攻型戰略。
而較之于日本,中國的海軍戰略主要是立足于“防”。從1874年(同治十三年)開始,清政府加緊了籌建海軍的步伐。同年,江蘇巡撫丁日昌提出《海洋水師章程》六條。建議購買和制造大型兵艦,擇沿海險要修筑炮臺,編練水師,簡選精干人員到海軍任職。并建議于沿海建立北洋、東洋、南洋三支水師。北洋水師負責山東、直隸沿海防務,設北洋水師提督于天津;東洋水師負責浙江、江蘇沿海防務,設東洋水師提督于吳淞;南洋水師負責廣東、福建沿海防務,設南洋水師提督于南澳。每支水師各設大兵輪六只,小輪船十只。“三洋提督半年會哨一次,無事則以運漕,有事則以捕盜”(32)三只水師(海軍)分置天津、吳淞、南澳三地,實行分區防御,同時在海岸各險要之處設立炮臺,這種戰略的核心思想是以靜制動,以守為攻,以至于這一思想的影響直至甲午戰爭開始仍未消弭,北洋海軍未能主動尋敵,在經歷了黃海一役后就龜縮于港內,避而不戰,最終被聚殲于威海衛,這一悲劇的發生與清政府整體的海防戰略思想是有著很大關系的。歷史已入近代,艦船的機動性能和續航能力已經有了很大提高,萬里海疆可謂是防不勝防,然而清廷的戰略思想仍然沒有從過去傳統的海防觀念中轉變過來,把大量的金錢和精力放在岸炮建設和近岸防御上,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遠洋海軍的發展,這不能不說是一大失策。
教育制度之殊
從對海軍的教育和培養這一方面看,中國方面與日本方面也存在較大差距。
首先來看中國方面:(光緒)二年,沈葆楨會同李鴻章奏派學生,分赴英、法各國,入大學堂、制造局練習。此為第一屆出洋學生。(33)六年……李鴻章設水師學堂于天津。(34)十一年,曾國荃疏言:“于福建、廣東、浙江三省增設鐵艦、快艦、雷艇。嗣后各兵船專事操練巡洋,不得載勇拖船。”與北洋大臣會奏,派第三屆學生出洋。(35)十三年,……北京設水師學堂于昆明湖,廣東設水師學堂于黃埔。(36)十六年,……八月,北洋設水師學堂于劉公島,南洋設水師學堂于南京。(37)十九年,船政制福靖魚雷快船成。粵督改水師講堂為水師學堂。(38)由此看,從中國1876年(光緒二年)首次派遣學生前往歐洲諸國學習海軍技術到1893年(光緒十九年)為止,清政府先后派遣留洋學生三批,興建了北京昆明湖、廣東黃埔、劉公島、南京四處水師學堂(由于資料不足可能還有遺漏)應該說海軍教育具有了一定的規模,但是尚處于無系統的零散狀態。
而日本方面則是另一番景象:1869年(同治八年、明冶二年)“版籍奉還”之后,長州、薩摩和土佐三個藩,把所屬之全部軍隊交給明冶政府管轄,以補充正在創建中的天皇軍的基本隊伍。為了發展海軍事業,同年在東京開設了海軍學校,其后,在此基礎上建立了海軍大學和海軍工程學校。在這些學校里,聘請英國軍官任教。并選派許多學員到英、美各國實習。(39)從征兵告諭發布時起,日本先后設立了海軍學校一所,海軍兵團三處,用以培養和補充海軍軍官。(40)為了培養海軍人員,日本政府分別在吳港、廣島、橫須賀等地設立海軍兵學校、海軍駕駛學校、海軍造船工業學校、海軍炮術練習所、海軍水雷術練習所等等。1887年(光緒十三年、明治二十年),決定于東京設立海軍大學校,規定“兵學校、水雷部、駕駛學校等畢業之學生可入大學校高等科學習,學期為兩年”。(41)此外,在東京和大阪、函館設商船學校。1888年(光緒十四年、明治二十一年),頒布了《海軍兵學校官制》,其第一條規定:“海軍兵學校為教育海軍將校的學生之所”,辦學宗旨是培養海軍軍官。1889年(光緒十五年、明治二十二年),頒布了《海兵團條例》,在各鎮守府設海兵團,負責各海軍鎮守軍港的守衛兵員,軍艦水兵的教育訓練和新兵征集的工作。(42)關于海軍兵學校,黃遵憲的《日本國志》里有詳盡的描述:“兵學校有校長、教師、助教。學舍分三種,一曰幼年,二曰壯年,三曰專業,幼年取十九歲以下、十五歲以上,在學以五年為期。壯年取二十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在學以三年為期,專業則不論長幼,不拘年限,每年四月海軍召募生徒,有愿學者具狀上申,每年八月入校,入校之始有檢查之法,筋骨強壯與否、能作書與否……各分其等級,第其淺深而受業焉。……校中分官學生、私學生二類,官學生于入校之始自呈誓文。愿終身從事海軍,不營他業,費用皆由官給。……官學生成業后,拔其尤者使留學泰西諸國,亦有別遣士官附居使館以時考究他國兵制,或遇戰爭,如近日荷蘭亞齊之戰,普佛之戰,俄土之戰,皆特遣官吏俾往觀焉。”(43)由上述材料可以看出,日本不僅海軍教育制度興起較中國早,而且從規模和完善程度來看,也比中國略勝一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已經有了一套較為完整的培養體制,能夠源源不斷的為海軍輸送人才,這一點對于中日海軍力量對比的改變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發展環境之殊
就中日雙方海軍的發展環境而論,無疑日方也具有很大的優越性。應該說在19世紀中葉,日本和中國共同遭到了來自西方的強大威脅。中國經歷了1840-1842年的鴉片戰爭,日本經歷了1853年美國內佩里艦隊的叩關。中國和日本都被迫打開了國門。然而之后發生的情況確是截然不同的。
“不論好壞,日本同它之前的中國一樣,這時也被迫遭受西方的入侵。但是,它對這一入侵的反應完全不同于中國。”(44)的確,日本很快作出了積極的回應,戊辰戰爭和大政奉還之后,日本的明治天皇開始了一場大刀闊斧的改革,這一變革使日本在不太長的時間內逐步擺脫了西方殖民者的干涉,贏得了主權的獨立。“經過長期的外交努力之后,1894年,他們(日本)說服英國和美國在五年之內結束其治外法權領事裁判權。……從此以后,不再有任何理由將日本看作是一個劣勢國家,其他列強也步英、美之后塵,很快放棄了他們的特權。到1899年時,日本已獲得對其國土上的所有外國人的法定裁判權,在這情況下,它成為亞洲第一個砸碎西方控制的鎖鏈的國家。”(45)
然而中國的情況卻正與此相反,自1840年以來,中國的半殖民地化程度不是有所下降,而是不斷加深。經過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和19世紀70-80年代的邊疆危機,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受到巨大損失,同時也承受了巨額的戰爭賠款。(鴉片戰爭為2100萬元,第二次鴉片戰爭為1670萬兩——其中英國850萬兩,法國820萬兩)此外,在1851-1864年間中國還經歷了太平天國運動,這場農民運動給清朝的社會經濟造成了嚴重的破壞,花費了清廷數億兩軍費,這樣巨額的花費與空前規模的破壞無疑也對于清政府發展海軍的實力產生了極其不利的影響。
以上主要分析的是內部環境,就外部環境而論,中國處在遠東利益和核心地區,時刻處在列強環伺的狀態之中,諸列強出于自身在華利益的考慮根本不可能允許中國擁有一支強大的海軍。而日本則不同,其處在遠東利益的邊緣地區,而且列強之間由于存在諸多矛盾,也都希望利用日本的擴張來限制其他勢力,因此對于日本采取了縱容的態度,為日本這一時期的軍備擴張提供了一個相對較為安定的國際環境。
四、結論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已不難看出,中日海軍力量在19世紀后半期的消長并非偶然,其有著十分深刻和復雜的原因。由于資料不足,本文這里無法一一進行深入探究,只是勾勒出一個大概的輪廓,理一個大概的思路出來。總而言之,中日海軍力量在19世紀后半期的消長是體制、經費、重視程度、戰略理念、教育制度和國內外環境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我們分析這一問題,應該站在一種全面客觀的角度上,甲午海戰的最終失敗原因是十分復雜的,絕不能簡單的歸咎為慈禧太后、李鴻章、丁汝昌等個人的因素,我以為,甲午戰爭中中國海軍的失敗實是19世紀后半期的數十年間中日分殊的必然結果,不是一二人之力所能夠左右得了的。
注釋:
(1)朱熹,《楚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一百三十六·志一百十一·兵七·海軍
(3)戚其章,《甲午海戰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377頁
(4)李鴻章,《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78,第61頁
(5)戚其章,《甲午海戰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126-127頁
(6)《斐利曼特關于黃海海戰的評論》,《海事》第10卷,第1期,第41頁
(7)《明史·鄭和傳》
(8)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一百三十五·志一百十·兵六·水師
(9)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一百三十六·志一百十一·兵七·海軍
(10)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一百三十六·志一百十一·兵七·海軍
(11)黃遵憲,《日本國志》卷二十五·兵志五,天津人民出版社(點校本),第627頁
(12)孫克復、關捷,《中日甲午海戰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
(13)田內丈一郎,《海軍辭典》,第3頁
(14)井上清、鈴木正四,《日本近代史》,日本東京合同出版社,昭和三十一年(1956年),上卷,第70頁
(15)內田丈一郎,《海軍辭典》,第3頁
(16)小山弘建、淺田光輝,《日本帝國主義史·日本帝國主義的形成》,第36頁
(17)川崎三郎,《日清戰史》第1編,第3章,第97頁。日本參謀本部:《日清戰史》則作第四、五海軍區尚無鎮守府,暫時合并于佐世保和橫須賀兩鎮守府。
(18)根據孫克復、關捷《中日甲午海戰史》和黃遵憲《日本國志》相關資料
(19)(20)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一百三十六·志一百十一·兵七·海軍
(21)孫克復、關捷,《中日甲午海戰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
(22)黃遵憲,《日本國志》卷二十五·兵志五,天津人民出版社(點校本),第627頁
(23)參考黃遵憲《日本國志》,孫克復、關捷《中日甲午海戰史》等,姜鳴《北洋海軍經費初探》等資料綜合分析擬定
(24)(25)孫克復、關捷,《中日甲午海戰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
(26)《清德宗實錄》(一),第496、561頁
(27)《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三十六,第21頁
(28)《清末海軍史料》,第627-628頁
(29)姜鳴,《北洋海軍經費初探》,《浙江學刊》,1986,第五期
(30)孫克復、關捷,《中日甲午海戰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
(31)斯塔夫里阿諾斯著,吳象嬰、梁赤民譯,《全球通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第488頁
(32)《丁日昌擬海洋水師章程》(同治十三年十月十一日),見《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98,第26頁
(33)(34)(35)(36)(37)(38)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一百三十六·志一百十一·兵七·海軍
(39)(40)(41)(42)孫克復、關捷,《中日甲午海戰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
(43)黃遵憲,《日本國志》卷二十五·兵志六,天津人民出版社(點校本),第644-646頁
(44)斯塔夫里阿諾斯著,吳象嬰、梁赤民譯,《全球通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第483頁
(45)斯塔夫里阿諾斯著,吳象嬰、梁赤民譯,《全球通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第488頁
主要參考書目:
朱熹,《楚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
戚其章,《甲午海戰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李鴻章,《李文忠公全書》
《明史·鄭和傳》
黃遵憲,《日本國志》,天津人民出版社(點校本)
孫克復、關捷,《中日甲午海戰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
田內丈一郎,《海軍辭典》
小山弘建、淺田光輝,《日本帝國主義史·日本帝國主義的形成》
川崎三郎,《日清戰史》
《清德宗實錄》(一)
《清末海軍史料》
姜鳴,《北洋海軍經費初探》
斯塔夫里阿諾斯著,吳象嬰、梁赤民譯,《全球通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