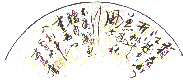內容提要:本文搜集史料對隋煬帝征討高句麗戰爭的全過程進行了詳細考訂,對戰爭爆發的原因、結果,及隋與高句麗雙方戰術進行了深入分析。高句麗經五百年的獨立發展擴張,在東北亞形成有如后來滿清對明朝般俯瞰中原的形勢,已非華夷朝貢體制可以包容。但隋煬帝妄自尊大御駕親征瞎指揮,期望象經通西域降服突厥那樣,以炫耀武力大陳中華禮樂不戰而屈人之兵。但高句麗利用天時地利頑強抵抗,使百萬隋軍三次潰退。隋煬帝唯權力意志是用,國內民眾無法承受兵役徭役起義反叛,政治失控使隋朝滅亡,煬帝本人成為千古暴君。
關鍵詞:隋煬帝高句麗朝貢圣人可汗地緣政治
隋大業三年(607),盛世天子隋煬帝旌旗結彩帶著后妃百官北巡蒙古草原,在啟民可汗牙帳見到通使于突厥的高句麗使者,即宣旨要求高麗王來朝,“如或不朝,必將啟民巡行彼土”。[1]煬帝北巡后又西狩,經通西域,萬乘西出玉門關,并親征青海滅吐谷渾,又遣使出海通使南洋、日本。其時四夷賓服,隋國力達于鼎盛,在開鑿大運河等連年大役后,煬帝沒有讓民眾休養生息喘一口氣,而是緊接著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因高麗王不朝而于大業八、九、十年連續三年興師百萬,三次御駕親征高句麗,卻均歸于失敗,致使天下騷動,隋王朝也由極盛而劇轉為敗亡。隋煬帝征高句麗是中世紀政治史上的大事,后果也出乎其預料,成為歷史的轉折點,牽涉的問題很多,中外史學界多有評論。筆者趁來韓國講學訪問之際將舊作再作一番修改,試圖以客觀公正的態度對這一影響深遠的事件作一全面考察,以求教于中韓學界。
一、亞地緣政治形勢和高句麗與中原王朝的關系
隋時東北亞地區居住著許多民族集團和民族國家,《隋書》將其列入東夷傳而統稱東夷,其中高句麗國力最為強盛并與隋接壤。高句麗立國有四五百年之久,已地跨鴨綠江兩岸,西至遼水,領有今遼東半島和朝鮮半島北部,建都平壤。其南端是百濟,東南面有新羅,在朝鮮半島上鼎足而立。高句麗北面松花江流域是靺鞨部族,嫩江和黑龍江上游一帶是室韋部族,其西面是契丹、霫、奚等游牧部族,再往西蒙古草原上就是隋扶植的啟民可汗東突厥政權。隨著吐谷渾的滅亡及中亞西突厥的崩離,高句麗成為隋邊境唯一擁有強大軍事力量的民族國家。按照中國傳統的華夷朝貢體制,因高句麗王作為藩國主朝貢于中國,被南北朝及隋唐歷代王朝封為高麗王,故又稱其國為高麗國。
從現代語言學考察的結果來看, 東夷各部族和民族國家均屬阿爾泰語系通古斯語族,種族上是近親,其中契丹、室韋、奚、霫屬東胡系統,他們與先前的烏桓、鮮卑、柔然及后來的蒙古為同族。高句麗與三韓的百濟、新羅、任那及靺鞨屬濊貊系統,與后來的女真、滿洲人為同族。但語言相近風俗不同,高句麗與三韓主要為農業,其他則是游牧和狩獵民族。中國古籍記載公元前11世紀周武王滅殷商時,殷宗室箕子率眾東走朝鮮,教濊人田桑禮教,建朝鮮國并受周封爵。[2]但韓國有學者認為“箕子”可能只是古朝鮮人用自己的語言系統發出的王號之一,從而否定箕子東遷說。[3]日本學者白鳥庫基則認為箕子是虛構的人物[4]。箕子的事跡不在本文討論之例,但朝鮮半島早在三千年前已有了王國應是有史可據。箕子朝鮮傳了40余代漢初被燕人衛滿襲破,建立衛氏朝鮮。公元前108年,漢武帝出兵滅衛氏朝鮮,于其地分置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后又罷臨屯、真番,以其地并入樂浪、玄菟。東漢末建安九年(204),遼東太守公孫康在樂浪郡南另設帶方郡,三國曹魏于正始五年(244)滅公孫氏。這樣,從漢元封三年(前108)一直到魏晉四百年間,中原王朝都控制著遼東半島和朝鮮半島北部,實行和內地一樣的郡縣制度。先進的漢文化及典章制度由此直接輸入朝鮮半島,并影響半島以外的其它地區。[5]
晉末喪亂,五胡入主中原,遼東半島和朝鮮半島在戰亂中逐漸脫離中原的控制。所以當大業三年(607)隋煬帝巡視東突厥在啟民可汗帳見到高句麗使者時,裴矩就說:“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之封箕子,漢世分為三郡,晉氏亦統遼東”。[6]認為遼東朝鮮均曾是中國的舊疆。但是,朝鮮半島南部卻從來未被中原王朝征服領轄過。約在公元1至2世紀時,半島南部濊貊族中出現許多部族國家,有馬韓、辰韓、弁韓三大區域,漢朝官員通過樂浪郡與三韓打交道。4世紀時,三韓分別形成百濟、新羅、任那三個王國,其中百濟與新羅交通中國,特別是與南朝交往更多,任那則依附隔海相望的倭國以自重。
三韓以北的高句麗興起于公元前37年,也是從濊貊部落中發展起來,創業主朱蒙在漢郡縣管不了的長白山區建立政權,多次與漢朝發生戰爭。晉末五胡亂華之時,高句麗如五胡入主中原一樣,也于公元313年乘機南下攻占樂浪郡,翌年又占領帶方郡,不久將都城遷入平壤,使中原王朝直接統治朝鮮半島的歷史宣告結束。又跨過鴨綠江與立國遼東的鮮卑慕容氏前燕政權爭雄,被慕容氏擊敗。前燕敗亡后漢人馮氏曾奉高句麗人高云為主,后又自己取而代之建立馮氏后燕政權,而終被立國中原的鮮卑拓跋氏北魏政權攻破,其國人大批逃亡入高句麗,或有浮海遠逃到今廣東地區者。北魏在六鎮叛亂中瓦解,中原東西魏分立,北周北齊禪代,及北周滅北齊,多次政治動亂與政權易姓,使塞外遼東無遐顧及,高句麗趁機向西侵蝕拓展,把疆域擴張至遼水邊,成為東北亞最強大的國家。
千百年來,東北亞各民族均受到中原先進文化的影響,吸收漢文化使用漢字并爭先恐后通使朝貢于中國,其中繼古朝鮮國而起的高句麗文明程度也最高,與中原關系也最為緊密。由于侵蝕吞并遼東,地跨鴨綠江,使高句麗成為多民族國家,境內除統治民族高句麗人外,還有大量被征服的漢人、鮮卑人、契丹人、靺鞨人及新羅、百濟人等。南北朝時高句麗頻繁通使于中國,光派往東晉南朝貢獻方物的使團就有30多次。劉宋元嘉十六年(439),一次就由海路貢獻戰馬800匹。派往北朝的使團更多達90余次,有時一年派兩三次。另外,中原人為避亂逃亡到高句麗的也很多,給半島帶去農耕技術和思想宗教文化。高句麗很早就接受了儒家思想,國都平壤設有太學。約公元4世紀佛教也由中原前秦王朝傳入高句麗,并再南傳入百濟、新羅和倭國。
百濟與新羅也分別向南北朝遣使朝貢,學習中國文化,百濟更成為中國文明東傳日本的孔道。新羅則設置郡縣,其文字、甲兵一同于中國。南朝陳時有新羅僧玄光法師,從天臺宗三祖南岳慧思學習法華經,同智顗一起名列南岳門下28大弟子之一。[7]玄光學成回國授徒,門下弟子也不少。隋朝時,又有高句麗釋波若,于開皇十六(596)入天臺山從智顗學天臺宗教義,“以神異聞”,但學成后沒有回國。[8]朝鮮半島與日本各國也派遣留學生、學問僧來隋朝學習,他們“好尚經述,愛樂文史,游學于京都者,往來繼路,或亡不歸”。[9]隋煬帝為此在鴻臚寺專門設館,聘請名僧,“教授三韓”,[10]“訓開三韓方士”[11]。隋文士杜正蕆所著《文章體式》被學人號為“文軌”,傳入高句麗、百濟,“亦共傳習,稱為杜家新書”[12]。中華文化不斷地向東北亞諸國傳布,到隋唐時已形成與漢字為載體的東亞文化圈。
但朝鮮半島諸國的矛盾沖突一直很激烈。公元5世紀時,高句麗聯合新羅,百濟聯合倭國,在半島曾進行了長時間的爭霸戰,倭國曾派兵渡海,以任那國為據點,與百濟組成聯軍向北推進,結果被高句麗好大王擊敗。公元562年,新羅吞并了任那,將日本勢力逐出了朝鮮半島。高句麗的勢力推進到半島南部,進一步統一半島也就提上了議事日程,為此又與新羅交惡[13]。高句麗甚至想西聯東突厥,與東突厥劃分勢力范圍,以安撫西北契丹、靺鞨之眾。高句麗在成為東北亞最為繁盛強大國家的同時,也處于各種矛盾的中心。
中國南北朝分裂對峙時,朝鮮半島也三國鼎立,各國都結交與國來牽制敵手,利用各種機會建立自己的霸權。時南朝文化優于北朝,故百濟、新羅及倭國多往南朝朝貢。高句麗與北朝接壤,故向北朝朝貢多,但也常渡海通使南朝,北魏曾多次在海上擒獲高句麗派往南朝的使者,但除詔書責讓外,并不能阻止高句麗向南朝朝貢。南朝亦有意與高句麗、百濟往來,用以牽制北朝。高句麗曾阻止百濟與北朝通使,為此百濟曾請求北魏攻打高句麗,遭拒絕。其時的中國南北朝統治者和朝鮮半島對立三方都希望對方長久的分裂,以求自已的發展與安穩。而隋統一中國,必然打破幾百年來的東北亞地緣政治秩序。
二、句麗謀求地區霸權及其與隋朝的政治沖突
高句麗立國五百年來一直在四面拓土擴張,隋時高句麗北面的靺鞨有7大部落,各有酋長,不相統一,常遣使朝貢中原,并南下侵寇高句麗。高句麗王征討不過想招撫他們,但力不從心。高句麗西面的契丹、奚、霫和西北面的室韋等游牧民族也互為雄長,難以馴服。其中契丹有8大部落,而以大賀氏最強,《遼史·太祖紀》追溯契丹先世出自炎帝,但現代語言學已確認炎黃子孫的漢族屬漢蕆語系,從語源上看與東北亞及蒙古草原各族阿爾泰語系民族并無語族親緣關系,所以契丹自封炎帝之后只是自吹而不確切。其時契丹的文明程度也較奚、霫諸部要低,最為“無禮頑囂”。與契丹同族類的室韋文明程度更低,民眾貧弱,分為5大部,不相總一。所有這些部族皆依附于東突厥,啟民可汗置官吐屯設總領他們,并得到隋朝的認可,高句麗對此當然很不高興。
高句麗謀求東北亞地區霸權的野心不僅使百濟、新羅恐慌,而且不見容于隋朝。隋建立后,東北亞諸國都關注中原局勢的發展,爭相朝貢,想借助隋天子的威權為自已謀取好處。如高句麗王湯在北周武帝掃滅北齊后即“遣使朝貢,武帝拜湯上開府、遼東郡公、遼東王”。至隋文帝“受禪,湯復遣使詣闕,進授大將軍,改封高麗王。歲遣使朝貢不絕”[14]。不甘落后的百濟王余昌也遣使朝貢,被封為“上開府、帶方郡公、百濟王”[15],與高麗王湯平起平坐。東北亞各民族也紛紛主動向隋貢獻方物,據《隋書·高祖紀上》:
開皇元年(581)秋七月庚午(二十三),靺鞨酋長貢方物。冬十月乙酉(初九),百濟王扶余昌遣使來賀,十二月壬寅(二十七),高麗王高陽遣使朝貢。
開皇二年(582)春正月辛未(二十七),高麗、百濟并遣使貢方物。十一月丙午(初六),高麗遣使貢方物。
開皇三年(583)春正月癸亥(二十四),高麗遣使來朝。五月甲辰(初七),高麗遣使來朝。五月丁未(初十),靺鞨貢方物,八月丁丑(十一日),靺鞨貢方物。
開皇四年(584)夏四月丁未(十六日),宴突厥、高麗、吐谷渾使者于大興殿。五月癸酉(十二日),契丹主莫賀弗遣使請降,拜大將軍。
開皇五年(585)夏四月甲午(初八),契丹主多彌遣使貢方物。
開皇初年高句麗幾乎每年都來朝貢,有時一年遣使二次,表現最為主動積極。但值得注意的是,百濟和高句麗同時也向江南的陳朝朝貢。史載陳后主至德二年(584)十一月戊寅(二十曰)和至德四年(586)九月丁未(三十日),百濟國兩次遣使向陳獻方物。至德三年(585)十二月癸卯(二十一日),高麗國遣使向陳獻方物[16]。高句麗和百濟在交接隋朝的同時沒有中斷與南朝的交往,并在交往中互通情報,同時根據各自的利害,尋找戰略伙伴。
隋文帝時對四夷的方針是息事寧人。其時敗亡的北齊宗室高保寧據有營州(今遼寧朝陽市),連結契丹、靺鞨興兵反隋,文帝“以中原多故,未遑進討,以書喻之”[17]。契丹與靺鞨互相劫掠,文帝與來朝的靺鞨使者說:“我憐契丹與爾無異,宜各守土壤,豈不安樂?何為輒相攻擊,甚乖我意”。但文帝君臨天下為四夷主的立場也是堅定的,稱:“朕視爾等如子,爾等宜敬朕如父”[18]。時隋對外主要敵手為突厥和陳朝。值得注意的是,開皇九年(589)滅陳后,高句麗等國的朝貢使者與隋的往來斷絕了好幾年。特別是高麗王湯聞陳亡,“大懼,治兵積谷,為守拒之策”[19]。南朝與北朝漢晉時本為一家,遼東在漢晉時也為中國統轄,隋滅陳統一中國,原亦為中國郡縣的高句麗自然感到震恐,高麗王預感到隋兵鋒將轉向自已,于是開始了備戰[20]。
隋臣中最早提議滅高句麗的為吳人陸知命,他曾直詣朝闕上表,請求出使高句麗,說:“陛下當百代之末,膺千載之期,四海廓清,三邊底定。唯高麗小豎,狼顧燕垂,王度含弘,每懷遵養者,良由惡殺好生,欲諭之以德也。臣請以一節,宣示皇風,使彼君面縛闕下”[21]。隋文帝雖沒有派陸知命出使高句麗,但對他的言論是贊賞的。
直到開皇十一年(591)春正月辛丑(十八日),高句麗才又遣使入隋朝貢,五月,高句麗又遣使貢方物,恢復了與隋朝的朝貢關系。這年高句麗來朝兩次,但以后就很少來了,與開皇初“頻有使入朝”的情況判若兩人。同年十二月丙辰(初九),有靺鞨遣使貢方物。開皇十二年(952)十二月,靺鞨又遣使貢方物。十三年(593)春正月丙午(初五),契丹、奚、霫、室韋并遣使貢方物,其中契丹在開皇十年(590)十一月丙午(二十二)亦曾朝貢一次。十三年七月戊申(初十),靺鞨遣使貢方物[22]。開皇十四年(594),新羅遣使貢方物,隋文帝拜新羅王金真平為“上開府、東浪郡公、新羅王”[23]。隋統一后東夷各族都來朝貢,以靺鞨最為積極,高句麗來得顯然少了。直到開皇十七年(597)五月己巳(二十三),高句麗才又一次遣使貢方物[24]。說明隋與高句麗的關系已呈緊張。
隋文帝既對東夷采取懷柔政策,所以始終沒有主動出擊征討各部,時韋沖任營州總管,“懷撫靺鞨、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霫畏懼,朝貢相續”[25]。對于高句麗的治兵積谷拒隋舉動,文帝派出使團往高句麗“撫慰”,美其名曰:“欲問彼人情,教彼政術”,實際上是進行偵察。但高麗王卻將隋使置之“空館”,“嚴加防守,使其閉目塞耳,永無聞見”[26]。開皇十七年(597),文帝給高麗王湯修璽書一封加以責備。高麗王湯收到隋文帝的璽書惶恐萬分,將奉表謝罪,卻因病謝世。太子高元嗣立,文帝又冊封高元襲爵遼東郡公,高元奉表謝罪,請求封王,文帝又再冊高元為高麗王[27]。
但史載開皇十八年(598)高元竟率靺鞨之眾萬余騎入寇遼西,被隋營州總管韋沖擊退[28]。隋未先擊高句麗,高句麗何以敢先舉兵侵隋?這件事頗值得思量,高元恐怕不致如此魯莽。據史書記載,有原依附于高句麗的“契丹別部出伏等背高麗,率眾內附,高祖納之,安置于渴奚那頡之北”[29]。看來,高句麗率靺鞨之眾討擊背己入塞依附隋朝的契丹,而不是侵犯隋疆,才是事實的真相,這反映了高句麗試圖讓契丹、靺鞨之眾依附于已,雖未敢冒犯隋廷,但其追求東北亞地方霸權的野心與隋朝利益發生了沖突。高元追擊契丹不僅入侵了隋邊疆,而且違背了文帝“自化爾藩,勿忤他國”的訓示。為此,開皇十八年(598)六月丙寅(二十七),文帝下詔黜高麗王元官爵,大興問罪之師,命漢王楊諒為元帥,宰相高颎為元帥長史,總領水陸二路30萬大軍討伐高句麗。由于準備不足,王師不振,損失慘重,而高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于是罷兵,隋恢復對高元的冊封,高句麗也恢復了對隋的朝貢。
隋還曾聯絡百濟國夾擊高句麗,百濟王昌也“遣使奉表,請為軍導”。但戰事很快結束,文帝乃下詔給昌:“往歲為高麗不供職貢,無人臣禮,故命將討之。高元君臣恐懼,畏服歸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隋與百濟陸地上不接壤,關系處理得好一些,平陳之役,隋有一艘戰船飄至海東聃牟羅國(今濟州島),被送到百濟,百濟王昌資送他們回國,并遣使奉表祝賀隋平陳成功,受到文帝褒揚,其情形與高句麗正好相反。但高句麗得知百濟與隋的這些交往,即“以兵侵掠其境”[30],使聽命于隋的百濟國蒙受了損失。
開皇二十年(600)正月辛酉(初一),突厥、高麗、契丹并遣使貢方物,時契丹別部又背突厥降于隋,文帝“悉令給糧還本,敕突厥撫納之”。這表明隋文帝對邊境四夷的政策始終還是安境保民。到隋煬帝即位,國家殷富強盛,朝野皆以遼東為意,唯獨劉炫以為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已是絕無僅有的少數派。
隋文帝晚年和煬帝大業初年何以朝野皆以遼東為意呢?
從地緣政治來看,高句麗立國己五百多年,在東北亞局部地區己建立了霸權,百濟、新羅不能抗衡,倭國的干涉也被擊退,靺鞨、室韋俯首稱臣,契丹雖叛附不一,亦不能興風作浪,特別是高句麗西聯突厥,又曾南結陳朝,在東北邊境出現了俯瞰中華的態勢。一旦中原有亂,則有如后來的與高句麗有血親關系的滿洲女真人,入關滅明席卷中原易如反掌,其勢真可謂“狼顧燕垂”,虎視眈眈。所以大業三年(607)隋煬帝在塞外突厥啟民可汗牙帳見到高句麗使者,即引起了警覺。更何況隋煬帝的對外政策顧問裴矩所謂:“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為郡縣,今乃不臣,別為異域”。孰不可忍。而當大業全盛之時,“安可不取?使冠帶之境,遂為蠻貊之鄉乎”[31]?其時隋的北方勁敵東、西突厥均己俯首帖耳徹底臣服,西突厥處羅可汗親詣長安朝貢,煬帝對他說:“譬如天上止有一個日照臨,莫不寧帖;若有兩三個日,萬物何以得安”?[32]隋不能容忍東北邊境強大的高句麗獨立存在,正如其不能容忍北境蒙古草原上強大的突厥政權一樣,突厥已破,兵鋒自然轉向了高句麗,而且成為隋唐百年來對外征服戰爭的焦點,高句麗不亡,征戰不斷。
三、隋煬帝夸示四夷耀武征遼大擺儀仗
如何變高句麗“蠻貊之鄉”為隋朝的“冠帶之境”呢?早在大業三年(607)突厥啟民可汗帳前,裴矩就曾為隋煬帝策劃并獻計:“今其使者朝于突厥,親見啟民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后伏之先亡,脅令入朝,當可致也”。裴矩以為其事易如反掌,在國力較高句麗更強大的突厥都“合國從化”的情勢下,只需讓其目睹了這一文物盛事的使者回國向高麗王傳話,“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33]。似乎只須恫嚇利誘,高元即會象東、西突厥可汗啟民、處羅及高昌王麴伯雅那樣親自詣闕朝拜。隋煬帝當即采納了裴矩的意見,下令征高麗王元入朝。然而,高元懼,“藩禮頗闕”,不但不入朝貢獻,反而斷絕了朝貢使者,干脆不與隋朝往來。
這當然讓隋煬帝大失面子,使天子龍顏震怒,被激怒了的煬帝當即下定了征討高句麗的決心。大業四年(608)元月,煬帝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余萬開永濟渠,顯然就是為征討高句麗作準備。《隋書·閻毗傳》記閻毗“以母憂去職,未期,起令視事。將興遼東之役,自洛口開渠,達于涿郡,以通運漕,毗督其役”。同書《五行志下》記這年太原廄馬死者大半,煬帝令巫者視之,“巫者知帝將有遼東之役,因希旨言曰:‘先帝令揚素、史萬歲取之,將鬼兵以伐遼東也’。煬帝大悅,因釋牧馬者”。這是正史中有關煬帝征遼的最早信息。
永濟渠北通涿郡(治今北京市),隋煬帝宣布聲討高句麗及發兵的地點,都在涿郡,永濟渠的開鑿,有利于隋征調全國兵力及運送全國物資到涿郡。隋煬帝既在大業五年(609)將吐谷渾納入隋郡縣體系中,將高句麗重新歸入王朝版圖當然己在他的通盤考慮之中。他先巡江都,作軍事調度,然后沿大運河直達涿郡,正式總動員令隨即下達了。《資治通鑒》記當時的軍事動員和人員調動情況云:
(大業七年二月)壬午,下詔討高麗。敕幽州總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夏四月庚午,車駕至涿郡之臨朔宮,文武從官九品以上,并令給宅安置。于是,詔總天下兵,無問遠近,俱會于涿。又發江淮以南水手一萬人,弩手三萬人,嶺南排[]手三萬人,于是四遠奔赴如流。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供載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秋七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艫相次千余里,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填咽于道,晝夜不絕,死者相枕,臭穢盈路,天下騷動。[34]
征調范圍遍及全國,其動員人數之眾,規模之大,遠遠超過開皇九年(589)平陳之役,可以說是“掃地為兵”。仗還沒打,已經搞得天下騷然。
由于頻興工役,大業五年(609)的大索貌閱雖搜括出大批人口,但仍感人役不夠,有“總持菩薩”法號的隋煬帝這時甚至打起佛教寺院的主意。據唐人高臨《冥報記》記載:“大業五年,奉敕融并寺塔”。釋家史料記載了隋煬帝詔天下僧徒無德業者并令罷廢的詔令,拆毀寺院,沙汰僧尼,用于充工役,充實國用[35]。直到大業七年(611),裁汰僧尼的命令仍在全國推行。據《隋書·王文同傳》:“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齋戒菜食者,以為妖妄,皆收系獄。比至河間,求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為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為聚結惑眾,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童女者數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于路”。王文同敢于“收系沙門”,“裸僧尼”,肯定是有上方的指示,但做過了頭,民憤極大,被隋煬帝斬首,成為替罪羊。
大量裁汰僧尼也有可能引起社會不穩,為防止有人利用佛教聚眾鬧事,隋煬帝又將天臺宗智者大師上首弟子灌頂召到涿郡,“遠至行所,引見天宸,敘以同學之歡”[36]。煬帝還專門派遣員外郎崔鳳舉將道士王遠知請到涿郡臨朔宮,親執弟子之禮[37]。隨即,煬帝令跟隋著他的大批佛、道人士在涿郡擺起了四道場,為征人祈福,用以安撫人心。
隋煬帝還把鼓吹、樂隊帶到了臨朔宮,在江都的各國朝貢使者也都來到涿郡,其中還有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設、吐谷渾王太子順等。大業七年(611)十二月已未(初八),西突厥處羅可汗也來到臨朔宮朝見,煬帝“備設天下珍羞,盛陳女擲,羅綺絲竹,眩耀耳目”,舉辦了盛大的歌舞宴會。由于隋煬帝對征遼勝利充滿信心,招各國使者和藩屬君王隨軍,就是要耀武讓四夷領略大隋天子的威風,親眼看一看不事藩禮的高麗王元的下場,以收殺一儆百之效。
但讓人疑惑的是東突厥沒有遣使來也沒有如約派兵參戰,其時啟民可汗已死,其子始畢繼位,與隋的關系發生了變化。突厥騎兵善于在惡劣條件下作戰,此前隋將韋云起曾率東突厥騎兵征討契丹,大獲全勝,這次征討高句麗若得突厥騎兵相助,沿西遼河上游快速突擊,對高句麗將會是致命的打擊,在塞外廣漠天寒地凍環境下作戰,突厥騎兵的戰斗力無疑優于隋朝府兵。但三次征遼竟未見東突厥以一兵一卒相助,這當然是大問題。時始畢可汗雖仍受隋冊封,但關系己疏遠,大業五年(609)始畢就沒有如約派兵協助隋軍西攻伊吾鐵勒軍。年輕的始畢可汗看到隋煬帝正著力扶植西突厥處羅可汗,對隋離強合弱伎倆已有警惕。另外高句麗既與東突厥通使,雙方面對強隋在戰略上共同利益更多,實際上是唇亡齒寒的關系。始畢可汗從自身的切身利益出發,嚴兵不動,坐山觀虎斗,這當然是對隋煬帝的不恭,但煬帝也暫且不能處置。
隋煬帝不能得到突厥騎兵助力,僅能邀得靺鞨渠帥度地稽所部有限人馬從征,度地稽雖“每有戰功”,但力量太小于大局無關輕重。在這場戰爭中,外藩諸夷多考慮自身利益,大多都只是作為觀眾。高句麗的世仇百濟可謂是隋的天然戰略伙伴,百濟王余璋,對夾擊高句麗也很有積極性,大業三年(607)就曾主動遣使請求征討高句麗,煬帝令他“覘高麗動靜”。但百濟是小國,開皇十八年(598)貿然進兵不但沒有撈到好處,反而在隋師敗績后遭到高句麗報服,當然要吸取教訓,且余璋也深知高句麗若滅亡了下一個就會輪到自已,不如保持現狀于己更為有利,于是鼠首兩端,暗中與高句麗通款,反例“挾詐以窺中國”。大業七年(611),百濟王余璋又假惺惺地遣使問隋煬帝征高麗的行期,實際上是為高句麗探聽軍事情報。蒙在鼓里的隋煬帝反而“大悅,厚加賞賜,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與相知”[38]。翌年隋大軍渡遼,余璋也集兵邊邊境,聲言助隋,但實際上按兵不動,沒有給隋軍絲毫相助。
然而,雖然沒有外援,隋煬帝卻并不在乎。高句麗蕞爾小國,隋傾全國之力,以大擊小,必將勢如破竹。隋煬帝對勝利有絕對的自信,認為只要隋大軍齊集,嚇也會嚇得高麗王屈膝投降。同時,隋煬帝也有意向包括東突厥、倭國等不馴服者在內的四夷顯示力量。征遼之役與其說是征討高句麗,不如說是殺雞給猴子看,在擊滅高句麗的同時,煬帝要一舉威服四夷,建立大隋天子為中心的天下朝貢體制。
也正因為如此,隋煬帝進行了超乎尋常的軍事調動。煬帝的期望值很高,試圖通過充分顯示大隋國力,調集龐大軍力來威嚇高麗王,“脅令入朝”,以期不戰而屈人之兵,迫使高句麗王就范。大業七年(611)夏秋之際山東河南發生大水災,漂沒30余郡,但這并沒有改變隋煬帝討伐高句麗的決心,大規模集兵繼續進行,煬帝并決定御駕親征。
按照古禮,巡狩親征有造廟致祭之禮,據《隋書·禮儀志三·軍禮》記載:“大業七年(611)征遼東,煬帝遣諸將于薊城南桑干河上,筑社稷二壇。設方墻,行宜社禮。帝齋于臨朔宮懷荒殿,預告官及侍從,各齋于其所。十二衛士并齋,鄣袞冕玉輅,備法駕。禮畢,御金輅,服通天冠,還宮。又于宮南類上帝,積柴于燎壇,設高祖位于東方。帝服大裘以冕,乘玉輅,祭奠玉帛,并如宜社。諸軍受胙畢,帝就位,觀燎,乃出。又于薊城北設壇,祭馬祖于其上,亦有燎”。隋煬帝的御駕親征大講排場,軍禮儀式如此隆重,各國使節及諸藩王駐足觀看,其實就是向四夷發出警告,不向大隋天子低頭是絕無好下場的。對于隋煬帝來講,這場戰爭只能嬴不能輸,也只會贏不會輸,煬帝本人對取勝沒有半點懷疑,所以不僅御駕親征,而且帶上各國使者前往觀摩。
大業八年(612)正月辛巳(初一),從全國各地調集來的征討大軍齊集涿郡(治今北京市),總計達1133800人,號稱200萬。這么多軍隊在遼東一隅其實無法展開,也用不著,反倒徒然增加了后勤饋運的困難。饋運者“填咽于道,晝夜不絕”,供輸軍糧等物資,其數比軍隊還要多。隋煬帝親征還帶著后妃宮女、公卿百官及僧尼道士、儀衛鼓吹等,這架式那象是去打仗,簡直是在演戲。煬帝只期望以大軍壓境而令高麗王膽寒,以求不戰而勝[39],其實并沒有認真從軍事上仔細研討戰略出軍戰術。
也有人對如此興師動眾而又滑稽的征討提出異議,出來諫止。如右尚方署監事耿詢隨車駕至涿郡時,即上書稱:“遼東不可討,師必無功”。煬帝得書大怒,要將耿詢問斬,幸何稠苦諫才得免[40]。給事中許善心也上封事諫煬帝不必御戎東討,結果也“忤旨免官”[41]。術士庾質被召到臨渝宮(今河北撫寧縣境)行在所,問以吉兇,煬帝問:“朕承先旨,親事高麗,度其土地人民,才當我一郡,卿以為克不?”庾質回答:“以臣管窺,伐之可克,切有愚見,不愿陛下親行”。煬帝對庾質勸導不必御駕親征很不高興,板起臉孔說:“朕今總兵至此,豈可見賊而自退也!”庾質于是分析說:“陛下若行,慮損軍威。臣猶愿安駕住此,命驍將勇士指授規模,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42]。其所分折可謂切中時弊,很有道理,但頭腦發熱的煬帝根本聽不進。
隋煬帝任命兵部尚書段文振為前敵總指揮,從軍事指揮員的角度,段文振也同意庾質“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的戰略思想,而不同意隋煬帝的耀武威嚇戰術。他在其后出師途中遇疾,上表煬帝分析征戰的天時地利人和說:
竊見遼東小丑,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百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心懷背叛,詭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愿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余城自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為艱阻,兵糧又竭,強敵在前,靺鞨出后,遲疑不決,非上策也。[43]
段文振的分析可謂極具遠見,遼東地處塞外北方高寒地帶,冬季嚴寒無法出兵,從時間上講只有半年用兵時間,且夏季多雨,道路泥濘,行軍住宿扎營很不便,加上路途遙遠,以牛車人力車運送軍需十分困難,軍隊越多后勤越困難,若不速戰速決則自已就會陷于被動。開皇十八年(598)楊諒出師就因天時不利,“霖潦疾疫”,“饋運不繼,六軍乏食”,30萬大軍尚未接戰即自行潰散,是為前車之鑒。對此,陳寅恪先生有獨到分析:“中國東北方冀遼之間雨季在舊歷六、七月間,而舊歷八、九月又為寒凍之時期,故以關中遠距離之武力而欲制服高麗攻取遼東之地,必在凍期已過雨季未臨之短時間獲得全勝而后可。否則,雨潦泥濘冰雪寒凍皆于軍隊士馬之進攻糇糧之輸運已甚感困難,茍遇一堅持久守之勁敵,必致無功或覆敗之禍”[44]。由于天時地利不在隋一方,人海戰術派不上用場,人再多也斗不過老天爺,所以段文振認為宜出奇兵,星馳速發,水陸俱進,直取平壤。可惜段文振在行軍途中病故,未能肩負起前敵總指揮的責任,實際最高指揮者正是不顧天時地利人和頭腦發昏的隋煬帝本人。
隋煬帝根本沒有認真考慮戰役的戰術問題,在完成了一切調動之后,于大業八年(612)正月壬午(初二)正式下詔宣布討伐高句麗,詔文直把高句麗王高元稱之為“小丑”,輕蔑憤怒地聲討高元罪狀,指斥高元不修職貢,無事君之心,無為臣之禮,掩匿懷奸,招納亡叛,穿著靺鞨的衣服侵擾遼西,這些內容和開皇十八年(598)文帝詔責高元差不多。值得注意的是詔文后半部指責高元內政不修,法令苛酷,賦斂煩重,百姓愁苦,冤枉莫申,則和當年討陳檄文差不多。暴虐者不堪為國主,煬帝于是有理由協從天意,拯民于水火,“取亂覆昏”,親總六師進行討伐[45]。這就把隋軍變成了王者正義之師。隋煬帝甚至把自已比作商效問罪的周武王姬發,成文王之志滅商紂,圣王當然要承先帝之志滅高句麗,“二代承基,志包宇宙”[46]。
隋煬帝的詔文是寫給高句麗看的,也是寫給四夷各國看的。為了揚威張大聲勢,詔文甚至公開了用兵作戰部署,隋百萬大軍分成左右兩翼,每翼又分為12路軍,共24路,各路軍隊都要“先奉廟略,駱驛引途,總集平壤”。詔文云:“今宜授律啟行,三令五申,必勝而后戰。左第一軍可鏤方道、第二軍可長岑道,第三軍可海冥道,第四軍可蓋馬道,第五軍可建安道,第六軍可南蘇道,第七軍可遼東道,第八軍可玄菟道,第九軍可扶余道,第十軍可朝鮮道,第十一軍可沃沮道,第十二軍可樂浪道。右第一軍可黏蟬道,第二軍可含資道,第三軍可深彌道,第四軍可臨屯道,第五軍可侯城道,第六軍可提奚道,第七軍可踏頓道,第八軍可肅慎道,第九軍可碣石道,第十軍可東暆道,第十一軍可帶方道,第十二軍可襄平道”。24路軍全面展開,鋪天蓋地,但明眼人一看就知無法展開于24道上,各道相隔遙遠,根本沒有24條路可走,完全是紙上談兵,虛張聲勢。詔文吹噓隋大軍為百戰百勝之雄師,“顧眄則山岳傾頹,叱咤則風云騰郁”。且煬帝“躬馭元戎”,總其節度,控弦待發,摧枯拉朽,似乎一口就可將高句麗吞下肚子里。煬帝還要“解倒懸于避裔,問疾苦于遺黎”[47],建立圣王可汗的不朽功業。
詔文最后稱:“王者之師,義存止殺,圣人之教,必也勝殘”,“若高元泥首轅門,自歸司寇,即宜解縛焚梓,引之以恩,其余臣民歸朝奉順,咸加慰撫,各安生業,隋才任用,無隔夷夏”。隋煬帝不是立足于打,而是立足于撫,百萬大軍首先考慮的不是進擊殲敵,而是先考慮如何接受敵人投降。因為在隋煬帝看來,面對如此強大的“圣王之師”,高麗小丑根本不敢負隅頑抗,投降是高句麗的唯一出路。于是乎隋煬帝又要求各路隋軍,“營壘所次,務在整肅,芻蕘有禁,秋毫勿犯,布以恩宥,喻以禍福”,而“若其同惡相濟,抗拒官軍,國有常刑,俾無遺類,明加曉示,黎朕意焉”[48]。隋煬帝全盤公開軍事部署,根本不關注也不講究取勝的軍事戰略戰術,而是強調義師形象。作為總指揮,隋煬帝導演了世界軍事史上前所未有的出師儀式。
一月癸未(初三),隋征討大軍的第一軍出發,隋煬帝根本不考慮快速進軍,出其不意,而是大講排場,要求步履齊整,“每天遣一軍發,每軍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24天才使兩翼24路軍開跋干盡,結果是排成了一條長蛇陣,當然也不會有什么戰斗沖擊力。隋各路軍“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亙九百六十里”,24路軍之后又有“天子六軍”次發,前后相置“又亙八十里,通諸道合三十軍,亙一千四十里”。煬帝又令諸軍以帛為帶,長尺5十,闊2寸,題其軍號為記。御營內者,合十二衛、三臺、五省、九寺,并分隸內、外、前、后、左、右六軍,亦各題其軍號,不得自言臺省。王公以下,至于兵丁廝隸,悉以帛為帶,綴于衣領,名“軍紀帶”[49]。這樣,光大軍出發儀式就用了40天,百萬大軍,整齊劃一,秩序井然,“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50]。然而,這那里是去打仗,簡直就是武裝大游行,是一次規模宏大的軍事大檢閱。
更有甚者,連綿千里的長蛇陣皆由隋煬帝“親授節度”,每軍設大將、亞將各1人。騎兵40隊,每隊百人置一纛,10隊為團,團設偏將1人,并有儀仗隊,“前部鼓吹一部,大鼓、小鼓及鼙、長鳴、中鳴等各十八具,棡鼓、金鉦各二具。后部鐃吹一部,鐃二面,歌簫及笳各四具,節鼓一面,吳吹篳篥,橫笛各四具,大角十八具”。[51]帶這么多笨重的鼓吹樂器是干什么?當然不是為了打仗,這和隋煬帝即位之初下江南在江都制羽儀大陳文物,大業五年(609)煬帝西巡在河西大擺魚龍漫延之樂,是同樣意思同一招式,即要用中華禮樂文明感召威服東夷,征討不如說是巡狩。
由于根本沒有立足于打,隋煬帝沒有設想這會是一場惡仗,不是費心思去考慮如何克敵致勝的戰術,卻十分注重禮儀排場,當大軍行至望海樓(今遼寧遼西縣境),煬帝又于禿黎山設壇,祀黃帝,行禡祭,設軒轅神座,煬帝與諸預祭臣侍侍諸軍將,皆齋一宿[52]。由于輕敵,煬帝甚至允許主將宇文述以婦人“家累”自隨[53]。蘇威年老,上表乞骸骨,想退休,煬帝不許,讓他以本官領左武衛大將軍從征[54]。二月甲寅(初四),煬帝又下詔:“朕觀風燕裔,問罪遼濱,文武協力,爪牙思奮,莫不執銳勤王,舍家從役”,表彰從征官兵,并令郡縣存問從征士兵家,使行役無后顧之憂[55]。
三月癸巳(十四曰),隋煬帝來到前線,因怕軍將貪功出擊,令各路軍主帥有事皆須稟報,諸將互相牽制,不設統帥,不許擅自揮師挺進。煬帝自以為高句麗臣民見到隋軍盛大架式必將自動瓦解投降,因此在每軍設“受降者一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制,戰時為監軍”[56]。如左驍衛長史游元即為蓋平道監軍[57]。仗還沒打,隋煬帝先把自已的軍隊捆住了手足。為防止百萬大軍中有人開小差,各軍并發給幡旗數百,有事往回走者要執幡而行,無幡而擅離本軍者斬。
四、御駕親征第一次渡遼征討及隋師潰敗
大業八年(612)三月甲午(十五日),隋煬帝率領征討大軍經過兩個月的行軍,齊集遼河邊,雖聲勢甚盛,但高句麗上下卻未見投降者,而是阻水拒守。“小國懼亡,敢同困獸”,高元“掃境內兵以拒之”[58],高句麗軍民同仇敵愾,將隋師擋在遼河以西。
隋煬帝來到遼河旁,令工部尚書宇文愷造浮橋三道,但橋短不及岸丈余,高句麗軍前來騷擾,隋軍赴水接戰,高句麗兵在岸上乘高射殺,隋兵無法登岸。只見右屯衛大將軍江南人麥鐵杖請為先鋒,跳上東岸與高句麗軍博戰,因接濟不上,與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叉皆戰死。隋煬帝在河西岸駐足觀戰,親眼看到麥鐵杖等戰死的慘景,為之流涕。“圣人可汗”這才體驗到了戰爭的殘酷。煬帝為戰沒者舉辦了隆重的葬禮[59],麥鐵杖的死乃征遼第一仗,雖僅為一次小接觸,但隋軍出師不利,損兵折將。
隋煬帝又令何稠繼續造橋,兩天后橋造成,大軍蜂擁渡過遼河,大戰于遼河東岸,高句麗軍大敗,死者萬余。隋諸路軍乘勝圍遼東城(今遼寧省遼陽市),即漢時的襄平城。隋煬帝車駕也渡過遼河,并引西突厥曷娑那可汗(即處羅)和高昌王麴伯雅、吐谷渾太子順等以及西域、南洋各國使者前往觀戰,“以懾憚之”[60]。
何稠又為隋煬帝制造了行殿和六合城,與高句麗遼東城相對而立。六合城造于夜中,“周圍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又四隅有闕,面別一觀,觀下開三門。其中施行殿,殿仙上容侍臣及三衛仗,合六百人”。這么大的工程僅一夜間就完成,諸夷使者雖親眼所見卻不敢相信。天亮之時,高句麗人遠遠望去,忽見一座城樓從天而降,大為驚駭,“謂若神功”[61]。但這也并沒有動搖高句麗軍民抵抗的決心。
遼河東岸作戰的一時勝利令隋煬帝興奮萬分,特下詔大赦天下,命刑部尚書衛文升、尚書右丞劉士龍撫慰遼左之民,給復10年,并在占領區建置郡縣,以相統攝。四月丙子(二十七),隋煬帝駐蹕臨海頓(今遼寧省遼西縣渤海邊)。見到兩只大鳥翱翔天空,即令侍臣刻石記功,自已詩興大發作《望海詩》及《紀遼東二首》[62]。緊張的征戰之余有如此詩興,不是畏懼戰事的殘酷,而是觸景詩意昂然,顯示此刻的隋煬帝心情輕松,對戰勝充滿信心。
但隋師渡遼后高句麗仍未見投降,這倒是煬帝萬萬沒有料到的!下一講該如何進討,煬帝心中并沒有計劃,也沒有作戰方案。五月,煬帝令隋軍水陸并進。水路由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為總管,周法尚為副總管,率江淮水軍,舳艫數百里,浮海先進,入涀水(今朝鮮大同江)。陸路諸將也分路齊頭并進,長驅直赴高句麗都城平壤,煬帝僅留樊子蓋在身邊宿衛。然而即使大軍已展開了攻勢,隋煬帝仍怕諸將深入敵境后貪功擅戰,破壞他的招降部署,又下詔告誡:“今者吊民伐罪,非為功名。諸將或不識朕意,欲輕兵掩襲,孤軍獨斗,立一身之后名以邀勛賞,非大軍行法。公等進軍,當分為三道,有所攻擊,必三道相知,毋得輕軍獨進,以致失己。又,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毋得專擅”[63]。于是乎諸將各奉詔旨,互相監督,不敢赴機,高句麗軍民據城堅守,使隋軍進展緩慢,遼東城亦圍攻了數月不能攻下。
隋煬帝一時火氣,令隋軍猛攻遼東城,但同時又敕諸將:高句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在實施打擊的同時,仍未拋棄招降的幼想。結果,隋軍進圍遼東城,眼看就要拿下,高句麗人即詐稱請降,因有煬帝明旨在先,諸將不敢再攻,只能馳奏于煬帝請旨,待報批準回來,城中已重新調整好城防,繼續頑抗。“如此再三,帝終不悟”,坐失戰機,空勞將士血汗,卻始終未能將遼東城攻下。
來護兒率水軍溯涀水而上,來到平壤以西60里,與高句麗軍相遇。來護兒派其第六子來整和武賁郎將費青奴出擊,大破敵軍。小勝后來護兒卻輕敵,不聽副總管周法尚的勸阻,違背事先約定的“俟諸軍至俱進”的旨令,挑選精甲4萬人,乘勝直赴平壤城下。高句麗伏兵于城內郭內寺中,出兵與來護兒戰佯敗,誘隋軍入城。隋軍入城后縱兵大掠,無復部伍,高麗王弟高建武率伏兵乘亂出擊,大破隋軍,來護兒僥幸逃脫,生還者不過數千人。高句麗軍追到涀水隋船隊前,周法尚嚴兵列陣拒戰,高句麗軍也不硬拼,即行退走。但來護兒經此一敗己不敢按原計劃留屯平壤城下接應陸軍,只好引兵還屯海邊。
陸上隋宇文述、于仲文、薛世雄、崔弘升等各路將軍攻遼東城不下,遂率軍繞過高句麗城池東進,會于鴨綠江西,試圖跨江南下直趨平壤,會合水軍翻動敵軍根本。但人多馬眾,后勤補給極為困難,高句麗堅壁清野,遠征軍需自負資糧。大軍由瀘河(今遼寧錦卅市)、懷遠(今遼寧遼陽西北)二鎮出發時,各路人馬皆給百日糧,還有排甲、槍矟等武器裝備,及帳篷衣服等,每個士兵負重在3石以上,長途跋涉,人馬皆不勝負荷。行軍時又立下軍令狀:“士卒有遺棄米粟者斬”。但實在背不動,士卒宿營時皆在帳篷內偷偷地掘坑,將糧食掩埋,以減輕行軍負擔,期望到高句麗境內能槍劫米麥受用。結果,大軍才行至中路,就快斷炊了。
隋軍有9路約30萬人渡過鴨綠江南下,兵出樂浪道的老將于仲文較有謀略,他率軍來到烏骨城(今遼寧鳳城縣),故意挑選羸馬驢數千置于軍后,自己率大軍向東進發,高句麗出兵掩襲后路輜重,于仲文揮師回擊,大破高句麗軍[64]。高麗王遣大臣乙支文德來到隋軍營帳前詐降,實為探聽軍情,由于隋煬帝大張旗鼓,以勢壓人,本無軍事機密可言,乙支文德是來查看隋進軍的決心及士氣的。高句麗也知道隋煬帝有投降者不殺的詔令,知道詐降不死必有功效,所以身為宰相的乙支文德也敢于來到隋軍大營,旁若無人。但是,隋煬帝也事先密向于仲文布置,“若遇高元及文德來降,必擒之”。于仲文想趁機逮捕乙支文德,但監軍的慰撫使尚書右丞劉士龍不知煬帝密旨,只知“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的明旨,乃出面制止了于仲文的企圖。宇文述等諸將也意見不一,當時9路軍也沒有一個統帥,沒有敢拍板負責任的,結果白白錯失了擒獲敵方主帥的機會。乙支文德被放走后,諸將反悔,派人追文德,說:“更有言議,可復來也”。孤身闖虎口的乙支文德哪里肯依,急速回營。于仲文和宇文述等放走了敵宰相,心里很不踏實,宇文述以糧盡欲退兵,于仲文則不甘心無功退還,議以精銳追擊文德,并沖著宇文述怒斥:“將軍仗十萬之眾,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他見諸將面有難色,又大吼:“仲文此行,固知無功,何則?古之良將能成功者,軍甲之事,決在一人,今人各有心,何以勝敵!”辭氣慷慨激昂,諸將亦為之動容,大家平起平坐,互不統轄,但于仲文敢負責,諸將也就不好意思撤退。宇文述雖知軍中糧食維持不了幾天,仍不得已而附從了于仲文。于是,隋諸軍將揮師渡過鴨綠江追擊乙支文德。乙支文德老謀深算,他在隋營己察看到士卒面有饑色,于是故意打疲勞戰,一有接觸便佯敗,引誘隋軍追擊,誘敵深入。結果一日七戰,隋軍皆捷,隋諸將于是放開腳步,恃勝長驅直入,東渡薩水(今清川江),追到距平壤城30里處,傍山扎營,但卻沒有見到應該來接應的來護兒水軍。
狡猾的乙支文德再次遣使來詐降,聲稱只要隋軍撤退,便奉高麗王高元前往隋煬帝駐蹕處朝見。宇文述等見士卒疲憊不堪,軍中已無糧草,來護兒水軍又未按期來接應,在高句麗之南面答應出兵北上夾擊的百濟軍隊也遲遲未發,而平壤城防險固,一時無法攻拔,于是即因高句麗使者口頭承諾的投降條件而退軍,算是不失體面的班師。
但隋軍撤退時,高句麗軍卻趁機四面抄襲,隋軍結成方陣且戰且退。乙支文德派人送于仲文等詩一首:“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勝功既高,知足愿云止”[65]。氣得于仲文等隋將嗷嗷叫。秋七月壬寅(二十四),隋軍退至薩水(今清川江),軍剛半渡,高句麗軍向后路發起總攻擊,饑餓無力的隋軍大潰,右屯衛將軍辛世雄戰死,各路軍將爭相逃命,不可抑止。落荒而逃的隋軍將士一日一夜狂跑了450里,真可謂一瀉千里!直到鴨綠江才站住腳。多虧殿后的將軍王仁恭、李景在后面拼命抵抗,高句麗兵才未窮追上來。猛將薛世雄軍在白石山被圍百余重,四面矢下如雨,薛世雄選200騎為敢死隊,縱擊沖鋒,破圍而還[66]。陸上諸軍惟衛文升一軍獨全。來護兒水軍聞陸軍潰敗,只好渡海回師。御駕親自指揮自的隋百萬大軍竟然無功大敗而還。
隋煬帝首征高句麗是徹底失敗了,而且是慘敗!當初渡過鴨綠江的隋9路軍共355000人,回到遼西的僅2700人,資儲器械巨萬計,也亡失殆盡。唯一的戰果是攻拔了遼河西岸的武厲邏(今遼寧法庫南),隋在此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已。其余則一敗涂地,一無所獲。隨駕出征的元老大臣也因病因累死了好幾個,除兵部尚書段文振外,還有工部尚書宇文愷、內史令元壽、司空觀德王楊雄也在隨駕途中病故,其弟納言楊達竟卒于師,煬帝嘆惜久之[67]。士兵死者,更不計其數,直到唐貞觀十九年(645),其戰場依然是“骸骨相望,遍于原野”[68]。
意想不到的慘敗令不可一世的隋煬帝羞愧難當,但他委過于領兵將領,下令將宇文述等鎖系引還。七月癸卯(二十五),下令班師。九月庚寅(十三)車駕回到東都(洛陽),煬帝即追究征遼失敗罪責,斬尚書右丞劉世龍以謝天下,敗將于仲文、宇文述“除名為民”,由監軍的游元任御史加以審訊,楊義臣等皆坐免官。來護兒“坐法受戮”,煬帝還欲盡誅其子,以解其恨,但未執行[69]。宇文述因與煬帝情深,又為兒女親家,雖系獄卻不忍加刑,不久釋放。諸將皆將敗績罪過諉之于于仲文,仲文憂憤發病而卒。[70]
隨駕的高昌王麴伯雅等眾多藩主和外國使節們都從頭至尾觀看了隋軍的潰敗,隋煬帝原想以征討高句麗耀武夸示四夷,但敗績讓他威風掃地,無地自容,回到東都后各國使者紛紛回國,這將使隋師敗績傳遍天下四方。當然隋煬帝仍百方籠絡,十一月己卯(初三),高昌王麴伯雅得尚隋宗女華容公主,啟程歸國。靺鞨渠帥度地稽亦因功“賞賜優厚”[71]。隋煬帝雖對四夷酋領百般籠絡,但“圣人可汗”紙老虎的面孔己被徹底戳穿。
五、掃地為兵第二次征討及國內叛亂
隋煬帝發動規模空前的征討高句麗戰爭遭到意外慘敗,更為嚴重的后果還是造成了國內政治失控和動亂。煬帝為耀武而“掃地為兵”,民眾則“苦于上欲無厭,下不堪命,饑寒交迫,救死萑蒲”[72]。沉重的兵徭役征使農民難以承受,一場反隋農民大起義揭開了序幕。早在大業五年(609)因開北運河永濟渠輸送征遼軍資,“丁男不供,始役婦人”,使逃役的“狂寇數萬”聚集長白山(今山東章丘、鄒平境)[73]。大業六年(610)雁門(今山西代縣)尉文通“聚眾三千,保于莫璧谷”。大業七年(611)征遼開始,青壯年幾乎全數就役。士兵從四遠奔赴如流,民工夫役往返饋運,填咽于道。而天公也不作美,十月山東、河南黃河大水決堤,人或為魚鱉,煬帝不加撫恤,仍加倍征發役夫軍糧,使“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生。于是始相聚為群盜”[75]。
隋煬帝在即位之后不顧子民死活虐用民力,要建立千古圣王偉大功業,一連串的工程大役如營東都、開馳道、筑長城、鑿運河、游江都等等,總計役民在3000萬人次以上,未得喘息又是三征高句麗,一役未消,一役又起,搞得田疇荒蕪,海內怨叛。征討高句麗之役成為規模宏大的隋末農民大起義的導火線。苛政猛于虎,急政狠如狼。農民起義首先爆發地就在遭受嚴重水災而兵役、徭役又最嚴重的山東地區。史稱“是歲,大旱,疫,人多死,山東尤甚”[76]。鄒平人王薄自稱“知世郎”,即自謂是通曉當今世事之人,編了一首《無向遼東浪死歌》,在民間傳唱:
長白山頭知世郎,純著紅羅錦背襠。
橫侵矟天半,輪刀耀日光。
上山吃獐鹿,下山食牛羊。
忽聞官軍至,提劍向前蕩。
譬如遼東死,斬頭何所傷。[77]
歌謠直接鼓動民眾不要去遼東為隋煬帝賣命,拿起刀槍造反,唱出了掙扎在死亡線上的廣大民眾的心聲。王薄和孟讓于是擁眾據長白山(今山東章丘東北),首先揭起了反隋煬帝暴政的大旗。
隨著隋煬帝百萬大軍在遼東前線的潰敗,國內抗役的農民起義更是所在蜂起,而尤以山東、河北地區為甚,官府莫能禁止。但輸紅了眼的隋煬帝竟不顧國內民眾的生存死活,也不顧農民赴死反抗的嚴重局勢,為挽回面子又要再次親征高句麗。大業九年(613)正月元旦剛過后初二,煬帝即令修遼東古城,以貯軍糧,并詔“征天下兵,募民為驍果,集于涿郡”[78]。驍果即驍勇果敢之士兵,與府兵不同。府兵是輪番宿衛的義務兵役制,驍果則是募兵制,向社會廣泛招募士兵。原府兵在高句麗前線死散大半,需要在義務兵之外招募更多的平民入伍,募兵取代府兵,隋兵制發生重大變化。
正月戊戌(二十三),隋煬帝宣布大赦天下,己亥(二十四),任命刑部尚書衛文升等輔佐皇孫代王楊侑留守長安,拜京兆內史,許以便宜從事。又詔恢復敗將宇文述等人的官爵,讓他們繼續從征將功補過。隋煬帝對再次出征決心很大,說:“高麗小虜,侮慢上國,今拔海移山,猶望克果,況此虜乎?”[79]恨不得將高句麗一口吞下。但是高句麗真的好吞嗎?滿朝大臣經上次潰敗均心存疑慮。左光祿大夫郭榮認為“中國疲弊,萬乘不宜屢動”,無須“親辱大駕以臨小寇”[80]。術士庾質也認為“陛下若親動萬乘,糜費實多”。眾臣多勸煬帝不必御駕親征,派一得力將領指揮即可。隋煬帝大為震怒,吼道:“我自行尚不能克,直遣人去,豈有成功也”[81]。煬帝自視甚高,聽不進任何勸告,上次潰敗在沒有立足于真打,這次將毫不手軟出擊,又何能不勝?于是,一切仍按他的個人意志行事。
三月戊寅(十六日)煬帝自東都洛陽啟程,任民部尚書樊子蓋等輔佐皇孫越王楊侗留守東都,安排好一切內政后,乃率后妃百官和大隊人馬兼程北上。夏四月庚午(二十七)渡過遼水,第二次征討高句麗又在隋煬帝親自指揮下開始了。
但隋煬帝并沒有什么新招數,部署幾乎和第一次一樣。陸路主力以宇文述為主帥,楊義臣為副帥,率大軍渡鴨綠江直赴平壤。水路仍由來護兒率舟師自東萊(膠東半島)海路出發,期與宇文述合圍平壤。隋煬帝自率后路在后督戰,其余各路分道出擊,攻掠高句麗城池。不同的是此次“聽諸將便宜從事”,煬帝收回了軍事進止必須奏報,不許諸將專擅的成命,讓各路大軍放手狼狠地進攻。另外,不再設招降慰撫使,而設監軍,如王仁恭出扶余道,有房彥謙“監扶余道軍”[82]。因給予軍將自由作戰權,使某些將軍得以發揮所長獲得戰役勝利,如王仁恭率軍進攻新城(今遼寧撫順北),以千騎沖垮高句麗數萬人陣地,進而率大軍圍城,得到煬帝嘉獎[83]。
高句麗方面仍然采取堅壁清野,據城堅守的戰術,隋煬帝親自統率后路大軍來到遼東城(今遼寧遼陽市),重新布置圍攻。攻防戰斗打得無比慘烈。為克城立功,隋將郭榮甚至“親蒙矢石,晝夜不釋甲胄百余日”[84]。隋軍用飛樓、橦、云梯、地道四面俱進,但高句麗軍民隨機應變,頑強抵抗,使隋軍仍舊久攻不下。煬帝乃令士兵造布囊百余萬個,貯上土一袋一袋背于城下,堆成闊30步,高與城齊的魚梁大道,使士卒可登而攻城。又命工匠趕造八輪樓車,更高出城墻,可以俯射城內。隋軍在城外圍了一層又一層,用人海戰術,連續進攻,勢在必取。煬帝并寫詩《白馬篇》助威:“白馬金貝裝,橫行遼水傍;問是誰家子,宿衛羽林郎”[85]。在圍攻遼東城的同時,隋各路大路大軍也按部署向高句麗縱深進軍,宇文述、楊義臣率軍再次進至鴨綠江邊,來護兒水軍也齊集東萊海角,張帆待發。高句麗在隋數路大軍的猛烈進攻下,其勢“日蹙”,國家已到了危亡之秋。
但就在這緊要關頭,形勢突然發生逆轉。
大業九年(613)六月乙巳(初三),隋煬帝留在后方督運糧草的禮部尚書楊玄感在黎陽(今河南浚縣東北)舉兵造反了!并進逼東都,這是隋煬帝萬萬沒有料想到的,此舉使煬帝精心策劃并調集了全國一切力量的滅高句麗計劃全盤打亂。《隋書·高麗傳》記其事云:“九年,帝復親征之,乃敕諸軍以便宜從事。諸將分道攻城,賊勢日蹙。會楊玄感作亂,反書至,帝大懼,即日六軍并還”。為應付貴族楊玄感的反叛,隋煬帝不得不馬上停止正在進行中的對高句麗的全面進攻,令各路大軍回師平叛。
楊玄感是已故宰相楊素的長子,體貌岸偉,能文能武,大業二年(606)襲父爵楚國公,不久遷禮部尚書。父楊素戰功顯赫,卻受到煬帝猜忌,有病不喝藥而死。楊玄感暗懷不滿,結交達官子弟和天下豪杰,潛謀廢黜隋煬帝。大業九年(613)再征高句麗,隋煬帝委楊玄感以后方督糧重任,終于給了他復仇機會。時大軍百萬隨御駕出遼東,國內異常空虛,“百姓苦役,天下思亂”。楊玄感故意滯留運河上的漕運,企圖造成遼東百萬隋軍無炊斷糧,因饑餒而自動瓦解。煬帝遣使來催,楊玄感托辭水路多盜,須武裝押送,不但不發遣,反而將船夫武裝起來。又暗中派家僮將從征遼東的弟弟楊玄縱、揚萬碩召回,往長安召弟楊玄挺及李密等人。偽稱來護兒因攻高麗失期而謀反,而以鎮壓叛軍名義舉兵。
舉兵時揚玄感誓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為念,天下騷擾,死江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受苦役的民眾踴躍高呼萬歲。起義后的行動計劃,李密獻三策,上策長驅入薊,扼其咽喉,斷煬帝歸路,中策為直搗長安,翻動根本,均不為楊玄感所納,而采下策進圍東都。一時“從亂者如市”,但東都洛陽堅城一時難以攻下,這就給隋煬帝贏得了喘息調兵平叛的時間。
在遼東前線,兵部侍郎斛斯政因偽造文諜放走了楊玄感的弟弟揚玄縱和楊萬碩,遭到隋煬帝追究。六月戊辰(二十六)夜,發生了斛斯政逃奔高句麗的嚴重事件[86]。斛斯政久知兵部機要,對隋軍事部署內外情況十分熟悉,他的叛逃意味著隋軍全部機密作戰方案及內部情勢都泄露給敵方。這對高句麗當然是意外的收獲,對隋軍則是巨大的損失。隋煬帝得悉大為震怒,即命將作少監閻毗率二千騎追擊,但不及。斛斯政據高句麗栢崖城,閻毗攻了兩天不能下,只好退軍,竟于路上暴卒[87]。煬帝氣恨難當,嚴查叛黨,許多人受牽連,如高士廉與斛斯政多有交游,煬帝將他謫至邊遠[88]。連煬帝的親信藩邸舊臣文士王胄和虞綽也因與楊玄感友善而俱徙邊[89]。江南縉紳康抱因其兄受楊玄感官竟坐當死[90]。
隋煬帝改任裴矩知掌兵部機事,詔宇文述等班師,發諸郡兵討楊玄感,并派老宰相蘇威安撫關中。庚午(二十八)夜二更,隋軍撤退,其軍資、器械積如山丘,全部棄之而去。時眾心洶洶,爭相奪路,亂成一團。諸道分散,人流滾滾,無復部伍。高句麗人在城墻上看見,聚為奇觀,但未敢貿然出城追擊,只是在隋煬帝御營全部渡過遼水后,才追殺走在最后的嬴弱數千。在東萊尚未出海的來護兒聞知楊玄感反狀,也自動放棄了出海攻擊高句麗,速回師返救東都。
于是乎隋百萬大軍又一次狼狽退回,由于后院起火,出師未捷先退兵,隋煬帝二征高句麗又遭到失敗,一無所獲,皇帝的無上威權再一次掃地蒙羞。
六、惱羞成怒第三次征討無功而還
貴族楊玄感的叛亂毀掉了隋煬帝志在必得的第二次征高句麗行動。由于不用李密謀,出下策兵頓東都堅城不下,到再謀西取關中長安時已來不及,從遼東、膠東撤下來的官軍對叛軍合圍,很快將其鎮壓。叛將被捕者“并具梟磔”,楊氏兄弟全被誅滅,公卿中有人奏改楊玄感兄弟姓“梟”氏,以免污沒皇姓,隋煬帝詔可[91]。但楊玄感公開打出推翻隋煬帝暴政的口號,要“廢昏立明”,則大掃了隋煬帝威風,對隋政權的沖擊無可估量,各地農民起義風起云涌,社會各階層都參加了反暴政的暴動,包括不少統治集團貴族成員,以致于“舉天下之人,十分九為盜賊,皆盜武馬,始作長槍,攻陷城邑”[92]。但隋煬帝竟不顧國內嚴重形勢,仍念念不忘“高麗小丑”高元,執意要第三次征討高句麗。
大業十年(614)元旦,隋煬帝是在高陽(今河北定縣)行在所度過。正月甲寅(十五日),煬帝以宗女信義公主嫁予西突厥曷娑那(處羅)可汗。處羅兩次都隨御駕征遼,煬帝本想讓他及四夷使者親眼看看他掃平高句麗如彈指一揮,但兩次慘敗讓煬帝臉面丟盡,嫁公主是進一步籠絡處羅,煬帝還要帶他第三次出征,希望能挽回面子真正威服四夷。
這年,百濟又遣使朝貢[93],隋煬帝接見了其使者并再約以夾擊高句麗之事。二月辛未(初三),煬帝詔百官商討再伐高句麗,全體官員竟沉默了數日。群臣知道盡管楊玄感叛亂已平定,但國內“群盜所在皆滿”,局勢已亂,征遼鬧得天怒人怨,百官明知安撫國內動亂才是當務之急,但煬帝駐蹕高陽對高句麗志在必取,群臣又有何話可說,又有誰敢說呢?只能任憑煬帝一意孤行,一錯到底,看著他敗亡了。
戊子(二十日),隋煬帝下了一道奇怪的詔書,稱“往年出車問罪,將廟遼濱,廟算勝略,具有進止。而諒昏兇,罔識成敗,高颎愎恨,本無智謀,臨三軍猶兒戲,視人命如草芥,不尊成規,坐貽撓退,遂令死亡者眾,不及埋藏。今宜遣使人分道收葬,設祭于遼西郡,立道場一所”[94]。煬帝裝出一副悲憫心腸,派人收葬棄于荒野的隋征遼士兵骸骨,設立道場祭壇超度死者亡靈,但不檢討自己瞎指揮,反而將過錯推到開皇十八年(598)漢王楊諒及高颎身上,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啊。清人王鳴盛論曰:“大業十年詔收葬征遼死亡者,而遠引漢王諒、高颎開皇十八年征遼敗退事,以大業八年之敗為諱,欲駕罪于父也”[95]。此舉當然也是相當滑稽的。
二月辛卯(二十三),隋煬帝下詔第三次御駕親征高句麗,詔曰:“黃帝五十二戰,成湯二十七征,方乃德施諸侯,令行天下”。把自己打扮成湯武一般的圣王,要除暴止戈。詔書掩蓋了前兩次出兵的失敗,反而編造出“高元泥首送款請罪”,“朕許其改過,乃詔班師”[96]的謊言。是高元怙惡不改,所以煬帝御駕再征,要解民于倒懸。這顯然是彌天大謊,愚民惑眾,煽動仇恨,是專制帝王慣用的手法。
隋大軍百萬就這樣又一次被隋煬帝帶上了遼東前線。和前兩次一樣,征人四遠奔赴如流,舳艫相次千余里,役夫往返在道者常數十萬,死者臭穢盈路,逃役者不計其數。如劉弘基從征遼東,家貧不能自備行裝,自度失期當斬,遂與同伴殺牛,讓官吏來逮自己進縣大牢[97]。征遼路上,征人與逃亡者幾乎是擦肩而過,人流洶涌。癸亥(二十五),煬帝來到北平郡盧龍縣的臨渝宮(今河北撫寧縣境),在曠野設壇祭祀黃帝。隋煬帝親御戎服主祭,將抓到的逃亡士兵斬首,以人血涂鼓,以示警誡,但兵民從役者仍逃亡不絕。
雖然一路上各地變亂的消息不斷傳來,但隋煬帝一面發詔各地官員征討鎮壓,一面繼續行軍。由于逃亡不斷,行程很慢,走了近3個月,秋七月癸丑(十七日)煬帝車駕才趕到塞外遼河邊上的懷遠鎮(今遼寧懷遠縣)。隋煬帝雖又一次親臨前線,但原先征發的軍隊多失期不至,士兵厭戰,役夫逃亡,加上秋涼已到,時間不多,隋軍雖多,但實際上很虛弱。同時,高句麗屢遭隋軍剽掠攻擊,自己又主動毀壞稼禾,實行堅壁清野,雖頂住了隋軍進攻未致亡國,但三年不種稼穡,野無青草,舉國饑荒,亦舉動困弊,難以招架。當時隋再鼓一把勁滅亡高句麗的可能性并非沒有,但即使滅了高句麗也控制不住,因為隋煬帝連本國局勢都無法控制,何談他國。因此,一昧征討高句麗對隋來講已毫無意義。但隋煬帝主要是天子顏面下不來,總要討個說法,不能不勝而退,否則皇帝難當。
此時,來護兒率水軍泛海先于遼東半島登陸,占領了高句麗的畢奢城(今遼寧大連市北),但水軍副總管周法尚則在進軍途中遇疾而亡,死時遺言以未能親見滅高句麗而遺憾。高句麗舉兵迎戰來護兒軍,被擊敗,來護兒于是勒兵將轉攻平壤,高麗王高元震恐,連年守土作戰已人疲馬乏,戰爭搗毀農田三年顆粒無收,全國大饑無力再戰,于是遣使執送隋叛臣斛斯政于遼東城(今遼寧遼陽市)下,上表乞降。
由于前兩次失敗,隋煬帝對取勝也不象先前那樣有把握,對戰局的發展也沒有底,國內的頻頻叛亂和軍糧轉輸困難使他頗為沮喪,心亂如麻,難以下臺收場。七月甲子(二十八),當高麗王的使者囚送斛斯政來贖罪乞降時,煬帝異常興奮,這不是給自已臺階下嗎?自己不失為勝利者,至少挽回了點面子。對于隋煬帝來講,這時死要活要的就是皇帝的威嚴臉面。于是,隋煬帝立即下令隋各路大軍停止進攻,接受高句麗降款,并遣人持節往來護兒軍中,詔其率水軍回師。
來護兒剛打了勝仗,一雪前次平壤戰敗之恥,且水軍隨船帶糧有運輸條件,士卒士氣較高,對戰爭前景持樂觀態度。接到回師詔令,來護兒大為不滿,即召集部眾喊:“三度出兵,未能平賊,此還也,不可重來。今高麗困弊,野無青草,以我眾戰,不日克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偽主,獻捷而歸”。不肯奉詔,上表請戰。長史崔君肅認為詔命不可抗,來護兒激憤地說:“吾在閫外,事合專決,豈容千里稟聽成規,俄頃之間,動失機會,勞而無功,故其宜也”[98]。認為勝利進軍中未達目的突然退兵太輕率,表示寧可獲罪也要擒得高元,況舍此成功機會,今后就不會再有了。從領兵將帥的角度看,來護兒和于仲文都堪稱大將,有建功立業之心,能謀善戰,若隋煬帝不御駕親征,而將大局委交這樣的將帥,發兵二三十萬,用不著百萬人眾,未嘗就不能克敵制勝,然而,有將帥卻不能用。這時,崔君肅也大聲向眾將喊叫:“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將聞奏,皆獲罪也”。諸將恐懼,都勸來護兒奉詔退軍,護兒無奈,只好率水師回還。
八月己巳(初四),秋涼陣陣,隋煬帝自懷遠鎮班師回朝。三次大規模的征遼軍事行動就此結束了,最后一次雖走得從容,但同樣是一無所獲!
回師路上,隋煬帝御駕在邯鄲竟遭到農民軍楊公卿部抄劫,被劫去飛黃上廄御馬42匹。冬十月丁卯(初三),御駕回到東都洛陽,未作休整就繼續西行,己丑(十五日)回到京師大興城(長安)。隋煬帝讓高句麗使者押斛斯政親告于太廟,算是獻捷。于是下詔征高麗王高元入朝,當然高元根本不會加以理會,煬帝又自感羞辱,拘留高句麗使者,并下敕令將帥整裝嚴備,試圖再舉兵問罪遼左[99]。但此時天下已大亂,煬帝再也奈何高元不得了,小丑不再是高元而是自己,帝王權力再大也有限度,他終于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隋煬帝于是把滿腔仇恨都集中到高元送來的替死鬼斛斯政身上。宇文述最了解皇上的心思,上奏稱:“斛斯政之罪,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忿。若同常刑,賊臣逆子何以懲肅,請變常法。”十一月丙申(初二),隋煬帝下令將斛斯政押解至金光門外,縛于柱上,不用劊子手行刑,而讓公卿百僚都操弓擊射,然后臠割其肉烹煮之,讓百官啖之。所謂啖,即吃,也就是讓大家把斛斯政吃了來解恨。在隋煬帝兇惡的目光威逼下,即使是衣冠楚楚的朝官也不得不強忍惡心,嘗一嘗人肉味道,有佞者竟“啖之至飽”。人肉吃完后再收余骨,“焚而揚之”[100],這比千刀萬剮還更泄憤。
隋煬帝三征高句麗失敗的政治后果十分嚴重,國內反叛已成燎原之勢,隋煬帝已無法處理,心如一團亂麻,他在京師長安還未呆上一個月,即率百官往東都洛陽。大業十一年(615)春正月甲午(初一)元旦大朝會后,隋煬帝于東都宮殿大宴招待公卿百僚四夷使節,但高句麗并沒有派朝貢使者來,已滅亡的吐谷渾王伏允也趁機“復其故地,屢寇河右”[101]。而四夷使者與其說是來朝貢,不如說是來看熱鬧,看大隋天子的狼狽樣。三征高句麗慘敗標志著以大隋王朝為中心的東亞國際秩序華夷朝貢體制徹底崩潰。但隋煬帝還是厚著臉皮拉開遮羞布。乙卯(十五日),大會蠻夷,設魚龍漫延之樂,對各國使節頒賜各有差。一陣鬧騰過后,煬帝實在按捺不住悲痛的心情,回宮獨自飲酒大醉,因賦詩曰:“徒有歸飛心,無復因風力”,說的是自己志慕秦皇、漢武,有圣王凌云之志,卻無回天之力,征遼慘敗國家政治失控,圣王變成了小丑,可憐的煬帝,今后這皇帝還怎么當下去啊!煬帝令宮人吟詠,自己聽著聽著不禁泣下沾襟,侍御者莫不欷噓![102]
八月秋高氣爽時,隋煬帝不聽勸阻,試圖北巡突厥,想重演大業三年(607)入啟民可汗牙帳受四夷共推為“圣人可汗”的盛事,以求挽回一點面子。但在雁門(今山西代縣)遭到東突厥始畢可汗幾十萬騎兵圍困,雖然各路勤王之師來解圍,將御駕迎回東都,但煬帝小丑再一次威風掃地。高句麗、突厥、吐谷渾均已成為敵國,不再把隋煬帝放在眼里。面對國內反者多如帽毛,群盜所在蜂起的嚴重局勢,隋煬帝魂褫氣懾,竄身江湖,不敢在帝國中心的中原久居,于大業十二年(616)七月南下江都,兩年后被身邊侍衛驍果弒于江都宮,大隋王朝也就隨之滅亡了。江山易主,各地豪杰經過一番爭奪,自太原起兵襲奪長安的李淵最后建立了唐朝,而他乃是隋煬帝的親表弟。
七、結語
隋煬帝三征高句麗慘敗喪國已是一千五百年前的歷史,如何評價這次規模空前而結局滑稽的戰爭呢?
古今中外學者對隋煬帝的荒唐舉動多持異議。其戰爭的性質無疑是侵略擴張,是中華帝國盛世的對外擴張舉動,當然我們也不否定高句麗也曾四處侵略擴張,拓土遼東南攻百濟,隋朝打著收復故地的晃子,把征討高句麗稱之為“征遼”,并不能改變侵略擴張的性質。高句麗畢竟是立國五百多年的獨立國家,并沒有招惹隋朝,有自己的獨立權和發展權,隋以不朝貢為由輕啟戰端,站在高句麗的立場上講,是絕無道理而不能接受的。中國古代的華夷朝貢體制妄自尊大,講究排場死要面子,不尊重小國鄰國,要外國人象本國臣民一樣對皇上頂禮膜拜,隋煬帝夸示四夷在這方面虛榮心更堪,不少人將戰爭歸咎于隋煬帝的好大喜功,強調個人因素,認為煬帝是典型的昏君。
但從歷史上看,在隋煬帝之前已有隋文帝派漢王楊諒征遼,而且代隋而立的唐朝以英明皇帝著稱的唐太宗也數次征遼,太宗以“今天下大定,唯遼東未賓”為辭,一而再,再而三地征討高句麗,其決心與隋煬帝竟無二致。唐太宗死后,繼位的唐高宗又連續發兵征遼,直到總章元年(668)聯合新羅滅亡高句麗,攻拔平壤才算了事。隋唐好幾代帝王都把征討高句麗當作國家頭等大事,而大動干戈。這至少可以讓我們明白,把這場戰爭完全歸結為隋煬帝個人的虛榮心,權力意志,也是不足以服人的!
隋唐帝國與高句麗的戰爭有著深刻的歷史和地緣政治背景,正如我們前面所述,高句麗趁漢魏晉中華帝國崩離,南北朝分裂戰亂的局勢,由一個長白山小國侵吞漢魏故郡,征服周邊部族,發展為遼東大國,其性質與鮮卑、匈奴等五胡入據中原一樣,與突厥、吐谷渾發展為強大獨立國家的情形也相同。在古代各民族國家都有自己的發展權,我們不能以現代的國際法來規范古人。不同的是五胡及各族政權均短命不長,高句麗卻五百年不衰,廣開土好大王四面擴張,甚至想統一朝鮮半島,在東北亞一隅建立了地方霸權,與中華帝國勢不兩立。我們不能以高句麗向隋朝貢接受隋冊封就否認其為獨立的國家,新羅、百濟也一直朝貢。獨立強盛的高句麗在遼左俯瞰中原,在古時國際政治法則下與隋唐無法和平共處,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隋唐若不滅高句麗,高句麗完全可能趁中國有亂而入踞中原。后來的歷史已作證明,唐雖滅高句麗,但幾百年后與高句麗、渤海國有親緣關系且語言相近的女真人兩度由遼東入主中原,先后建立了金與清兩個王朝。特別是滿清前身的后金(意為金朝的繼承者)與明朝在遼東的對峙,形勢與高句麗與隋唐的關系極為相象,只不過結局不同,滿清趁中國內亂而一統中華。從大歷史的眼光看問題,我們就不能簡單地把隋煬帝征討高句麗視為荒唐,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皇帝,國家生死存亡當然不能不加考慮。
隋煬帝的荒唐在于不顧天時地利瞎指揮,致使隋軍慘敗。高句麗無疑是勁敵,但隋煬帝妄自尊大,試圖以耀武揚威恫嚇之術讓對方投降,精心導演出兵儀式,以中華禮樂夸示四夷,百萬大軍耗費巨大的打仗卻有如演戲,成為世界軍事史上的笑柄。專制皇權不可違,隋煬帝想入非非,百萬士兵跟著遭秧,并直接導致民變叛亂國家滅亡,萬民涂炭。獨裁專斷的皇權可因一人而毀天下,煬帝難逃亡國之責,是典型的暴君。
高句麗軍民面對強敵不屈服敢于保家衛國,利用天時地利采取堅壁清野誘敵深入的戰術,善戰善謀及表現出的民族自尊心可歌可泣,其以弱抗強堅持抗戰取得最后勝利的事跡是值得高度評價的。
注釋:
[1]《隋書》卷84《北狄·突厥傳》。
[2]見《尚書·洪范》、《論語.微子》、《左傳》僖公15年、《淮南子.齊俗訓》等。又參見韓國學者沈白綱編《箕子古記錄選編》,民族文化研究院學術叢書,民族文化研究院2002年版。
[3]參見(韓)李基白《古朝鮮國家的形成》,載《韓國史市民講座》第2集,漢城,一潮閣,1988年,p17。
[4](日)白鳥庫基《箕子不是朝鮮始祖》,載《每日新聞》,東京,1910年8月31日。
[5]有關漢晉在朝鮮半島北部地區設置郡縣的史實,中國史籍《漢書》、《后漢書》、《三國志》、《晉書》、《水經注》等,朝鮮古籍《三國史記》、《三國遺事》等均有翔實記載。秦漢王朝還在今越南設置郡縣,有交趾郡、象郡等,象郡以其地產大象而名之。高句麗之名即起自漢置玄菟郡句麗縣,其王高姓,稱高句麗。
[6]《隋書》卷67《裴矩傳》。
[7]《佛祖統記》卷9。
[8]《三國遺事》卷5。
[9]《隋書》卷82《東夷傳·史臣曰》
[10]《續高僧傳》卷15《唐京師弘福寺釋靈潤傳》。
[11]《續高僧傳》卷13《唐京師大莊嚴寺釋神迥傳》。
[12]《隋書》卷76《文學·杜正藏傳》。
[13]參見(日)山中順雅《日本古代一千五百年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p147。
[14]《隋書》卷81《東夷·高麗傳》。
[15]《隋書》卷81《東夷·百濟傳》。
[16]《陳書》卷6《后主紀》。
[17]《隋書》卷39《陰壽傳》。
[18]《隋書》卷81《東夷·靺鞨傳》。
[19]《隋書》卷81《東夷·高麗傳》。
[20]《三國史記》卷19《高句麗本紀第七》記:“三十二年,王聞陳亡大懼,理兵積谷,為拒守之策”。
[21]《隋書》卷66《陸知命傳》。
[22]《隋書》卷2《高祖紀下》。
[23]《隋書》卷81《東夷·新羅傳》。
[24]《隋書》卷2《高祖紀下》。
[25]《隋書》卷47《韋沖傳》。
[26]《隋書》卷81《東夷·高麗傳》。
[27]《隋書》卷81《東夷·高麗傳》。
[28]《隋書》卷47《韋沖傳》。
[29]《隋書》卷84《北狄·契丹傳》。
[30]《隋書》卷81《東夷·百濟傳》。
[31]《隋書》卷67《裴矩傳》。
[32]《隋書》卷84《北狄·西突厥傳》。
[33]《隋書》卷67《裴矩傳》。
[34]《資治通鑒》卷181隋煬帝大業七年二月。
[35]《法苑珠林》卷18引《冥報記》。
[36]《續高僧傳》卷19《唐天臺山國清寺灌頂傳》。
[37]《舊唐書》卷192《王遠知傳》。
[38]《隋書》卷81《東夷·百濟傳》。
[39]參見劉健明《一場求不戰而勝的攻戰——隋煬帝征高麗試析》。載《唐研究》第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40]《隋書》卷78《藝術·耿詢傳》。
[41]《隋書》卷58《許善心傳》。
[42]《隋書》卷78《藝術·庾質傳》。
[43]《隋書》卷60《段文振傳》。
[44]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下篇《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及外夷與內政之關系》。
[45]《隋書》卷4《隋煬帝紀下》。
[46]《隋書》卷81《東夷傳·史臣曰》。
[47]《隋書》卷4《隋煬帝紀下》。
[48]《隋書》卷4《隋煬帝紀下》。
[49]《隋書》卷8《禮儀志三·軍禮》。
[50]《隋書》卷4《隋煬帝紀下》。
[51]《隋書》卷8《禮儀志三·軍禮》。
[52]《隋書》卷8《禮儀志三·軍禮》。
[53]《隋書》卷61《宇文述傳》。
[54]《隋書》卷41《蘇威傳》。
[55]《隋書》卷4《隋煬帝紀下》。
[56]《隋書》卷8《禮儀志三·軍禮》。
[57]《隋書》卷71《游元傳》。
[58]《北史》卷76《來護兒傳》。
[59]《隋書》卷64《麥鐵杖傳》。
[60]《資治通鑒》卷181隋煬帝大業八年。
[61]《隋書》卷12《禮儀志七·宮衛》;《隋書》卷68《何稠傳》。
[62]見《文苑英華》卷201。
[63]《資治通鑒》卷181隋煬帝大業八年五月。
[64]《隋書》卷60《于仲文傳》。
[65]《隋書》卷65《薛世雄傳》。
[66]《隋書》卷65《薛世雄傳》。
[67]《隋書》卷42《觀德王雄傳》。
[68]《唐大詔令集》卷114《政事·牧瘞》。
[69]牛僧孺《玄怪錄上》。
[70]《隋書》卷60《于仲文傳》。
[71]《隋書》卷81《東夷·靺鞨傳》。
[72]《隋書》卷70《史臣曰》。
[73]《全唐文》卷915,德宣《隋司徒陳公余寶造寺碑》。
[74]《隋書》卷3《煬帝紀上》。
[75]《資治通鑒》卷181隋煬帝大業七年。
[76]《資治通鑒》卷181隋煬帝大業七年。
[77]曾慥《類說》卷6《知世郎》。
[78]《隋書》卷4《煬帝紀下》。
[79]《資治通鑒》卷182隋煬帝大業九年。
[80]《隋書》卷50《郭榮傳》。
[81]《隋書》卷78《藝術·庾質傳》。
[82]《隋書》卷66《房彥謙傳》。
[83]《隋書》卷65《王仁恭傳》。
[84]《隋書》卷50《郭榮傳》。
[85]《文苑英華》卷209。
[86]《隋書》卷70《斛斯政傳》。
[87]《隋書》卷68《閻毗傳》。
[88]《舊唐書》卷65《高士廉傳》。
[89]《隋書》卷76《文學·王胄傳》。
[90]《冥報記》卷下《隋康抱》條。
[91]《隋書》卷70《楊玄感傳》
[92]《隋書》卷24《食貨志》。
[93]《隋書》卷81《東夷·百濟傳》。
[94]《隋書》卷4《煬帝紀下》。
[95]《十七史商榷》卷66《大業十年》條。
[96]《隋書》卷4《煬帝紀下》。
[97]《舊唐書》卷58《劉弘基傳》。
[98]《隋書》卷64《來護兒傳》。
[99]《隋書》卷81《東夷·高句麗傳》。
[100]《隋書》卷70《斛斯政傳》;《資治通鑒》卷182隋煬帝大業十年。
[101]《隋書》卷83《西域·吐谷渾傳》。
[102]《隋書》卷22《五行志上》。
(本文刊于韓國《中央史論》第23輯,2006年6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