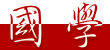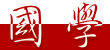|
初識鐘敬文先生是他資產(chǎn)階級情調(diào)十足的散文,連一區(qū)區(qū)荷塘也要"清賞"再三后而"憶舊"。使我這個慣于追逐轟轟烈烈的攝影記者很不習慣,仿佛于跑跑顛顛中,隔岸觀看煙霧中的彼岸世界,虛無飄渺而節(jié)奏緩慢,好像泡在陳年的顯影液中,由于陳舊腐朽而愈發(fā)呈黃褐色,猶如隔世的一道風景。
鐘敬文原名譚宗,筆名靜聞、靜君、金粟。1903年生于廣東海豐,陸安師范畢業(yè)后東渡日本。他自幼讀書成癖,自詡"我是書呆子,對于讀書,差不多有一種不易動搖的癖好。假如我對于別的許多事情,我是任性的、隨便的,對于這卻多少要有點特別的處置"
。 留學(xué)日本時有一個時期,鐘敬文每天把自己關(guān)在東京都九層樓的圖書館里,"盡情去書城里閑蕩",以完成年初給自己制定的讀書計劃。鐘敬文每讀好書,都如佳釀入腹,盡情陶醉。讀書之外他還熱衷散文,喜歡對羅曼·羅蘭、法朗士的散文名篇反復(fù)吟誦、細細品味。由此開始模仿著寫出《荔枝小品》、《西湖漫拾》、《湖上散記》等。也許受東洋日式教育影響,文風頗具日風,很有日人俳句的意境。相形之下,日后當作飯碗的民俗學(xué)反倒幾成副業(yè),這與另一位我采訪過的民族學(xué)家林耀華形成天壤之別。林教授乃哈佛博士,舊中國當過燕京大學(xué)社會學(xué)系主任,新中國曾任民族研究所所長,畢生埋頭專業(yè)心無旁騖,著作等身學(xué)業(yè)精深,但因受西洋正規(guī)教育桎梏,遠不如留學(xué)東洋的鐘敬文活得滋潤。
曾在北京師范大學(xué)任教、現(xiàn)已退休的96歲老翁鐘敬文自稱也是北大人,"因為師范大學(xué)本來就是京師大學(xué)堂的師范館"。但話音未落,馬上意識到自己畢竟與北大有段距離,于是轉(zhuǎn)而對北大壟斷學(xué)界憤憤不平。"國外大學(xué)對北大情有獨鐘,也應(yīng)該把師大包括進去",老頑童般為自己耿耿于懷的北大情結(jié)鳴不平。談到師大人應(yīng)處處為人師表時,鐘敬文不由對胡適肅然起敬,說世界上沒有哪個大學(xué)校長能像北大校長胡適那樣為人師表:得36個博士學(xué)位、風流瀟灑,品德高尚,民主,科學(xué),自由。他說張中行著作中已經(jīng)寫了許多胡適,可惜還不夠,他還有意再說而特說。
鉆了一輩子書齋的鐘敬文有時會突然變得很激憤,大有一夫當關(guān)萬夫莫開、老兔子急了也咬人的架勢。我頭一次往北師大他府上拜訪,就吃了閉門羹。非但沒有以往造訪其他耄耋老者家感受到的溫暖,而且待客之道很難說與"平和"沾邊。鐘宅規(guī)定"但凡記者來訪,非事先預(yù)約,否則不得入"
。我只能隔著門縫問答,好似當年在巴格達采訪薩達姆的總統(tǒng)府。 待到日后按規(guī)矩預(yù)約,他又約法三章:"不帶攝影機,不接電線,不碰屋內(nèi)一切物品。"等我全盤接受后才獲恩準:"坐一下便走。"進得屋內(nèi),他雙目炯炯以NBA盯人戰(zhàn)術(shù),看著我坐下,并再三審視我的確只有一人,身后絕沒有人偷偷接電線后才釋然。又再次叮囑,絕對不可打開攝影包,這才在我對面頹然落座。
據(jù)鐘老講,之所以這樣全民皆兵,全因遭某電視臺一朝蛇咬所至。年前,該電視臺突然派來一彪人馬,說要搶救文化遺產(chǎn),做人物專訪,老人聞之暗喜,鼎全力配合。不料家中從此翻江倒海,打燈光、接電線、移物布景,弄得雞飛狗走,累的老人幾乎氣絕。臨走還"借"走一大批珍貴資料,說回去翻拍,鐘老只有忍痛借出。誰知從此肉包子打洋狗,一去不回頭。現(xiàn)在說起此事還急得老人心疼。事后派人找到該電視臺,結(jié)果根本找不到"苦主"。找人一問,才知道該電視臺銳意改革,十停人馬中有六七停為臨時招募,"盡是些七長八短漢,四山五岳人"。來如雨去如風。氣得95老翁擊案狂呼上當,要我這個"新華社,回去內(nèi)參一下,電視臺招臨時工,罪責遠大于出版社賣書號"。直嚇得我五官易位,一臉茫然,鐘敬文卻坐在一邊嘻嘻而笑。說他向我怒發(fā)沖冠,只圖自己一吐為快,并非真要我"參"誰,他自己明知是"講了也白講,不講白不講"。自言自語絮絮叨叨,一連重復(fù)五、六遍之后,才面露得意之色。揮舞起兩只雞爪般小手,猶如曹孟德橫槊江東一般,頗為自己一怒而得佳句而自得。
據(jù)鐘敬文自己講,他這個書癡并非一心深居幽室, 盡管埋頭讀書,卻也熟諳天下事。據(jù)他說不久前他還聯(lián)合了北大教授季羨林并肩給訪談他們的電視臺提意見,言辭尖銳舉座皆驚。幾年前,他還和復(fù)旦教授蘇步青同期在《求是》雜志上發(fā)表政論文章,向黨內(nèi)不正之風提意見。文章發(fā)表之時萬分興奮,特意上街買了上百本送人。"因為這是黨內(nèi)最高刊物,連黨員寫的文章也非輕易可上。更何況我們非黨人士。"
談興正健,鐘敬文忽以右手指結(jié)擊案,示意暫停,原來已到讀書時間。96歲的鐘老先生積習難改,果然是個"書癡"。一時間關(guān)閉了所有神經(jīng),引身于書堆之后,沉浸在夕陽里,宛若一幅發(fā)黃的陳年舊照,又隱回到30年代的故紙堆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