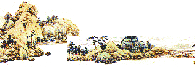|
|
|||
|
荒
|
||||
|
唐
|
||||
|
歲
|
||||
|
月
|
||||
|
□
董新芳
|
||||
|
登記號(hào):21-2001-A-(0656)-0115
|
||||||
公元一千九百五十八年三月,槐樹溝的人們還沉浸在成立人公社的興奮和激動(dòng)之中,人人臉上都堆滿了笑容,他們聽公社趙書記說,人民公社是通向共產(chǎn)主義的橋梁,是一座金橋,是通向幸福的金橋。他們雖然弄不清楚什么是共產(chǎn)主義,但他們聽趙書記說,到了共產(chǎn)主義住的樓上樓下,屋里是電燈電話,吃的是想啥有啥,穿的是要啥給啥。一句話說到底,是各取所需。他們多么希望共產(chǎn)主義早點(diǎn)到來,好享享共產(chǎn)主義的清福。但共產(chǎn)主義究竟還有多遠(yuǎn),誰也不知道。他們都在心里殷切地期盼著。張光春更是著急,他象一條發(fā)情的黃牛躁動(dòng)不安。在家里,他的屁股上象長(zhǎng)了疔瘡坐臥不寧。在外面,他的腳底象被虱子咬了似的癢得鉆心。他坐著心焦,站著著急,只有來回走動(dòng)著心里才感到舒坦。他總象在尋找著什么,究竟尋找什么他也說不清。也許是人人都在尋找的那條通向共產(chǎn)主義的大道。那天,雞叫頭遍他就起床了。他仰頭望望天,藍(lán)藍(lán)的天上一片繁星,密密麻麻不住地眨著眼睛。他低頭看看地,模模糊糊什么也看不清。他抬起頭向遠(yuǎn)處看,座座大山象黑暗中的魔影。張光春猶豫了片刻,抬腳向村頭走去。他來到村頭的老榆樹下,手扶著歷經(jīng)蒼桑滿身傷疤彎腰駝背的老榆樹的樹身,望著老榆樹骨瘦如柴的胳膊上吊著的那塊厚厚的綱板,久久未動(dòng)。沉重啊!多么地沉重!老榆樹是長(zhǎng)在石頭上的,雖已百年也只有碗口那么粗。樹身彎曲,樹冠極小,象一位歷經(jīng)蒼桑受盡磨難頭戴斗笠的駝背老人。由于老榆樹生長(zhǎng)在村口,當(dāng)?shù)溃业貏?shì)頗高,因而在老榆樹很小的時(shí)候,村里的人就在它細(xì)小的胳膊上掛了一口不大但又不是很小的鐵鐘,村里有什么事了就敲響那口鐘。后來那口鐘不知哪兒去了,張光春復(fù)員回來后,在平川市一個(gè)工廠的熟人那里找了一塊鋼板,吊在老榆樹上替代了那口不知去向的鐵鐘。幾年了,鋼板雖然生了銹,表面象鍍了一層銅,但敲起來依然聲音響亮。每當(dāng)張光春敲起這塊鋼板,村里的人都會(huì)自動(dòng)走出家門聽從張光春的分派。想到此,張光春情不自禁地伸手摸了摸猴子似的吊在樹枝上的鋼板。 天上的星星漸漸地退到了幕后,越來越稀,越來越少了。魚肚白從東方慢慢泛起不斷地?cái)U(kuò)充著自己的領(lǐng)地,稀少的星星無奈地讓出了自己小得可憐的地盤。天就要亮了。張光春沿著小路爬上了山坡。滿山的洋槐樹剛剛吐綠,散發(fā)著縷縷清香。張光春雙手叉腰,深深地吸了口黎明前清新的空氣,頓感心清氣爽。他回望還在沉睡的村莊,房朦朧,樹朦朧。那兩棵朦朧的大槐樹,那大槐樹上朦朧的鳥窩。他忽然覺得村中的一切都是朦朧的,包括那朦朧的房子里的人也是朦朧的。那兩棵大槐樹,一棵在溝北,一棵在溝南,都有幾摟粗,而且都已空心,樹冠如傘,濃蔭數(shù)丈,象兩位慈祥的老人守護(hù)著槐樹溝,守護(hù)著他們的子孫。兩棵大槐樹上都有一個(gè)籮筐大小的老鸛窩,窩里住著白肚子老鸛,它們總是出雙入對(duì),恩愛有加。春天,古槐吐綠,槐花串串,引蝶招蜂,香溢全村。老鸛在樹枝上跳來跳去,喳喳地叫著,歡快無比。麻雀成群結(jié)隊(duì)落滿枝頭尤如樹上結(jié)出的串串果實(shí)。夏天,村里男女老少為了躲避盛夏的暑熱,不少人都來到大槐樹下,享受著濃郁的蔭涼。他們?cè)谶@里講述著祖祖輩輩傳下來的關(guān)于大槐樹的故事。張光春清楚地記得他爺爺他父親不厭其煩地一遍又一遍地向他們的子孫們復(fù)述著大槐樹的古老的傳說。張光春沒有忘記他還是一個(gè)光屁股娃子的時(shí)候,他的爺爺把他攬?jiān)趹牙铮鎸?duì)乘涼的張姓人家捋著白胡子說,前人栽樹,后人乘涼。如今,咱們?cè)谶@棵大槐樹下乘涼,是不能忘記咱們的祖先的。這棵大槐樹是咱們的祖先栽下的。爺爺說著,抬起頭深情地望了大槐樹一眼,眼神中對(duì)祖先充滿了無限的崇敬,無限的懷念。接著,爺爺講述了祖先遷居和種植槐樹的緣由。爺爺說,說來話就長(zhǎng)了。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也就是從宋末到元初到朱元璋奪取天下建立明朝。這期間,河南一帶一直處于兵荒馬亂之中,你打過來,他打過去,象拉鋸一樣瘋狂地爭(zhēng)奪著中原大地。神仙打仗,凡人可就遭殃了。糧食被當(dāng)兵的搶光了,牲口被當(dāng)兵的宰吃了。加上黃河連年決口,這一帶的百姓是既遭天災(zāi)又遭兵禍,要吃無吃要穿無穿,凍死的,餓死的,被黃河水淹死的,難計(jì)其數(shù)。那時(shí)的河南是千里無人煙,荒涼又凄慘。明太祖洪武年間和明成祖永樂年間,朝廷為了均衡全國(guó)人口分布,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先后兩次將未致戰(zhàn)禍的山西人遷于河南。我們的祖先就是那時(shí)從山西洪洞縣遷來的。據(jù)說,洪洞縣有個(gè)廣濟(jì)寺,寺中有一棵大槐樹,我們的祖先在離開家鄉(xiāng)時(shí)到寺院里祭奠故土祭奠祖先后坐在大槐樹下傾訴離別之情。大槐樹上結(jié)有串串槐角,于是我們的祖先做出了一個(gè)決定,凡是離開故土的人都要帶一把大槐樹的種籽,無論遷到哪兒,哪怕是天涯海角都要種植槐樹,讓槐樹象洪洞縣的人一樣在天涯海角生根發(fā)芽開花結(jié)果,世代繁衍,永遠(yuǎn)興旺。用種植槐樹的方式使他們世世代代牢記故土不忘祖先。溝南溝北這兩棵大槐樹就是咱們祖先遷來時(shí)栽種的。槐樹溝的村名也是咱祖先在這里遍植槐樹而得。爺爺?shù)脑挘瑥埞獯翰]有忘記。 山坡上除了槐樹,還有兩片霧憧憧的柏樹林,各有數(shù)畝,那是兩塊墳地。墳地上,柏樹有粗如臉盆的,也有細(xì)如碗口的,樹身挺拔,枝繁葉茂。在巨大的樹冠濃郁的樹蔭籠罩下,形成一派凝聚不散的仙氣神韻。東邊那片柏樹林是何家墳,西頭那片柏樹林是張家墳。張何兩家的墳都扎在溝北的山坡上,那里向陽,風(fēng)水好。柏樹林里埋葬著張何兩家的先人們,因此,他們對(duì)柏樹關(guān)愛備至,從不準(zhǔn)砍伐。即如是過年,也只在樹身上剔一點(diǎn)小枝小杈插在門口以示吉慶祥和。張光春望著茂密的柏樹林,想起了去年二月十五上墳時(shí)父親當(dāng)著眾人對(duì)他的交待:光春,你要記住,無論發(fā)生什么情況,墳地的柏樹一棵也不能砍。每年上墳時(shí),每家每戶都要在墳地上栽一棵柏樹,遇到天旱要給柏樹澆水。逢年過節(jié)砍柏枝時(shí),只能剔枝杈而不準(zhǔn)傷主桿。 張光春的父親是張家這一族人的族長(zhǎng),近幾年身體一年不如一年,一旦走了,張家這一族人就要由張光春挑起族長(zhǎng)這副擔(dān)子,所以,去年上墳時(shí)他的父親當(dāng)著眾人給他作了交待,其實(shí)也是告誡大家要遵守這一條家規(guī)。 天放亮了。村頭電線桿上的木匣子響了起來,莊嚴(yán)、渾厚、激越、悠揚(yáng)的歌聲從木匣子里飄出,回響在槐樹溝的上空。那首歌是他們?nèi)巳硕紩?huì)唱也喜歡唱的《東方紅》。歌聲打破了清晨的寧靜,歌聲喚醒了沉睡的山莊,也喚醒沉思中的張光春。他知道歌曲之后就是傳達(dá)上頭精神的聲音,他得細(xì)細(xì)地聽聽。于是,張光春轉(zhuǎn)身匆匆地向那個(gè)木匣子走去。“現(xiàn)在播送《人民日?qǐng)?bào)》社論,題目是《乘風(fēng)破浪》”。女播音員圓潤(rùn)清脆的聲音通過那根細(xì)細(xì)的電線,從祖國(guó)的首都遙遠(yuǎn)的北京傳到了深山老林中的槐樹溝。那聲音甜甜的,脆脆的,充滿自信,給人以力量。張光春駐足靜聽。“我們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時(shí)間內(nèi),在鋼鐵和其它重工業(yè)產(chǎn)品產(chǎn)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guó),在這以后……準(zhǔn)備再用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時(shí)間在經(jīng)濟(jì)上趕上并超過美國(guó)”。趕英超美,多么偉大的戰(zhàn)略任務(wù),多么鼓舞人心的奮斗目標(biāo)!張光春聽著,有些激動(dòng)了,他感到身上的血液一股一股往頭頂上沖。美國(guó)佬有什么了不起?在朝鮮戰(zhàn)場(chǎng)上,我們用小米加步槍不就打敗了他們的飛機(jī)大炮?趕英超美用不了那么長(zhǎng)時(shí)間。張光春熱血沸騰,搓著雙手奔到村頭老榆樹下,當(dāng)當(dāng)當(dāng),敲響了老榆樹上吊著的那塊鋼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