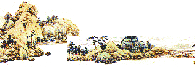|
|
|||
|
荒
|
||||
|
唐
|
||||
|
歲
|
||||
|
月
|
||||
|
□董新芳
|
||||
|
登記號:21-2001-A-(0656)-0115
|
||||||
張光春頭戴軍帽,身著草綠色軍裝,走起路來挺胸收腹,步履鏗鏘,單從背影上看嚴然是一位經過嚴格訓練的軍人。今天他刻意進行了裝扮,他要率領一個小分隊進軍平川,決不能萎萎縮縮,那樣有失井岡山兵團的氣概,有失井岡山兵團的雄風。尤其是在走資派面前,他要抖一下“井岡山”的威風。今天他帶領的隊員也是經過嚴格挑選的,身高都在一米七以上,著一色的黃軍裝,胳膊上的袖套也是展刮刮的,嶄新鮮紅。紅袖套上“井岡山兵團”五個黃色毛體大字龍飛鳳舞剛健遒勁。進軍平川,任務艱巨,他是奉趙書清之命去抓平川地委副書記龔亦平的。龔亦平是分管組織和干部工作的,他的一句話曾打破了趙書清坐縣委第一把交椅的美夢。地委在討論提拔趙書清為縣委書記時,龔亦平說趙書清作風飄浮,愛說大話。當一把手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穩重務實,踏踏實實地為老百姓辦實事辦好事。龔亦平說趙書清正是缺乏這一條。由于龔亦平的堅決反對,使趙書清的美夢落空。幾年過去了,趙書清仍耿耿于懷,他要借機來報這一箭之仇。這陣兒,揪斗走資派成風,借造反派之手報己之仇解己之恨豈不是一個高招!那天趙書清把張光春叫到他的辦公室,指著桌子上的一張報紙說,老張,咱縣的走資派已成死老虎了,再批再斗也沒啥意思。你看,現在平川地區的斗爭大方向已經明確,你們要積極參與進去,批判平川地區執行資產階級干部路線的代表龔亦平。張光春順著趙書清的手指望去,見報紙上確實點了龔亦平的名。張光春問,趙書記,龔亦平是地委副書記,咱們咋參與?趙書清說,你們造反派想想辦法把他揪到咱縣來批。張光春說,我不認識龔亦平,恐怕抓錯了。趙書清說,龔亦平有一個明顯的特征,你記住。張光春點點頭。趙書清說,龔亦平是個大高個兒,黑長臉,右臉上有一塊指頭寬的紫紅色的傷疤。平時身上總穿著一件退了色的黃軍裝。張光春領命之后進行了精心的準備,但能否完成這一重任,他心里仍沒有底兒。他從來還沒有跟這樣大的干部當面鑼對面鼓地敲打過。大躍進時到省上,那些大干部也只是禮節性地跟他握下手,友好地跟他點下頭。這次是抓人,而且是這樣大的干部,該咋開口,咋下手,他拿不定主意。他想打退堂鼓,又怕得罪趙書清。他當著趙書清的面曾經拍過胸口,說沒問題,回來了卻又下軟蛋,那不成了烏龜,濃包!他也會在趙書清眼里失去份量。張光春硬著頭皮也得上。張光春怕隊員們看出他內心的虛弱,故意做出雄赳赳氣昂昂天不怕地不懼的樣子,但到了地委大門口時,張光春的兩條腿象被抽去了筋似的有些發軟,不那么聽使喚了。地委的大門口站著兩位軍人,身子筆直,形象威嚴。張光春心里有些虛,也有些害怕,但他畢竟是當過兵的,略一鎮靜,決定改為第二方案(第一方案直接抓,第二方案瞞和騙)。張光春讓隊員們站到了一邊,自己走上前,禮貌地遞上介紹信,衛兵看過,用手指了指傳達室,示意張光春到傳達室去。傳達室里坐著一個五十多歲的模樣有點象干部的人,戴著一副老花眼鏡,他反復看過張光春的介紹信,并做了登記。然后跟張光春說搞外調用不著那么多人,去兩個就夠了。張光春花言巧語說了很多理由,最終準進四人。于是張光春選了三個機靈的跟他進去,并告誡說進去后少說話,一切看他的眼色行事。地委大院他還是第一次進來,但他從傳達室得知龔書記在二樓辦公。張光春直接上了二樓,在二樓過道里一個人的指點下,他們走進了龔書記的辦公室。龔書記正在閱讀文件,見有人進來,緩緩抬起了頭。張光春不看便罷,一看嚇得他膽肝俱寒,屁滾尿流,象老鼠見了貓一樣直往后退。這是他的恩人也是他的冤家。張光春的大腦里迅速閃現出了朝鮮戰場上那驚心動魄的場面。 美軍的飛機象一群烏鴉一樣黑壓壓一片,遮天蔽日狂轟濫炸。他們正在行軍。突然一顆炸彈象一個巨大的蘿卜在他的頭頂上空直瀉而下。臥倒!宏亮的聲音從他身邊發出,他雖然最先聽到,但他不是自己趴下的而是被這個聲音壓下的。隨著一聲巨響,泥土飛濺著象冰雹一樣從空中嘩嘩落下。敵機遠去,他抬起頭,發現連長趴在他的身上。他好好的,但連長的臉上被飛起的彈片削去了一塊生肉。連長的臉上流著鮮紅的血。連長的臉上包著一塊雪白的紗布。連長仍然邁著雄赳赳氣昂昂的步伐。傷好后,連長漂亮的臉蛋上留下了一塊永遠無法消失的傷疤。后來連長升了營長。在一次進攻戰中,他們連是尖刀,由營長親自率領。敵人龜縮在碉堡里,機槍吐著火舌,噠噠噠地射個不停,進攻受阻。炸掉它!營長一聲令下,一個手持炸藥包的戰士應聲沖了上去,但剛跑幾步就倒下了。接著又一個戰士沖上去,又倒下了……下一個輪到他了。上!營長命令。營長的這一聲命令,嚇得他褲襠里濕了一大片。他猶豫著遲疑著趴著沒動。一秒,兩秒,三秒……營長憤怒地一把把他抓起,舉起了手槍……他是在醫院里醒來的,后來做為傷員送回了祖國…… 張光春退到了那三個人的后面。龔書記抬起頭,迅速掃視了一下來人的臉,最后目光在張光春的臉上停下,凝視片刻。張光春覺得龔書記的目光似一把利劍刺得他臉上發疼,他的身子不由自主地顫了一下。就在龔書記的目光離開他的瞬間,他迅速地悄悄逃了出來。 “你們找誰?”龔書記和藹地問。 前面三個人等待著張光春的回答,但遲遲沒有聽到張光春的聲音,他們不約而同地回過頭,早已不見了張光春的身影。 “你們找誰?”龔書記又問。 “找地委領導。”一個機靈的小伙子回答。 “找哪位領導?” “牛書記。”又是那個小伙子回答。他以前曾聽說過地委有個牛書記。 “牛書記到省上去了。你們有啥事兒?” “那就算了。”說著,三個人轉身出門,心里暗自慶幸,這一關總算混過去了。他們象入室偷竊的盜賊被主人發現而又瞞過主人一樣暗自竊喜,同時又為未能得手而后悔。逃脫就是福。他們腳底象抹了油滋滋溜溜地往樓下竄。剛下幾個梯階,身后傳來了龔書記的聲音: “你們等等。” 他們象被使了定身法,立即停住了腳步,規規矩矩的站在原地。 “進來。”龔書記仍然態度溫和。 他們的心里開始慌亂,以為龔書記發現了他們的企圖,他們不想進去。但龔書記那溫和的命令,他們又咋敢不執行?他們誰也不愿走在前面,互相推著,最終還是說找牛書記的那個小伙子先進門。 “你們不是來了四個人,還有一個呢?”龔書記望著三個人的臉問道,聲音很輕。 “走了。”一個小伙子回答。 “他叫什么名字?” “張光春。” “張--光--春。”龔書記手摸額頭若有所思地慢吞吞地重復了一遍。忽然問道:“他是不是當過兵?” “對,當過。”還是那個小伙子回答。 “志愿軍?” “志愿軍。” “你們是哪個地方的?”龔書記轉換了話題。 “紅衛縣。” “紅衛縣。”龔書記重復了一遍。 “龔書記認識張光春?”那個機靈的小伙子問。 “不認識。”龔書記搖著頭。 三個人似乎都有些失望。 難道真的是他?龔書記這樣想。 難道真的是他?張光春這樣想。 回到縣上,張光春仍象驚弓之鳥驚魂未定,他對自己這次行動后悔不已。既然龔書記在了解他的情況,肯定把他認出來了,不然那犀利的目光為什么會在他臉上停留如此之久?張光春看得很清楚,龔書記在看他時不光目光異樣,而且臉上那塊紫紅色的傷疤微微抽動了一下。唉,真是冤家路窄!天地如此之大,宇宙如此之闊,共產黨咋偏偏把他這個老山東安排在河南省的平川城!大概他要倒霉了。人飛黃騰達是要經過艱苦奮斗的,人要倒霉是用不著費勁兒的,就象從山坡上往下走,不知不覺輕輕松松。禍事要來總是悄悄秘秘而不打招呼的。張光春抱怨自己運氣不好,揪斗龔亦平,這壺水還沒燒就起了鍋巴,這口涼水還未進口就塞了牙。但是張光春想錯了,不是他的運氣不好,而是他做下了不該做的事,倒霉是必然的,只是遲早而已。張光春在驚恐之中度日如年,如喪家犬一樣惶惶不可終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