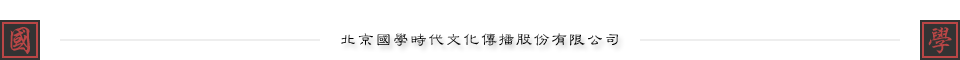古文點校著作權問題研究
——兼評“中華書局訴國學網案”等近期案例*
三、以復原古文原意為目的的點校不是著作權法意義上的“整理”
在認定點校結果為作品的案例中,法院均將點校結果劃入“演繹作品”的范疇。如“中華書局訴索易案”中,法院認定:
對古籍加注標點、劃分分段和校勘后所形成的作品,應屬于演繹作品的范疇。[21]
而這一結論的直接法律依據,就是《著作權法》第12條。該條規定:
改編、翻譯、注釋、整理已有作品而產生的作品,其著作權由改編、翻譯、注釋、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權時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權。
在“中華書局訴國學網案”中,一審法院對此認為:
《著作權法》作出上述規定的原因,就是為了在作品因語言、表達方式等因素不利于傳播時,以給予改編、翻譯、注釋、整理人著作權保護的方式,促進作品的傳播。在本案中,如果不給予原告保護,……有悖于《著作權法》第十二條的立法目的。故而本院認定原告對“二十五史”進行的包括分段、加注標點和字句修正的校勘工作屬于《著作權法》第十二條中的“整理已有作品”,其產生的中華書局本“二十五史”點校作品應當依法受到保護。[22]
(一)著作權法意義上的“整理”是指產生新作品的“改編”或“編排”
法院的上述觀點誤解了《著作權法》第12條中“整理”的含義。“整理”一詞直接源于《伯爾尼公約》。其第12條規定:
文學藝術作品的作者享有授權對其作品進行改編、arrangements和其他變動的專有權利。
arrangement一詞,在日常英語中有時被譯為“整理”。這應是我國《著作權法》第12條中“整理”一詞的來源。而《伯爾尼公約》中的arrangement并非“文獻整理”意義上的“整理”,而是特指能產生新作品的“改編”或“編排”。
對于這一含義,可從《伯爾尼公約》第2條第3款(其名稱為“演繹作品”)[23]的規定中得到印證,該款規定:
文學藝術作品的作者享有授權對其作品進行改編、arrangement of music和其他演繹行為的專有權利。
中國政府在批準加入《伯爾尼公約》時,向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提交的《伯爾尼公約》中文本中將該條中的arrangement of music翻譯為“音樂改編”,[24]這較為準確地揭示了arrangement的原義。[25]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僅僅在技術上對音樂進行調整,并不能形成受《伯爾尼公約》第12條保護的作品,因為該條款的名稱就是“演繹作品”(derivative works),僅對“演繹作品”提供保護。[26]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編寫的《著作權與鄰接權法律術語匯編》在解釋arrangement of music時指出:
該詞一般理解為根據特定的交響樂團或樂器的要求,或根據歌手的實際音域等情況調整音樂作品的表現形式,使之適于特定目的。其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將其他樂曲改成管弦樂曲,或者以不同的音調轉換樂曲,并不一定構成對演繹作品的創作。[27](著重號為筆者所加)
根據這一解釋,許多情況下對樂曲的刻意調整都不能產生“演繹作品”。如果僅是為了“復原”古文而進行的點校,又怎么可能作為“演繹作品”受保護呢?
《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簡稱TRIPS協定)中也出現了arrangement一詞,其第10條第2款規定:
對數據或其他材料的匯編,……只要由于對其內容的選取或arrangement(編排)而構成智力創作,即應作為智力創作加以保護。……
由此可見,TRIPS協定中的arrangement仍然是指能夠形成新作品(匯編作品)的編排行為。而在判斷是否形成了受保護的新作品時,前文所述的一系列著作權法的基本原理,如事實和對事實的思想觀點不受保護,以及“混同原則”等均完全適用。并非任何技術上對文獻的“整理”都可形成受保護的作品。換言之,對《著作權法》第12條的規定,必須結合著作權法基本原理進行解釋。
(二)《著作權法實施條例》對“整理”的不當定義已被刪除
從上文的分析中還可得出一個結論:《著作權法》將《伯爾尼公約》中的arrangement譯為“整理”,并未準確地反映arrangement的原意,容易引發誤解。1991年《著作權法實施條例》對1990年《著作權法》第12條中“整理”的定義就反映了這一誤解,[28]該條例第5條第(十二)項規定:
整理,指對內容零散、層次不清的已有文字作品或材料進行條理化、系統化的加工,如古籍的校點、補遺等。
如果這一規定仍然有效,則即使其明顯違反著作權法基本原理,法院也只能適用。[29]但該規定已于2001年修改《著作權法實施條例》時被刪除。這說明立法者已經意識到了“整理”在著作權法中的真實含義。在這種情況下,法院顯然不應當再適用這一已被廢除的規定,或該規定背后對“整理”的誤解。
對此問題,審理“鄭福臣訴大眾文藝出版社案”的法院指出:
對內容完整的古籍斷句和標點,是在遵循古籍原意的前提下,為方便現代人閱讀而在古籍中本應該停頓的地方用現代漢語中的標點加以標識,……因此這種標點行為并不是著作權法中規定的匯編、改編、翻譯、注釋、整理等任何一種演繹行為。[30]
這即是上文所述的,根據著作權法基本原理對《著作權法》第12條所作出的合理解釋。
四、保護“古文點校”成果的司法與立法對策
綜上所述,以“復原”古文原貌為已任的“古文點校”雖然可能包含獨創的智力成果,但基于事實和對事實的思想觀點不受保護等著作權法的基本原理,其并不能作為作品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然而,這絕對不意味著這類智力成果不值得保護。在“中華書局訴國學網案”中,一審法院將點校成果作為作品加以保護的重要原因,即是“如果不給予原告保護,將對我國古文點校行業造成負面影響,嚴重影響古文點校行業的積極性,有可能對古籍作品的傳播帶來非常不利的影響”。[31]法院這種對公平審判結果的追求本身當然是值得贊許的。
然而,著作權法并非保護智力成果的唯一途徑。對于不受著作權法保護的智力成果,其他法律機制是可能提供保護的。例如,思想觀點不受著作權法的保護,但“點子公司”向企業提供的解決經營問題的方案,卻可以受到合同法的保護。
在“鄭福臣訴大眾文藝出版社案”中,法院雖然認定點校者不能以其斷句和標點行為作為依據主張著作權保護,但同時指出“該種勞動成果應當作為一種民事權益受法律保護”;“在使用該勞動成果前應當征得許可,并以適當的方式表明勞動者的身份”。[32]該案法院以《民法通則》有關“公民的合法的民事權益受法律保護”的規定為依據,認定在未經許可和未表明點校者身份的情況下使用點校成果構成民事侵權。[33]這一裁判方法既遵循了著作權法原理,又合理維護了點校者的利益,是法院值得認真考慮的司法對策。
另一方面,如果希望在不違反著作權法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從著作權立法上徹底解決保護“古文點校”的問題,可以考慮在《著作權法》中增設“對特定版本的鄰接權”。
“鄰接權”的客體均非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而是與“作品”關系相近,具有應受保護的社會價值。例如,沒有人會否認對作品的成功“表演”需要表演者對作品的深刻理解和領悟,需要反復和艱苦的訓練,以及其對作品傳播的重要意義。但“表演”的智力創造程度與創作作品相比畢竟較小,因此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均不認為對作品的“表演”能夠產生“演繹作品”。[34]但為了保護表演者的勞動和利益,絕大多數國家通過規定“表演者權”這一“鄰接權”對表演者提供保護。
對古文或其他類型作品進行以“復原”為目的的點校或其他編輯行為,與對作品的“表演”有類似的社會價值,也需要專業知識、技能甚至是智力勞動的投入,有時還需要大量投資。其成果雖然不能構成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但完全可以通過設立“鄰接權”加以保護。
目前,許多國家的著作權立法都規定了對特定版本的鄰接權。西班牙《著作權法》第129條規定:已不再受著作權保護的作品的出版者享有以下專有權利:許可復制、發行和向公眾傳播其出版的特定版本,條件是該版本可以通過字體設計、排版或其他編輯上的特征得以識別。保護期為25年。德國《著作權法》70條規定:對于不享有著作權的作品或文本的版本如果是科學分析成果的體現,而且與先前公知版本顯著不同,則該版本的編輯者可受到保護。該權利的保護期為自該版本出版之時起算25年。例如,莎士比亞的戲劇可能有不同版本流傳,而編輯者在比較各版本的基礎上經過分析和勘誤,出版了經其編輯后其認為最為準確的一個版本,則該版本即能夠受到第70條的保護。意大利《著作權法》第85條之四也規定:公有領域作品的科學分析版本的出版者對該版本享有20年專有權利。
我國的古代文獻資料極為豐富,而絕大多數人只能通過點校版本閱讀。因此,古代文獻的點校者及出版者應當受到保護。借鑒國外著作權立法,借助此次《著作權法》修改的機會,增加一項“對特定版本的鄰接權”,既不違反前文所述的一系列著作權法基本原理——因為鄰接權保護的本來就不是“作品”,又能使點校者和出版者受到合理期限的保護,可謂最佳的立法對策。
注釋:
*本文為上海市教委第五期重點學科“民法與知識產權”(項目號J51104)的成果。
[1]在“中華書局訴大眾文藝出版社案”中,法院認為:“所謂古籍點校,是點校人在某些古籍版本的基礎上,運用本人掌握的專業知識,在對古籍分段、標點,特別是對用字修改、補充、刪減做出判斷的前提下,依據文字規則、標點規范,對照其他版本或史料對相關古籍劃分段落、加注標點、選擇用字并撰寫校勘記的過程”,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8)東民初字第09562號。
[2]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2)一中民終字第14251號。
[3]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1)朝民初字第17229號,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1)二中民終字第12056號。
[4]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7)海民初字第11897號。
[5]《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協定)第9條第2款明確規定:版權的保護僅延伸至表達方式,而不延伸至思想、程序、操作方法或數學概念本身。
[6]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1)海民初字第12761號。
[7]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1)海民初字第12761號。
[8]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4)一中民初字第297號。
[9]A.A. Hoehling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618 F.2d 972, at 974 (2nd Cir, 1980).
[10]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1)海民初字第12761號。
[11]該實例見《智海觀瀾:標點的妙用》,http://www.sxpmg.com/2011/0926/37659.html,2013年1月2日訪問。
[12]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2)一中民終字第14251號。
[13]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1)海民初字第12761號。
[14] A.A. Hoehling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618 F.2d 972, at 978-979 (2nd Cir, 1980).
[15]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4)一中民初字第297號。
[16]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8)東民初字第09562號,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9)西民初字第2978號。
[17]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1)海民初字第12761號。
[18]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2)一中民終字第14251號。
[19]參見維基百科中“契丹文”詞條,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91%E4%B8%B9%E6%96%87,2013年1月2日訪問。
[20]見署名為“天南地北之子”的博文《破解契丹文——贊裴元博先生》,http://blog.sina.com.cn/lujun130031,2013年1月5日訪問。
[21]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4)一中民初字第297號。
[22]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1)海民初字第12761號。
[23]該名稱是《伯爾尼公約》自身就有的,并非學者們對條文內容的總結。
[24]該中文本載于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網站,http://www.wipo.int/export/sites/www/treaties/zh/docs/berne.pdf
[25]與此相對應的是,該中文本將《伯爾尼公約》第12條中的arrangement也譯為“音樂改編”。
[26]參見劉波林譯:《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1971年巴黎文本)指南》(附英文文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頁。
[27]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編,劉波林譯,《著作權與鄰接權法律術語匯編(中英法對照)》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頁,本書作者的翻譯與該書的中譯本略有不同。
[28]1990年《著作權法》第12條與現行《著作權法》第12條相同。
[29]事實上,在該條被刪除之前,確實出現過根據該條認定“古文點校”的結果是作品的案例。如在“陳智超訴北京大學、上海古籍出版社案”中,法院認定:“為已有作品進行校點整理,凝聚了校點人員的智力創作。依照我國著作權法及其實施細則的規定,校點屬于整理行為,整理作品的著作權由整理人享有”,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1)海知初字第9號。
[30]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1)朝民初字第17229號,第9頁,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1)二中民終字第12056號。
[31]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2)一中民終字第14251號。
[32]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1)朝民初字第17229號,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1)二中民終字第12056號。
[33]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1)朝民初字第17229號,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1)二中民終字第12056號。
[34]需要指出的是:美國的情況在此方面與其他國家不同。美國版權判例一直認為,表演音樂作品的行為本身就是創作,可以形成有“獨創性”的作品,See Capitol Records, Inc. v. Mercury Records Corp., 221 F.2d 657, p. 664 (2nd Cir., 1955), Melvile B. Nimmer& David Nimmer, Nimmer on Copyright, Matthew Bender & Company, Inc. (2003), §2.10 A(2)(b).但同時需要指出的是:對音樂作品之外其他類型作品的表演,在美國卻不被認為是創作,也不能形成作品。
(作者單位:華東政法大學)?
文章分頁: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