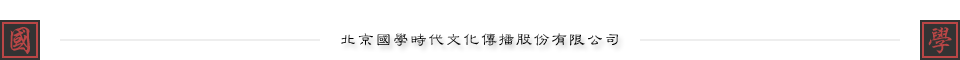國學三題
什么是國學
國學是什么?大家好象都清楚;但一具體到什么是國學?好象又說不甚清楚,仿佛是有點可以意會難于言傳似的。翻檢幾部新舊版的《辭海》、《辭源》一類工具書,對“國學”一詞的定義均謂:“本國固有之學術也。”顯然,這種釋義比較抽象,仍給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感覺。那么究竟什么是國學?國學一詞的本源何在?國學所包攝的內容范圍又是哪些呢?關于這類提問,我想援借牟潤孫先生關涉到“國學”的一文內容作答:
——所謂“國學”,其實是一個來自外國的名詞,外國人研究中國問題,自稱為“漢學”Sinology,文字、語言、歷史、地理、考古、民俗、美術無所不包。中國人辦研究所,自然不能用“漢學”兩個字,于是改稱“國學”。幾十年來積非成是,大家沿用不疑……雖然中央研究院不用“國學”這個名稱,而人們心中所向往的仍是外國人的“漢學”,經過北大、清華,到史語所成立,清代考據余風與外國“漢學”很容易地結合起來,成了“五四”以后中國文史之學發展的根源。(摘引《敬悼陳寅恪先生》一文,原載臺灣《新夏》雜志第11期,1970年5月臺北出版)
略需說明的是,“五四”以后,胡適先生首倡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北京大學率先創辦研究所,成立“國學門”。嗣后,清華大學仿北京大學開辦國學研究院,禮聘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四大導師,開啟了一代學風。站在今天來回顧昨天,幾十年來文科的頂尖人才主要源于清華研究院,理科的問鼎人物則主要出自西南聯大。此是題外話。再其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相繼成立,這也就是文中所說的北大、清華、史語所。在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國學研究之風大盛,有關國學研究的刊物如雨后春筍,達幾十種之多,在當時的學術界,國學之研討成了一種蔚為大觀的氣象。檢閱歷史故實,我以為牟先生對“國學”一詞的解說正名是可信的。
國學與國學家
“國學”的基本概念已如上所述。國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源頭來自清代的考據之學。有清一代形成的學術風尚,主要體現在乾嘉諸老的考據之學上。清儒治學講求證據,即所謂“訓詁明義理明”也。顧頡剛先生亦曾說過:考據文章好,好在說話有證據。考據之學又名“樸學”,即樸實之學,它本是針對晚明以來日見空疏的心性之學的一次反撥,但它發展的結果,卻形成了學脈學派,可謂“無心插柳柳成行”,影響十分深遠。可見一種學術生命的延續,主要是靠發“內功”,它可能會受到外因的影響,在此時得勢,在彼時失勢,但它的學術價值卻是恒久的。從上世紀二十年代始,在中國學術界被公認的幾位國學大師,基本上亦是承續了清代考據之學的風緒,但又不同于清儒汲汲于訓詁考訂,而是更上一層樓。如章太炎先生及稍后的錢穆先生,他們在治學的方法上,均是以考據為基礎,然又不是專治一曲,而是期于淹貫博通,冶文史哲、儒釋道于一爐,既博大又精深。
中國的學術傳統,比較注重于“通”;西方的學術傳統,卻更強調于“專”。這是由于學術文化背景的根本不同所形成的。在現代社會學術分工日趨細密,學科分支日見紛繁,專家之學是理在必然,但從事物的另一面來看,通人之學就更顯稀罕。何謂“通人”之學?葛洪在《抱樸子·尚博》篇中有一解說:“通人總原本以括流末,操綱領而得一致焉。”并斥陋儒不能認識通人博雜的真正價值,“或云小道不足觀,或云廣博亂人思,而不識合緇銖可以齊重于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于億兆,群色會而袞藻麗,眾音雜而韶濩和也。”葛洪指出了通人之學能考鏡源流、舉綱張目的高明處。綜觀被譽為“國學大師”者,其共有之特點,無不皆是學兼四部、出入經史、騰踔百家的通儒碩學。
近幾十年來,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學術界多不用“國學”一詞,對所謂“國學家”也不大以為然。國學與國學家隱隱然代表著一種文化守舊,多少還蘊含有一點貶意。這本是一種偏見,一種不該出現而實際出現的偏見。
國學研究的現實意義
隨著時代的進步,學術研究應該貼近時代,好的學說思想還應該對社會發展起積極指導作用。否則,任何一種好思想好學說,一旦脫離實際遠離社會,只能是一種裝飾品、點綴品,最終有可能會淪為毫無生命的木乃伊。
我們今天所講的國學研究,在方法上應該不囿于清人的考據之學,在意義上應該有更大的現實針對性。現在倡導弘揚優秀的傳統文化,這其中就有一個辨別、繼承與發展的關系問題。中國的傳統文化,實質上是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倫理道德型學說,盡管道家的思想源遠流長,但相對而言它不占有主導地位。《易經》里講乾坤陰陽,揭示宇宙萬物之生命運動,儒道兩家的宇宙觀俱源于此。儒家比較傾向于乾卦之“自強不息”,而道家比較傾向于坤卦之“厚德載物”,儒家陽剛進取,道家陰柔退守,兩者相輔相成,可謂平分乾坤。儒家比較注重社會奉獻,道家比較著重個人自由,因此道家的思想在民間有比較廣泛的基礎,但在上層建筑領域里卻未產生過真正意義上的影響作用。現在一說到“弘揚”,當不可不辨良莠,不分巨細,單是儒家的思想,有精華也有糟粕。如儒家講“三綱五常”之倫理,“三綱”中首先講的“君為臣綱”,就無法開出現代民主。過去十億人的大國,共用一個頭腦思考,興衰成敗定于一尊,殷鑒未遠,教訓深刻。“父為子綱”則容易釀造出畸形的血統論。“夫為婦綱”之本身定位就顯示出男女不平等。可見“三綱”思想與現代社會已格格不入。而“五常”所倡的“仁、義、禮、智、信”,在人欲橫流、物欲橫流的今日社會,似能起到道德自律的作用,因此它仍具有積極的正面價值。如何正確地對待中國固有的學說思想,我以為當代新儒家提出的“創造性的轉化”一說較宜,或可使之適應于現代社會的發展。
我們現在所講的國學,實際上是講的更廣意義上的傳統文化。時代不同,研治的方法、意義都應該有新的大的改變。講國學在現代社會中的價值意義,必須注意兩個方面:一是認識,一是研究。沒有認識,就談不上研究;沒有研究,更談不上弘揚。今天研治國學,應該不只是停留在整理國故,文化積累的層面,更應該著眼于傳統與現代的接榫通軌,打通經脈,古為今用,去粗取精,推陳出新,俾使優秀的學術思想之花結出豐碩的文化生命之果來。
(原載《東方文化》1996年第一期)
附記:拙稿《國學三題》,原是十多年前分別發表于《大公報》及《東方文化》雜志上的舊作。日前,因故重檢舊作,覺得當年的看法似未完全過時,于是央人照原文打印錄制,有意以舊文新刊于“國學網”上。希望對于厘清國學概念,能夠起到一點參考輔助作用。2009年8月20日記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