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夢家是中國大陸于簡牘學方面有顯著的突出貢獻的學者。他主持了武威漢簡的整理和校勘,推定其中的《儀禮》簡為與二戴本有所不同的慶氏本,第一次比較全面地將簡牘研究與文獻研究結合起來,使傳統文獻研究在方法上有所革新,也使簡牘學的研究領域有所擴展。陳夢家又曾經負責《居延漢簡甲乙編》的編纂工作。對于居延漢簡的研究,他改進了以往就簡牘論簡牘的方式,重視簡牘出土地點的分析,于是將簡牘學從單純的文字研究和文書研究,提高到科學地運用現代考古學理論與方法的高度,提高到通過簡牘資料的研究,從較寬層面認識歷史文化的高度。學術界對于漢代的簡冊制度、烽燧制度、郵傳制度、職官制度、紀時制度的認識,都因陳夢家的研究而得以深入。他承擔敘論、校記、釋文的《武威漢簡》,以及漢簡研究專著《漢簡綴述》,已經被看作簡牘整理和簡牘研究的經典。
由于陳夢家的工作成績,中國大陸的簡牘研究,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并不落后于海外,而此后大陸地區的簡牘學,也因此具有了良好的學術基礎和合理的科學導向。
一 簡牘學研究與歷史文獻的整理
陳夢家從一九六○年開始從事簡牘學研究。
一九五九年七月,甘肅武威出土大批漢簡。甘肅省博物館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支援整理。時任所長的夏鼐委托陳夢家擔任這項工作。一九六○年六月至七月間,陳夢家前往蘭州參加了這批簡的整理和研究工作。[1]有的學者在回憶文章中寫到當時的情形,“要把這批出土的散亂殘斷的竹木簡,加以整理復原,并確定它是一本今已失傳的《儀禮》本,這首先需要臨摹、綴合、校刊等技術性的工作,任務是艱巨的。當時博物館的新館還沒有蓋起來,只在一間倉庫樣的工房內工作。”“時值盛夏”,陳夢家“不分上下班,晚上在燈光下用放大鏡俯身工作”。當時不僅物質條件十分困難,陳夢家還承負著不能個人發表文章,不能對外聯系等精神方面的壓力。“但他全不計較,發揚古代文化的責任感促使他忘我地工作,僅用了三個月的時間便完成了任務。一九六二年出版了《武威漢簡》一書,供學術界研討。”[2]
據陳夢家的同事回憶,自參與并主持武威漢簡的整理和研究之后,“夢家先生的研究興趣,陡然從金文銅器方面轉到了漢簡方面。”一位學養深厚的,已經在古文字學、青銅器學、古文獻學等領域取得重要成果的學者[3]熱情投身于簡牘學研究,這實在是中國簡牘學的幸事。
由于逐漸形成了利用陳夢家的研究成果為基礎,遵循陳夢家的研究范式進行工作的簡牘學研究羣體,方才使得此后若干年考古發掘中出土的大批簡牘數據具備了可以進行整理和研究的前提。后來李學勤所提出“對古書的反思”[4]、“走出疑古時代”[5]等論點所體現的利用新出簡牘資料的歷史文獻研究的進步,正是以此為條件的。
武威漢簡本《儀禮》的發現,是二十世紀簡牘佚籍第一次比較集中的發現。武威漢簡本《儀禮》的整理,也是中國歷史文獻學在二十世紀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
陳夢家在歷史文獻研究方面的成果,原已有《老子今釋》[6]、《尚書通論》[7]等多種。[8]郭沫若曾經考論《周易》的“經部作于戰國初年的楚人馯臂子弓”,而《易傳》“著書的年代當得在秦始皇三十四年之后”。他以為八卦的構成時期不在春秋以前的主要論據,是金文中“決不曾見有天地對立的表現”,“確實可靠的春秋以前的文獻也沒有天地對立的觀念”。[9]對于郭沫若有關《周易》成書年代的推定,陳夢家指出,天地上下對立的觀念發生很早,甲骨卜辭中有牝牡合書,左右對稱諸例,有“下上若”的說法,金文亦見此例,這就是上天下地之意。郭沫若以春秋前不可能存在天地對立的觀念而斷言《易》之不產生于春秋之前,是缺乏力證的。陳夢家指出,“《易》無成于春秋中葉以后的確證。而《史》《漢》所敘傳《易》系統中的馯臂子弓亦自無理由認為作《易》者。”[10]就《易》學而言,陳夢家的許多論著其實都有所涉及。李學勤《周易經傳溯源》引錄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11]、《西周銅器時代》[12]、《六國紀年》[13]等專著以及《解放后甲骨的新資料和整理研究》[14]、《戰國楚帛書考》[15]等論文,共計十三處之多。[16]可知陳夢家的學術工作對《易》學進步確有貢獻。
可以看到,陳夢家以實踐體現出對王國維“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于新發見”,“紙上之學問頼于地下之學問”以及“二重證據法”的主張的信服和遵從。他以敏鋭的學術眼光,發現甲骨文數據、金文數據和帛書數據的文化價值,并且認真投入研究,不久就成為這些領域公認的專家。從這一角度說,他始終站在學術的前沿,始終勤于探討,勇于攻堅,于是成為成就卓著的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
陳夢家重視全面的學術訓練,重視從不同角度切入,以探索古代文化。在談到研究古史的道路時,他曾經說:“在工具方面,沒有小學的訓練就無法讀通古書,無法利用古器物上的銘文;沒有版本學和古器物學的知識就無從斷定我們所采用的書本和器物的年代;沒有年代學、歷法和地理作骨架,史實將無從附麗。”[17]正是因為對古代文化多層面、多方位的關注,使得他在并非專意研究古文獻時,也能夠通過對古文字學、古器物學、古史年代學、古歷法學以及歷史地理學的探討,極大地推進了歷史文獻的研究。
在討論馬王堆帛書《周易》的卦序卦位時,李學勤提到陳夢家的簡牘學研究成果:
關于“帝出于震”章的來源,至少有兩條線索可尋。
《漢書·魏相傳》云:“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表奏之,曰:……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所述五方之神本于《月令》,而八卦方位與“帝出于震”章相合,陳夢家先生考定此奏在漢宣帝元康年間,距《說卦》的出現不過幾年,所謂《易陰陽》可能是另一種《易》書。
關于陳夢家先生的“考定”,李學勤注:“陳夢家:《漢簡年歷表敘》,《漢簡綴述》,中華書局1980年。”[18]這只是陳夢家的簡牘研究收獲應用于歷史文獻研究的一例。
陳夢家直接以簡牘研究推進歷史文獻研究的工作,當然是武威漢簡的整理和研究。
1959年7月,甘肅武威磨咀子六號漢墓出土漢簡四百八十枚,以木簡居多,竹簡較少。其中除十一枚為日忌及雜占簡外,其余四百六十九枚均為《儀禮》簡。[19]武威出土的漢簡《儀禮》,被認為是“從所未有的發現”。如陳夢家說,“先秦典籍的原本,今已無存。今欲見漢代典籍的面貌,大約不外帛本、簡本、紙本和石本。帛本、紙本未有出現,而近世在洛陽故城南太學遺址所出的熹平石經,其中雖有《儀禮》殘石,散在四方,就可以搜集到的僅有數百字(詳《漢石經集存》第三九二至四七○號)。今此所出《儀禮》,竹簡、木簡并有,存四百六十九簡,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二字,首尾完整,次第可尋,實為考古發現上非常的一件大事。”[20]后來簡本和帛本漢代文獻屢有發現[21],當然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所能預見,但是武威漢簡《儀禮》發現的意義和整理的功績依然未能稍減。
武威漢簡《儀禮》甲、乙和丙本不但有竹、木之異,它們之間的內容亦有所異,甲、乙本是《服傳》而丙本是《喪服》經記。甲本七篇篇首題記篇題篇次,反映其編次和今本編次不同,和兩戴本及劉向《別錄》本亦不同。不但篇次不同,篇題亦有所異。陳夢家指出,“甲本將士禮置于前半,而將諸侯大夫禮置于后半,其先后次第似有勝于兩戴與《別錄》者。”[22]
經過整理和研究判定,“武威出土甲、乙、丙三本《儀禮》九篇,除甲、乙本《服傳》和今本有很大的出入外,其它甲本六篇和今本大略相同,丙本《喪服》經、記同于今本。但它們的篇次既不同于兩戴,又不合于《別錄》、鄭玄,它只可能是三家以外的一個家法本子。” [23]陳夢家認為,根據文詞和字形的考察,“這個本子也很可能是慶氏《禮》,故其經文不甚離于今本,其文句略同于今本,而其字形有異于兩戴本和今古文并存的今本者。”[24]
陳夢家為《武威漢簡》所寫的《敘論》,全文凡十一萬三千字,又《校記》六萬字。作為《儀禮》研究來說,完成了份量最為充實,而質量亦尤為優異的研究論著。
利用簡牘資料研究歷史文獻,陳直的《漢書新證》和《史記新證》有值得稱道的貢獻。陳直《漢書新證》即“以本文為經,以出土古物材料證明為緯。使考古為歷史服務,既非為考古而考古,亦非單獨停滯于文獻方面”,“有百分之八十,取證于古器物”。陳直所做工作,以“證”為主,其中也涉及對歷史文獻的校訂。我們說用考古資料考訂和校正歷史文獻,自然以簡帛本文獻的發現最值得重視,這涉及簡帛的版本學價值的問題。李學勤說,盡管出土簡帛文獻“就有傳本的幾種而言,其與傳本的不同,不一定是簡帛比傳本好”,然而通常說來,“新發現的簡帛書籍大多數是佚書秘傳,年代又這么古遠,自然是不容置疑的善本。”[25]研究保存較完整的簡牘本文獻,陳夢家進行了富有開創性的工作。此后卓有成就的新發現先秦秦漢簡帛文獻的研究,從某種角度來說,其實都是陳夢家的事業的繼續。陳夢家的武威漢簡《儀禮》研究,在一定意義上為簡帛佚籍研究確定了一種樣式,一種規范,一種標尺。
陳夢家的武威漢簡《儀禮》的研究,還引發了有關《儀禮》研究的有意義的討論。沈文倬不同意陳夢家以為武威《儀禮》為慶普本的意見,認為簡本《儀禮》是“古文或本”[26]。高明通過對武威簡本《儀禮》的研究,考察兩漢時期今古文的實質和變化,得出結論:武威簡本《儀禮》是目前所見第三個漢本;據校今古文及簡本的差異主要是各自使用本字和假借字;東漢今古文的分歧實質是兩派解經對經文的諧聲字取舍不同。[27]
二 簡牘學研究與古代制度的復原
1957年,勞干的《居延漢簡圖版之部》在臺北出版。三年之后,1960年,他的《居延漢簡考釋之部》也得以面世。1959年,在陳夢家主持下,據馬衡保存的 148版圖版,計二千五百多枚簡牘,整理出版了《居延漢簡甲編》。《甲編》中所收部分簡牘,是勞干的論著中所沒有的。以這兩部書,以及貝格曼去世后由斯德哥爾摩民族學博物館東洋部部長索馬斯達勒姆(Bo Sommarstrom)整理出版的《蒙古利亞額濟納河流域考古研究》為依據,內容完整的《居延漢簡甲乙編》得以于1980年出版。《居延漢簡甲乙編》出版后,使簡牘學研究層次的深入和研究領域的拓寬得到了新的條件,許多研究者相繼發表了有關居延漢簡的專著和論文,涉及漢代史研究的論著,也普遍開始重視利用簡牘數據。
應當看到,大陸的漢史研究,因《居延漢簡甲編》的出版得到了新的契機。如果考慮到大陸經歷1966年開始的十年動亂的特殊背景,注意到“文革”后恢復高考最先入學的歷史系七七級、七八級史學新人當時只能通過這部書接觸簡牘資料,則《居延漢簡甲編》的學術意義更應當得到肯定。
在1962年初,《武威漢簡》的編寫工作最終完成之后,陳夢家接著便集中精力,對居延漢簡、敦煌漢簡和酒泉漢簡進行了整理工作。其中包括對居延漢簡的出土地點與額濟納河流域漢代烽燧遺址的分布和形制的研究。其意義對于簡牘學至為重要,是因為這一工作第一次使得中國簡牘研究正式置于現代考古學理論與方法的基點上。從1962年初到1966年9月逝世前,在三年多不滿四年的時間里,陳夢家共完成了十四篇論文,約三十萬字。[28]
應當說,主要是居延漢簡研究的成績,使得陳夢家成為公認的大陸簡牘學研究者中成就最為突出的學者。陳夢家推出的研究論著,使得大陸簡牘學研究邁進到新的階段。
陳夢家有關居延漢簡的論文,在他生前已經發表五篇,即《漢簡考述》[29],《漢簡所見奉例》[30],《漢簡所見居延邊塞與防御組織》[31],《漢簡年歷表敘》[32],《玉門關與玉門縣》[33]。由于其研究成果的數量和質量,陳夢家在當時的簡牘學研究中已經成為公認的學術權威。
在一九六六年九月逝世前,陳夢家又完成了九篇研究漢簡的論文。即:《漢簡所見太守、都尉二府屬吏》,《西漢都尉考》,《關于大小石斛》,《漢代烽燧制度》,《河西四郡的設置年代》,《漢武邊塞考略》,《漢居延考》,《西漢施行詔書目錄》、《武威漢簡補述》。這九篇生前尚未發表的論文,加上已經發表的五篇,以及原先作為《武威漢簡》中的一章的《由實物所見漢代簡冊制度》,共計十五篇,編為《漢簡綴述》一書,于1980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據此書編者的《編后記》,沒有發表的九篇論文,“有的是初稿,有的已修改謄清,看來當時夢家先生是準備將它編輯成冊的,《漢簡綴述》就是他自己題的集名。”[34]有的學者則說,陳夢家“親自將其集結為《漢簡綴述》一書”。[35]
陳夢家在談到作著《殷虛卜辭綜述》時,曾經說道:“作此書時,曾時常注意到兩件事:一是卜辭、文獻記載和考古材料的互相結合;一是卜辭本身內部的聯系。”[36]他在進行漢簡研究時,依然“時常注意”這兩個方面。同時,通過漢簡研究,考察當時的制度,尤其為陳夢家所關注。他在《漢簡考述》中寫道:“我們在整理漢簡的過程中,感到漢簡的研究不僅是排比其事類,與文獻相比勘或者考訂某些詞、字或片斷的歷史事件,而需要同時注意以下諸方面:第一,關于出土地問題,即遺址的布局、建筑構造,以及它們在漢代地理上的位置。”“第二,關于年歷的問題,利用漢簡詳確的排列‘漢簡年歷表’,可以恢復兩漢實際應用的歷法。”“第三,關于編綴成冊和簡牘的尺度、制作的問題。”“第四,關于分年代、分地區、分事類研究與綜合研究相互結合的問題。”陳夢家說,“凡此皆需先加分別,然后才可綜合不同年代、不同地區的漢簡,互相補充,全面的研究表現于漢簡上的官制、奉例、歷制、烽火制、律法、驛傳關驛等等,并與文獻互勘,用以了解漢代經濟的、社會的、軍事的種種面貌。”[37]
《漢簡綴述》正是循這樣的思路從事考察,充分利用簡牘材料,對于漢代的政治制度、軍事制度、郵驛制度進行了說明的。
對于武威郡以及武威郡治姑臧的考論,已見于《武威漢簡》之《敘論》。[38]《河西四郡的設置年代》一文又依據簡牘數據,分別為河西四郡設置作時間定位,訂正了史籍記載的錯誤。此外,《玉門關與玉門縣》、《漢武邊塞考略》、《漢居延考》等論文,都是軍事歷史地理的專論。陳夢家在這組論文中從不同層次說明了漢代河西作為重要的政治歷史舞臺的形成過程。因為是以出土簡牘作為主要研究資料的,所以其結論的可信度相當高。這一方面的研究的重要性,正如陳夢家所說,“沒有……地理作骨架,史實將無從附麗”。《漢簡考述》一文的第一篇“額濟納河流域障塞綜述”,第二篇“郵程表與候官所在”,也是以地理“作骨架”的工作,從而為進一步的研究準備了基本條件。
同樣,如果沒有“年代學、歷法”“作骨架”,“史實”也“將無從附麗”。也就是說,如果只有空間的定位,沒有時間的定位,則歷史認識的基點仍然不存在。陳夢家利用居延漢簡所進行的關于“年代學、歷法”的研究成果,有題為《漢簡年歷表敘》的論文。
《漢簡所見居延邊塞與防御組織》在《漢簡考述》部分恢復漢代居延邊塞防御組織的基礎上,又做了進一步的工作。所使用材料,以居延簡為主,也部分利用了敦煌簡和酒泉簡。陳夢家強調,漢代北方諸郡,由于地理上、軍事上和經濟上的關系,和內郡在組織上稍稍有所不同。出于防御武備、屯田、轉輸以及處理民族關系的需要,“邊郡守除了直轄諸縣民政外,還要管轄二或二以上的部都尉,而在其境內存在有受制于中央大司農、典屬國的農都尉和屬國都尉。邊郡太守府和內郡一樣,有一套治事的官僚組織,即閣下和諸曹,另外又有倉庫。太守所屬的部都尉,也是開府治事的,它也有略同于太守府的官僚組織,即閣下和諸曹;除官僚系統外,它有候望系統(候、塞、部、隧),屯兵系統(城尉、千人、司馬),屯田系統(田官),軍需系統(倉、庫)和交通系統(關、驛、郵亭、置、傳、廄等)。后者或者屬于郡。”[39]陳夢家還指出,邊郡太守兼理本郡的屯兵,其所屬長史專主兵馬之事。在其境內的屬國、農都尉,雖然在系統上屬于中央典屬國與大司農,但是也兼受所在郡的節制。至于部、郡都尉,則直屬于郡太守。張掖郡屬下的兩個部都尉,各守塞四、五百里,凡百里塞設一候官,有候統轄而與塞尉直屬若干部;部有候長、候史,下轄數隧;隧有隧長,率卒數人。[40]這篇論文,主要論述了防御組織中的候望系統,亦兼述屯兵系統的一部分,以簡牘數據與文獻記載相結合,將有關組織的結構體系,大體已經梳理清楚。
對于邊郡太守府和都尉府的官僚組織和屬吏,文獻記載雖有涉及但是不免闕失疏略。陳夢家在《漢簡所見太守、都尉二府屬吏》一文中就此專門進行論述。此項研究據陳夢家自述,“以漢簡為主而與史書相印證,并利用少數的漢代銅器、碑刻、封泥、印璽上的銘文稍加補充。它對于西漢晚期和東漢初期的邊郡官制,提供了比較詳備的系統。”[41]重視多種文物數據的綜合利用,并且結合“史書”記載,以相互印證,這種方法在漢史研究中的運用,曾經先有楊樹達《漢代婚喪禮俗考》和《漢書窺管》的范例[42],而陳直的《漢書新證》和《兩漢經濟史料論叢》等論著其應用尤為練達[43]。而陳夢家在漢簡研究中注意“以漢簡為主而與史書相印證”,同時又“利用”其它文物數據以為“補充”,這一方法對于漢簡研究者的啟示意義無疑也是顯著的。
關于漢簡官制研究,陳夢家又有《西漢都尉考》一文。他指出,部、農、屬國都尉和少數騎都尉都是邊郡防御的重要設置,其分布和興廢都有關兩漢邊防守備的興衰。[44]這一研究,也豐富了我們對于漢代制度的認識。
可以反映當時社會政治生活和社會經濟生活若干重要信息的漢代所謂奉給或吏祿制度,其內容包括秩級、奉祿數量、官職和奉祿性質。陳夢家以河西出土漢簡補充文獻記載之不足,在《漢簡所見奉例》一文中總結了兩漢時期有關制度的變化,他指出,“兩漢奉例的變化可分為以下諸期:(一)漢高祖末及惠帝初,因秦制以石為秩,初具二千石至佐史諸秩等第。(二)武帝末至西漢末以錢為奉,間代以布帛,其間秩名減除、官職秩級有升降,三百石以下兩度益奉什五。(三)王莽(新)承西漢奉錢之秩,最后六年曾企圖以谷物代錢為奉,建武二十六年以前似受其影響。(四)東漢建武二十六年四月創立半錢半谷奉例,施行至東漢末,未有變更,延平例中所見半谷為半米。”“由此可知班固《漢書·百官公卿表》所代表的,往往是班固當時理解的西漢之制,不盡符合不同年代稍稍改易的地方,其例與《地理志》相同。”官員的秩級與奉祿,是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的重要構成內容,《漢簡所見奉例》一文使兩漢奉例的歷史演變趨勢得以明朗,實是對于漢代制度研究的重要貢獻。陳夢家在文章結尾處自謙地說,“作者初治漢書,很不熟悉,而漢簡數據又尚待系統整理,因此本文所涉論的必有不少錯誤,希望讀者指正。”[45]雖然隨著資料的日益增多和研究的逐步深入,對于這一制度的認識也一定有所推進。但是陳夢家的工作對于此項研究的貢獻,有必要給予充分的肯定。
漢代烽燧制度應用于軍事防御和信息傳遞,是當時體現先進技術的一種文化存在。有關漢代烽燧制度的研究,王國維、勞干、賀昌羣等學者曾經各有專論。[46]陳夢家搜集較多的漢簡資料,對諸家之說有所補正,實際上大大推進了這項研究的深入。他在《漢代烽燧制度》一文中就烽臺的建筑、烽火記錄、烽具、烽火品、烽燧的設置和烽燧的職責六個方面對漢代邊防烽燧體系的結構和作用進行了全面的總結。陳夢家所進行的漢代制度前與《墨子》城守之法后與唐代《烽式》的比較,對于全面認識漢代烽燧的形制有積極的意義,對于簡牘研究的方法,也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樣板。
三 簡牘學研究與社會文化的考察
在陳夢家的學術工作中,古文字的考證,古器物的考證,古文獻的考證,往往都并非就文字而文字,就器物而器物,就古書而古書的研究,而最終都歸結于對中國社會文化的考察,對中國社會文化的理解。他的《殷虛卜辭綜述》的許多章節,其實都是通過文字和器物,展示了社會文化的多彩的畫面。陳夢家的簡牘學研究,同樣與有些學者從字到字,從簡到簡,從物到物的慣式不同,而是于具體的研究之中,透露出他對社會文化的深刻體味,對社會文化的宏大關懷。
《武威漢簡》的“釋文”部分有“雜簡及其它考釋”一節。其中首先是“日忌、雜占木簡考釋”。列有“日忌木簡”七枚,“雜占木簡四枚”:
一 河平□〔年〕四月日諸文學弟子出谷五千余斛 六(背)
□□□不乏蹇人 買席辟壬庚 河魁以祠家邦必揚 (正) 日忌木簡甲
二 甲毋置宅不居必荒 乙毋內財不保必亡 丙毋直衣□…… 日忌木簡乙
三 丁毋威□□多作傷 戊毋度海后必死亡 己毋射侯還受其央 日忌木簡乙
四 〔庚〕…… 〔辛〕…… 壬毋□□必得 日忌木簡乙
五 〔辰〕毋治喪 日忌木簡丙
六 午毋蓋屋必見火光 未毋飲藥必得之毒 申毋財衣不煩必亡 日忌木簡丙
七 酉毋召客不鬧若傷 戌毋內畜不死必亡 亥毋內婦不宜姑公 日忌木簡丙
八 □有生財有吏事 有惡言者有客思之有諦泣 令人遠行 雜占木簡
九 ……有憙事 君思之 君子思之 有憙事 令人得財 雜占木簡
十 ……有 取有 之者有風雨 雜占木簡
十一 ……見婦人 雜占木簡
陳夢家隨后有約五千字的考論。如分析簡一,指出“河魁乃十二神中之土神,主疾病”,“據出土簡,知漢世有祠河魁之俗矣。”又指出,“‘以保家邦’之邦不避諱,同出《儀禮》簡則皆避之,知民間卜筮書可不避也。”陳夢家還寫道:“另有一簡,過殘。又有席片一,上亦有墨書跡。”這些現象,也值得研究者參考。對于河西漢簡中所見“占書、日禁之書”等,陳夢家分析說,“漢俗于日辰多忌諱,又信占驗之術,王充譏之。《后漢書·張奐傳》謂‘武威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日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所謂妖忌乃土著之所信奉,而統治階級之迷信實無所異。此改風易俗之張奐,在武威任內生子猛,占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后果驗云。不信民間之忌而信占驗之術,此所以此墓主雖為飽學經師而于日禁之書有死生不能忘者,故與所習儒書同殉焉。”[47]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五篇說:“中國本信巫,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而鬼道愈熾”。[48]應當說,在整個漢代,巫風和鬼道都全面影響著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陳夢家對于武威漢簡“占書、日禁之書”的分析,也是這一時代文化特征的具體說明。
睡虎地秦簡《日書》作為反映民間禮俗信仰的數術書,其發現引起學界的重視。《日書》研究集中了頗多學者的學力,已經多有力作推出[49],然而有關研究的奠基之作,應當包括陳夢家對于武威出土“占書、日禁之書”的研究成果。
收入《漢簡綴述》的《武威漢簡補述》一文,分“日忌簡冊”和“關于‘文學弟子’的考述”兩個部分。其第一部分將原以為分屬二冊的“日忌”簡試重擬編為一冊,并復原如下:
1 甲毋置宅不居必荒 乙毋內財不保必亡 丙毋直衣 □□□
2 丁毋威□□多作傷 戊毋度海后必死亡 己毋射侯還受其央
3 〔庚辛……………〕 壬毋□□必得□□ 〔癸毋……………〕
4 〔子毋…………… 丑毋……………… 寅毋……………〕
5 〔卯毋……………〕 〔辰〕毋治喪□□□□〔巳毋……………〕
6 午毋蓋屋必見火光 未毋飲藥必得之毒 申毋財衣不煩必亡
7 酉毋召客不鬧若傷 戌毋內畜不死必亡 亥毋內婦不宜姑公
陳夢家說,以上文字,“都是八字一句,有韻,字體亦相近,故可并為一冊。此冊至少七簡,今失其一。”陳夢家又寫道,敦煌莫高窟所出一失題殘卷(巴黎,伯2661),《敦煌綴瑣》九○錄其文,其中有這樣兩段文字:
甲不開藏,乙不納財,丙不指灰,丁不剃頭,戊不度□,己不伐樹,庚辛不作醬,壬不書家,癸不買履。
子不卜問,丑不冠帶,又不買牛,寅不召客,卯不穿井,辰不哭泣、不遠行,巳不取,午不蓋房,未不服藥,申不裁衣、不遠行,酉不會客,戌不祠祀,亥不呼婦。
其內容與漢日忌簡冊各有異同。簡冊可辨者十二條,和殘卷相同的是乙、戊、辰、午、未、申、酉、亥等八條。而甲、丙、己、戌四條與殘卷不同。陳夢家說,殘卷“丙不指灰”可能是“直衣”的誤錄。“戊不度□”,“度”下所闕應是“海”字。“辰不哭泣”和簡“毋治喪”應是一事。《論衡·辨祟》:“辰日不哭,哭有重喪”,可知東漢已有辰日不哭、不治喪的習俗。又敦煌殘卷“申不裁衣”與武威漢簡“申毋財衣”同。《論衡·譏日》說“時日之書,眾多非一”,又說:“裁衣有書,書有吉兇,兇日制衣則有禍,吉日則有福。”陳夢家注意到敦煌殘卷所錄“裁衣”之忌:
春三月申不裁衣,夏三月酉裁衣兇,秋三月未不裁衣,冬三月酉兇。
丁巳日裁衣煞人,大兇。
秋裁衣大忌申日,大吉。
申日裁衣,不死已兇。
凡八月六日十六日廿二日不裁衣,兇。
…………
晦朔日裁衣被虎食,大兇。
陳夢家進行對比后還寫道:“凡此以申日忌裁衣最多。殘卷分別‘寅不召客’‘酉不會客’而簡作‘寅毋召客’,稍異。殘卷‘丑不冠帶,又不買牛’與簡‘戌毋內畜’不同。殘卷以丑日不冠,與漢俗不同。”陳夢家又引《論衡·譏日》所謂“造冠無禁,裁衣有忌”,“沐有忌,冠無諱”,指出:“此可證漢代裁衣有忌而造冠與戴冠無日忌,則此殘卷所記乃是漢以后始有。”[50]有關“裁衣”宜忌的規定多見于《日書》[51],而陳夢家在整理武威漢簡時即已經有所涉及,是較早關注這一社會生活現象并且進行初步研究的學者。
在題為“關于‘文學弟子’的考述”的內容中,陳夢家討論了在武威日忌雜簡背面書寫記事中所見“文學弟子”稱謂的意義。他指出,“文學弟子”最可能是指郡國文學官的弟子。有關考論探索了西漢“文學”作為一種身份的源流,也涉及當時學校選舉制度以及相關的社會文化形態。[52]
對于狹義的“文化”,陳夢家也多有值得重視的論點發表。例如關于漢代的文書書寫形式,陳夢家的簡牘學成果中也有考證和說明。
古有“漆書”之說。例如《東觀漢記·杜林傳》中所謂“于河西得漆書《古文尚書經》一卷”。馬衡曾經在《凡將齋金石叢稿》卷七《書籍制度》中寫道:“至寫字所用之材,最初以漆書,其后利用石墨。因為照進化程序而言,應先用天然材料,而后有比較進步之人工制造材料。漆為木汁,無待于發明,文字最初用漆書,應為合理之事實。漆之燥濕不易調節,故又改用石墨,亦即石炭,俗謂之煤。顧微《廣州記》曰:‘懷化郡掘塹得石墨甚多,精好可寫書。’戴延之《西征記》:‘石墨山北五十里,山多墨,可以書。’是皆天然之墨,今稱燃料曰煤,蓋即墨字也。又其后以松燒煙,加膠制墨,則出自人工制造矣。但《后漢書·杜林傳》所載‘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及《后漢書·儒林傳》所言‘賄改蘭臺漆書經字’,恐已非真漆書。蓋后漢時人造書墨已盛行,不應尚用漆書,或此為相傳古本,非漢時所書也。”[53]東漢“漆書”所謂“為相傳古本,非漢時所書”的推測看來沒有什么根據。雖然“漆為木汁,無待于發明”,但是既然有“天然之墨”,則不必用墨書在用漆書之后。陳夢家《由實物所見漢代簡冊制度》文中說到《后漢書·杜林傳》及《儒林傳》兩例,指出:“凡此漆書,恐怕仍然是墨書。”[54]但是后來還有學者認為,“簡牘的書寫,應以墨的使用,漆的生產和筆的發明為前提條件。”[55]李學勤指出,據考古發現,“所有簡上的文字,都是用毛筆寫的,蘸的是黑色的墨。完全沒有用漆寫的”[56],“古人有‘漆書’之說,前人已指出‘漆’是指墨色黑而有光,并不是用漆寫字。”[57]這里所說的“前人”,似至少應當包括陳夢家。[58]
《漢書·藝文志》共著錄當時公家秘府所藏三十八種圖書,計五百九十七家,其中有的以“篇”計,有的以“卷”計,以“篇”計的大約占72%。實際計有八千八百四十二篇,四千三百四十卷,篇數超過篇卷合計數的67%。有的著作則又各有分別以“篇”、“卷”計的情形,[59]按照一般的理解,帛書以“卷”計,簡冊以“篇”計。這種情形,可能是同一書兼有帛書和簡冊兩種本子。馬衡指出,“《漢書·藝文志》撮錄羣書,或以篇計,或以卷計。以篇計者為竹木,以卷計者為縑帛。卷之數不如篇多,又可見西漢時代縑帛雖已流行,而其用尚不如竹木之廣。”[60]陳夢家《由實物所見漢代簡冊制度》則提出“以篇計者為竹木,以卷計者為縑帛”的說法是可以商榷的。例如《后漢書·杜林傳》“漆書古文《尚書》一卷”,既是簡冊而又稱“卷”。又如《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說,司馬相如去世,天子使者前往取所著書,其妻說道:“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也是簡冊稱“卷”的實例。出土漢簡也有稱“卷”的例子。如居延漢簡(8.1和46.7)是兩冊簿書的署檢,稱“吏病及視事書卷”,可證簿札之成編者可以稱為“卷”。又如居延漢簡(208.5)在署檢上端寫一“卷”字,這已成為后世檔案卷宗的濫觴。按照這一認識推斷,《漢書·藝文志》中“以卷計者”,可能其中也有相當一部分也是簡冊,而并非縑帛。那么其中簡冊本圖書所占的比例,還會大大超出我們前面所作的估算。事實更可以充分證明“西漢時代縑帛雖已流行,而其用尚不如竹木之廣”。縑帛的價格是相當昂貴的,皇家圖書檔案中收藏的書籍尚且以簡冊為主,民間流行的書籍當然以簡冊本更為普及。
陳夢家《由實物所見漢代簡冊制度》一文推斷,“在刮削平整,打磨光滑以后,書寫之前,似經過一道用特殊液體涂染的手續。”武威漢墓“出土木簡表面有光亮,似涂膠質者”。[61]這一發現,對于認識當時的文書制度,也是有意義的。
《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老而讀《易》,“韋編三絕”。《漢書·儒林傳》也寫道:“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顏師古注:“‘編’,所以聯次簡也。言愛玩之甚,故編簡之韋為之三絕也。”有人據此以為“古者用韋編簡”,不過,文物考古資料中始終沒有看到“韋編”的實例。[62]也有人認為用韋編簡與用絲麻不同,是由簡牘的穿孔編貫。清代學者李淳在《羣經識小》卷四《論方策》中就推測說,簡狹而長,編簡者大約是在簡的端部穿孔,“按其次第以韋穿之”,孔子讀《易》,韋編三絕,說的就是這種情形。陳夢家指出,“敦煌出土《急就章》,‘第一’兩字刻在觚端斜削之處,而‘第’與‘一’之間作有穿束之孔。此‘第一’之‘第’猶‘卷一’之‘卷’,最初是名詞,后來引申為次第的形容詞。簡冊所稱‘第一’‘第二’乃是‘冊一’‘冊二’之義。由此可知書冊分‘第’之法由于韋束,而韋束乃編束木札或木觚之上端穿孔之用,不宜作為編綴編冊的繩綸。因如以韋編冊,則卷用不便。”而王尭等考察新疆出土吐蕃簡牘時,確實發現,簡牘“在右端常有一洞,可以用繩子穿聯在一起”,研究者以為“即所謂‘韋編’”。[63]
陳夢家《由實物所見漢代簡冊制度》一文還通過武威漢簡《儀禮》的實例考察了當時簡牘書寫時每一簡容字大致的定規:
甲本木簡七篇是占數最多的,其中大多數以六十字為常例,當然每簡容許有一、二字的上下。《泰射》一篇百十四簡,最為嚴謹,多數簡為六十字,較少的為五十九字或六十一字。《少牢》一篇的前四十一簡,每簡字數略多于六十字而不超過七十字。只有《特牲》一篇第四十一至五十三的十三簡,是利用舊簡,一行八十字上下,和七篇中其它部分不同。
乙本木簡短而狹,字也小,故一簡容字一百至一百零數字,其第十七簡最多,為一百二十三字,幾乎為甲本一簡的倍數。
丙本竹簡的字數很參差,多者五、六十字,少者二、三十字。這由于它是分章的《喪服》經,每章另行起,故新章前一行多不足行;又由于因避竹節要多空一些,否則它也是以六十字為標準的。
《后漢書·光武帝紀上》李賢注引《漢制度》說到帝王下頒的文書有策書、制書、詔書、誡敕四種形式。“策書”又有篆書和隸書兩種書體:“策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木兩行,唯此為異也。”王國維《簡牘檢署考》指出,簡牘書體有這樣的等級差別,“事大者用策,篆書;事小者用木,隸書。”陳夢家《由實物所見漢代簡冊制度》一文也討論了漢代簡牘書體,他認為,當時大致有這樣四種情況:
一是篆書,用于高級的官文書和重要儀典的書寫。
二是隸書,用于中級的官文書和一般經籍的書寫。
三是草書,用于低級的官文書和一般的奏牘草稿。
四是古文,用于傳習先秦寫本經文。
有的研究者提出,事實上,古代書體是隨時代不同、場合不同而有復雜的變化的。因而王國維和陳夢家的說法各有不完善之處。不過,我們今天考察簡牘的文體,盡管存在皇帝詔書有時也書寫草率,而習字之作有時竟頗為工雅的情形,但從總體來說,篆書、隸書、草書在漢代文書形式中大體已經形成了等級差別的事實,是確實存在的。
簡牘文字的修改,據陳夢家的分析,大致有這樣三種形式:一為削改。這是最為多見的情形。在簡牘實物上可以看到被削去薄薄一層表面,而補寫的字跡往往暈開,易于識別。削改的實例大致有七種:①寫錯一字,削改后改寫一字,原字位不動;②寫錯偏旁,只削改偏旁,其余部位不動;③寫錯幾個字,削改后仍補寫幾個字;④漏寫數字,將一小段削去重寫,改寫后字位擁擠;⑤多寫了字,刪除改寫后,原占字位有了空缺;⑥錯字削去后遺忘未及補寫;⑦誤重抄書一段,刪削后不作補書,留出空白。二為涂改。削改一般是事后發現錯誤削除原寫而改寫的,涂改則是書寫當時即發現錯誤,不加削除,匆忙用水涂抹字跡,重新書寫,因而補寫后字跡周圍保留有涂抹痕跡。三為添寫。因簡札寬度有限,在字跡較小,排列緊密的情況下,在原字間側補寫更小的字;在原字較大,排列疏散的情況下,則直接補寫在兩字之間。
陳夢家《由實物所見漢代簡冊制度》一文通過武威漢簡《儀禮》的具體研究,總結了當時簡牘書寫時所使用的十一種符號的意義。后來簡牘的發掘者和研究者在記錄和分析簡牘的內容時,也多涉及到簡牘上的符號。[64]
居延漢簡中多有漢帝詔書簡。陳夢家分析出土于居延地灣的長達67.5厘米的著名的甲2551簡,認為這枚最長的簡是三尺之策,判定是西漢詔書目錄編冊中的一枚。此目錄為編冊第二簡。陳夢家推定這一簡冊共十簡,編目最多不會超過六十,但一定在五十二以上。所見目錄的內容為:
①“縣置三老,二” 這是這一詔書目錄編冊中的第二條,大約是漢高祖二年(前205)二月頒布的詔令,見于《漢書·高帝紀上》。陳夢家又推斷列為這一詔書目錄編冊中第一條的,可能是“約法三章”。
②“行水兼興船,十二” 這是這一詔書目錄編冊中的第十二條,陳夢家以為“此當指治水及行船之事”,其實,從睡虎地秦簡《日書》的內容看,“行水”,應是指水路行旅、水路航運。而“興船”,可能是指造船。
⑤“郡國調列侯兵,卌二” 這是這一詔書目錄編冊中的第四十二條,內容涉及郡國調遷列侯兵事,此事史書失載,陳夢家推定此詔書的頒布,在呂后元年(前187)詔之后,漢景帝后三年(前141)詔之前,大約在漢文帝時代。[65]
對于漢代文書制度和文書習慣的研究,看似瑣碎,卻多能夠反映當時的文化體制和文化風貌,對于文化史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1959年,甘肅武威磨嘴子十八號漢墓出土木簡十枚,記載漢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幼伯受王杖事。并錄有漢成帝建始二年(前31)九月“年七十受王杖”的詔書,以及河平元年(前28)毆擊持有王杖者應當處以棄市之刑的令。這就是著名的“王杖十簡”。由于簡上沒有編號,出土時次序已經擾亂,對于這十枚簡的排列方式,學術界存在不同意見。陳夢家《王杖十簡考釋》提出的編排方案,是最早發表的比較成熟的意見。[66]
陳夢家早年以詩作知名。青年陳夢家的詩句能夠震動人心,感染精神,不僅在于他的創作很早就與風花雪月的無聊呻吟劃清了界限,在抗戰救亡時期又有《在前線》組詩這樣的熱情奔揚之作問世,還在于他的吶喊與歌哭,很早就是以對于民族歷史和民族文化的理解和感懷為基點的。他的《塞上雜詩》、《唐朝的微笑》、《秦淮河的鬼哭》、《古戰場的夜》、《秋旅》、《太平門外》等作品,字句間都飽含深沉的歷史感想和文化思緒。如他在《鐵馬的歌》中寫道:“沒有憂愁,/沒有歡欣;/我總是古舊,/總是清新。/我是古廟/一個小風鈴。/太陽向我笑,/銹上了金。”通過這樣的詩句來認識和了解中年時代開始簡牘研究的陳夢家,依然是適宜的。他雖然深懷“清新”精神,卻能夠面對“古舊”,立足“古舊”。這一風格貫徹于他的文學生涯,同樣也貫徹于他的學術生涯。
陳夢家學術盛年不逢學術盛時,在五十五歲正全力投入簡牘研究時不幸逝去,使得從某種角度看來,大陸的簡牘學有所停滯并出現了一定意義上的倒退。
陳夢家的簡牘研究論著中的若干具體結論可能因資料的新發現和研究的新進展有修正的必要,但是他的學術精神,以及他從事簡牘學基礎建設的功績將在學人心中永存。
陳夢家是在一九六六年異常的政治風浪中以異常的方式結束學術生命的。三十七年過去,我們在懷念他的同時,應當以簡牘研究的新進步作為最好的紀念。我們也希望,簡牘學研究能夠在社會形勢的安定、考古發現的累積以及學術交流的擴展等方面,于比較陳夢家所處的學術時代更好的條件下實現健康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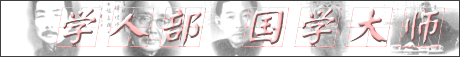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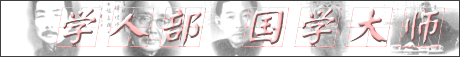

mailto:guoxue@guoxue.com
![]() 010-68900123
010-6890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