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保守主義者,或者現(xiàn)在所說的“國學(xué)派”,其言論有一個最基本的判斷,即,“國學(xué)”———無論是狹義的還是廣義的,都是可供重建、振興的。這個判斷,又建立在對國學(xué)衰微原因的錯誤認(rèn)識上。人大校長紀(jì)寶成在接受《新京報》采訪時,將“國學(xué)衰微”的原因歸之于“歷史虛無主義和‘左'的思潮泛濫”。由此可見,紀(jì)校長認(rèn)為,是外部的壓力,
而不是國學(xué)內(nèi)部的因素,決定了國學(xué)的命運。在這個基礎(chǔ)上,“國學(xué)派”只需要通過辦國學(xué)院這樣的方法,將外部壓力抹掉,國學(xué)復(fù)興指日可待,“中華民族的偉大復(fù)興”亦指日可待了。
事實上,正是國學(xué)自己,而不是其他人擊敗了國學(xué)。
1840年以后,中國人花了100年的時間,將這個古老的文明改造成現(xiàn)代國家。這個改造的過程,建立在對現(xiàn)代性認(rèn)同的基礎(chǔ)上———哪怕僅僅是被迫的認(rèn)同。在這個現(xiàn)代框架下,中國人刷新了自己的語言、自己的符號系統(tǒng)和自己的精神體驗,盡管這與前現(xiàn)代中國的語言、符號系統(tǒng)、精神體驗關(guān)系密切,但它們之間依然存在著鴻溝。在這些新工具的幫助下,中國的民眾正在建立屬于這個時代的中國文化。它的輝煌燦爛程度,并不遜色于那個已經(jīng)衰落的前輩。
事實上,即使是在“國學(xué)”的內(nèi)部,這樣的新陳代謝也始終沒有中斷過。“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我們總是用這樣的歸納來表達中國古代文學(xué)的簡約歷史。文體的演化,正是社會經(jīng)濟文化狀況變化的結(jié)果。用政治教科書里那句磨疼了耳朵的話說就是:經(jīng)濟基礎(chǔ)決定上層建筑。當(dāng)經(jīng)濟基礎(chǔ)不再為某種文化提供合適的環(huán)境時,為它設(shè)立一個保護基地,使之成為被瞻仰和被保護的對象成了最后的舉措。
這也就是為什么那些曾經(jīng)被我們認(rèn)為是最有趣最精彩的“玩意兒”,最終都被送進了博物館。
很顯然,這并不僅僅是“國學(xué)”一家碰到的問題。文化保守派忙碌得無暇關(guān)注他們海外同行的言論與行動。
1994年,“西學(xué)”的大師,耶魯大學(xué)文學(xué)理論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Bloom)出版《西方正典》(TheWestern Canon)一書。在書中,他為莎士比亞學(xué)、彌爾頓學(xué)或者但丁學(xué)的衰落頓足捶胸,并以一種咄咄逼人的姿態(tài),對“西學(xué)”面臨的“歷史虛無主義和‘左'的思潮泛濫”進行了批評。這本書最近由譯林出版社引進出版了。文化保守派不妨仔細(xì)研讀,爭取與海外同行構(gòu)筑掎角之勢,為捍衛(wèi)“古典主義”的尊嚴(yán)戰(zhàn)斗到底。
改造“國學(xué)”也是“國學(xué)派”的重要議題,總有人覺得使之成為一個具有現(xiàn)代性的學(xué)科,就可以挽回已去的大勢。于是,在紀(jì)寶成教授的理想中,“對《孫子兵法》的研究”和“對《管子》經(jīng)濟思想的開發(fā)研究”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李零教授在其《真孫子》一文中揶揄的“國學(xué)應(yīng)用研究”,被隆重地放到了人大國學(xué)院的神龕上。
還是讓“國學(xué)”回到書齋中去吧,就像那些偉大的前人做的那樣———在蘇格蘭北部的尼斯湖里,居住著一位名叫Nessie的家伙。這位屬于7000萬年前的貴族,在遠(yuǎn)離人類視線的地方孤獨地生存繁衍著,如它那些消失了的同類一樣。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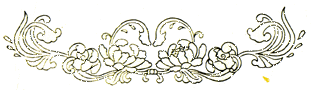
![]() web@guoxue.com
web@guoxue.com